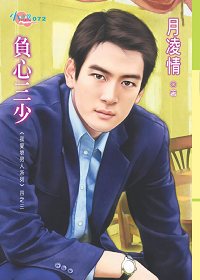北京男人和上海女人-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趿拉——”、“趿拉——”,爸爸的拖鞋是用一双退役塑料凉鞋改装的,走路敲打地面的声音跟木制趿拉板一模一样。这声音也敲在厨房母女三人的心坎上,都心情各异地望着书房和厨房之间的门。没能够把事情处理好,还得麻烦男人出面,妈妈心里责备自己无能,瞪两个孩子,嫌她们惹是生非。
“喊什么啊,山嚷怪叫的。”随着浓重的喉音,一个身材瘦高的半老年人跨进厨房。怕碰到门梁,他有意识地哈着腰,叫人感觉他突然有了水蛇腰的身段。
八仙桌的上首是把靠背椅,周围摆着的都是样式各异的凳子,有的坐上去还会唧唧叫。进到厨房,爸爸朝靠背椅走去,妈妈上前一步把它拉出来。从孩子们记事起,这把靠背椅就没动过地方,而且只允许爸爸一个人坐。结果光看见这把椅子,孩子们就能够肃然起敬。
“怎么回事?”爸爸扶着桌子往下坐,脸对着桌面问。话问完,也坐稳,他抬头冷冷地看二丫头,进行审讯前摧毁心理防线的工作。由于有意识地撅着嘴给二丫头看,把本来挺好看的薄唇弄得厚了好几分。
小丫头上前要向爸爸介绍案情,爸爸眼睛没动地方,朝她一摆手,小丫头泪水一下子涌上来。这一小小的摆手蕴涵着多少父爱和信赖啊,她心房紧缩,委屈地出长气。
外面有葡萄遮挡,又有纱窗过滤,上午的阳光照进来,形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光柱,整个厨房亮堂堂的,尘埃的飘荡也历历在目。阳光散射到西山墙上,让那里摆放的橱柜、条桌,以及它们之间的洗菜池子,还有地上放的脸盆、蒸锅、瓦罐、桌上放的案板、油盐酱醋瓶,以及墙上的筷子笼什么的,都本色分明,油乎乎的带着质感,仿佛名家油画上的物件。
西山墙齐腰高的地方贴着一圈报纸,用图钉按着,从发旧破损的程度看,不难猜出是春节大扫除时更换的。条桌上方的墙上,也就是对着厨房通向院子那扇门的地方,有一张对开的工笔画。因为它四周的墙,不是泛碱,冒出许多疙疙瘩瘩的东西;就是因渗水而发黄,反衬得这画有股少女般的整洁,给这间杂乱的屋子提升了档次。
这画是大女儿入团时,宿舍战友送她的礼物。拿回家她要挂到北屋正墙上,取代镶嵌着封建文人字画的四扇屏。爸爸不同意,她批评爸爸“不接受革命新生事物”,爸爸说这画“比例失调”。
画里面是三个年轻人,分属于“工农兵”的不同阶层,他们伸着胳膊合伙托着的一颗红心。红心有西瓜那么大,落款是“把一切献给党”。
说服不了父亲,大女儿只好把画贴到厨房,摘掉原来挂在那里的月份牌和陈旧年画。心里多少有点委屈,贴的时候她不停地叨咕,说爸爸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不留神被爸爸听见,老人家严厉地驳斥她,毫不客气回骂一百多句。整个发泄过程就听爸爸一个人在嚷嚷,静悄悄的,他也不怕邻居说他发夜症。
二丫头的确拿了妹妹的钱,她明白又到爸爸大发雷霆的时候。面对爸爸的灼人逼视,她坦然地和他对视,勇敢地僵持几秒钟,便随意看别处,眼皮天真地眨着。
爸爸瞪着她,缓慢地问拿没拿妹妹的钱,叫她说实话。她犹豫地说“没拿”,看爸爸一下,就不知道再往哪里看好了,身上开始痉挛。
“什么没拿?我早就发现我的钱少了,只是没说。”小丫头急不可待对着爸爸讲述,“刚才我假装上茅房,其实我根本没去,到了外院我就回来了,藏在窗台下面。我看见她翻我的抽屉,使劲抠钱,从我的手绢里……”她手指头朝着爸爸弯弯,“我原来那么多的五分钢蹦儿,都没了,得有两毛多呢,现在都没了!对啦,我还没看毛票少没少呢。”她掉头跑进里屋。她只穿着背心裤衩,裤衩的松紧带懈了,她一边跑一边往上提。 。。
第三章
第三章
从里屋出来,小丫头手里拿着一个裹成一团的手绢。打开里面是一卷脏兮兮的毛票,用猴皮筋儿勒着。她解开猴皮筋儿,套在手腕上,把毛票展开,手指头沾一下舌头,捻开一张,嘴里数:“一毛……”提一下裤衩,再捻开一张,嘴里数:“两毛……”
爸爸问二丫头,没拿妹妹的钢蹦儿都哪儿去了?二丫头没回答,极其痛苦地凝视空气中的某一点,脸色先是凝重,慢慢有些意味深长的舒展。以往看过的神话故事在脑海里飞扬,宝葫芦啦,*飞毯啦……最靠谱的是希望孙悟空叔叔来搭救。
二丫头仰着脑袋看天花板,妈妈以为她在犯拧,急忙捅她一下,二丫头猝不及防后退一步。看见妈妈朝自己眨麻眼睛,她会意,非常温顺地看爸爸,不好意思地嘟囔:“爸,我错了,下回不介了……我想和她借……还没来得及说……”说着话她用手揉眼睛,忽然哭了,等话说完,哭声也随之停止。
“啊?你还真拿啦?行啦,今天哪儿也别去了,牛奶也别喝了。倒省钱了。”爸爸双眼皮的眼睛瞪起来,两道褶子像是后天割的,一样的长短和深浅。
“你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不学好?”妈妈眼睛瞄着爸爸说,“啪——”,她打二丫头后背一下,“说!下回还这样不这样了?”她厉声问。二丫头又踉跄地前进一步,站到原来的位置。“不介了……” 她嘟囔。妈妈瞪她,脸往爸爸跟前凑,低声说她打了,爸爸就别打了。一缕乌黑的头发掉下来,她随手理到后面。头发这么黑是染的,别看爸爸的发黄,却是自然天成。
爸爸似乎没听见妈妈说什么,站起来伸出纤细的手指解小褂的扣子,脱下后递给妈妈,妈妈接过来郑重地搭在弯曲的小臂上。爸爸身上只剩件背心,横的竖的骨头一目了然。他迷着眼睛端详二丫头,像是不认识,平缓地对妈妈说这次不打她。随后问她除了这回,还拿了妹妹多少钱?二丫头两手垫着屁股,身子笔直地贴在墙上,揣摩着爸爸的脸,说以前还拿过几回一分、二分的钢蹦儿。爸爸命令她交出赃款,她回里屋把藏在秘密处的几枚钢蹦儿交给爸爸。看到自己的钱,小丫头伸手去拿,爸爸一把捂住,说先借他用用,待会儿再还她。
小丫头做作地歪着脑袋听;等爸爸说完,她说前几天想买二分钱的黑枣解谗,结果拿出“储蓄”发现,一分二分的钢蹦儿都没了。当时怀疑小姐姐行窃,但苦于没有证据,于是今天假装上茅房,留小姐姐一个人在屋,纵容她作案……她叨咕着,爸爸不听了她对着妈妈说,妈妈不听了她对着小哥哥说,都没人听了她自言自语。市场尽管如此冷淡,她还是为自己计谋的得逞而笑出两个酒窝,看着倒像是拣到钱。
小哥哥李云是刚进来的,他是黄城根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在他们这三个小的上面还有一哥一姐,老大是儿子,叫李露,在清华大学拖拉机系读书,今年毕业;老二就是张贴宣传画的大闺女,李雯,解放军文工团的演员。
大花猫跟在小哥哥后面进了厨房,它翘着尾巴在桌子腿上蹭痒痒,然后在地上打滚。
爸爸把几枚钢蹦儿在手里掂掂,抬头示意妈妈他们可以走了。丈夫打孩子不习惯旁边有人,妈妈眉头一皱,要和他说点什么。爸爸不耐烦地一挥手,说“我知道”,没礼貌的样子和地主资本家对待劳动人民一样。
二丫头用留恋的、甚至企求的眼光送妈妈他们离去,居然还用同样的目光看妹妹,真是大难临头、化敌为友。
屋里只剩下二丫头和爸爸,她在裙子上蹭蹭手上的汗,忽而夸张地哭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爸,我错了,别打我……从今天开始我天天扫茅房……爸,别打我,我错了……从今以后我天天给您捶腿……爸,别打我……从今以后我天天刷碗……爸,别打我……”嘴唇痛苦地哆嗦。
爸爸很少给孩子们零花钱,激励他们收集家里废弃的牙膏皮、废电池、碎骨头什么的卖废品,换回买零食的款子。相对来说小丫头更会过日子,因此她攒的钱比哥哥姐姐都多,难免叫人眼红。
爸爸不理睬二丫头的求饶,刚毅地合拢着嘴,走进里屋。估计他是拿扫炕笤帚去了,二丫头立刻放开喉咙大哭。大花猫立起耳朵,目不转睛看她。爸爸很快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闹钟,她马上不哭了,莫名其妙看爸爸。爸爸把闹钟放在吃饭的桌子上,走到水池子边,从夹缝里拿出搓板,用手胡噜胡噜这面、胡噜胡噜那面。他只顾低头走路,脑袋碰到横贯厨房的一根绳子,上面晾着的笼屉布掉下来。二丫头赶快过去拣起来,抖搂抖搂,郑重其事晾上。她有意拖延时间,希望爸爸看见。
爸爸将搓板放在饭桌前的空地上,想想,又弯腰拿起,回头让二丫头跟他走。“爸,不打我了吧?”二丫头小心地问,孝顺地笑。根据以往的经验,爸爸打他们一般用扫炕笤帚,打哥哥用皮带,对于搓板的作用一时不甚明了。“走!”爸爸催促她。看爸爸态度没有改善,二丫头又开始啼哭,走两步哼哼一声,同时偷看自己这一套在爸爸脸上的反映。
爸爸前面走二丫头后面跟,穿过客厅到了爸爸妈妈的寝室。妈妈他们都在客厅坐着,路过时,二丫头瞪妹妹,妹妹甜蜜地笑。
爸爸妈妈的寝室里有一个立柜,一扇门上安有镜子,爸爸把搓板放在镜子前,然后看着镜子,不断把搓板往后踢,直踢到他整个人都被镜子里呈现。好像还有什么不放心,他在搓板后面站好,双腿一点点往下蹲,要练中国功夫似的。蹲到后来,身子前后摇摆,为了保持平衡张开的两条胳膊,上下舞动像只大蝴蝶在扑腾。
“跪下——”布置就绪,他手指搓板命令二丫头。
瞧半天了,看爸爸在镜子前面做出各种顽皮的举动,她觉得挺有趣,专注的时候差点发表意见。听到爸爸叫她“跪下”,她快步上前,带着点急不可待,尝试新鲜玩具似的。
除了爱吃好吃的,照镜子是二丫头又一大业余爱好。她兴冲冲跪下,整理整理头发,揉揉眼睛,用力把它撑大。干妈早说过,姐妹当中数自己漂亮,真真假假哭了半天,原以为准得特别难看,可是现在看着,比平时还有气质,可怜兮兮的叫人心疼。
第四章
第四章
“啪——”她头顶挨了一下,一缩脖子,听爸爸问她:“听见了吗?我问你呢。”二丫头茫然地看他。爸爸已经一根鸡毛掸子在握,看她不说话又说:“数数多少钱?”用鸡毛掸子敲她跟前的地面。二丫头低头看,原来自己拿妹妹的那几枚五分、二分、一分钢蹦儿在面前一字排开。她数数说是三毛四分钱。“一共三毛四,对吧?一分钱罚跪两分钟,二四得八、二三得六……三毛四是……六十八分钟。”爸爸用掸子指墙上的挂钟,“罚跪六十八分钟。不准哭,哭一声延长十分钟。”说完他把掸子放在梳妆台上,脱去裤子,换上在家穿的便装,从床头拿起一本书,躺进躺椅,脚架在凳子上,将书翻到看到的地方看起来。
头一次跪搓板,原来以为这东西老实巴交的,亲身体验才知道它可比扫炕笤帚打屁股厉害。二丫头用余光瞄着爸爸,身子悄悄向后挪,坐在脚后跟上。“啪——”她后背挨一下鸡毛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