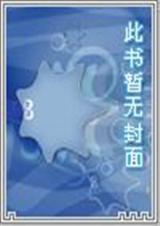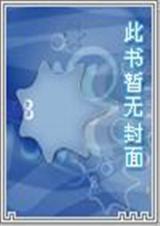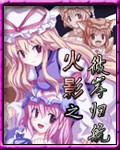母爱的阴影-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踩到刚割过的稻茬子上,会把脚扎破。起初我们还能保持正确的姿势,刷刷刷地一直割过去;没多久就站不住了,只好蹲着割;再后来蹲也蹲不住了,就单腿轮换跪着割。第一天劳动下来,人人腰酸腿痛,手打泡脚流血,可谓伤痕累累。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时感觉浑身疼痛,不想动弹;但毕竟是年轻,只要咬一咬牙跳下床,胳膊腿活动活动就没事,照样又是一天。
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课上课下疯狂地阅读。上课不听讲,迟到旷课也是寻常事;有的课我根本不上,在宿舍泡病号。为了能“治理”我,第一任“队长”(班主任)对我软硬兼施,结果也不起任何作用。我向他扬言:“要不你开除我,我正好不想上呢!”把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要打我。
期末考试八门功课我有六门不及格。补考时我照复习提纲恶补一气,虽说是“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佛脚居然显灵,又全部通过了。
一学年下来,我虽然补考后勉强升级,却因旷课太多,屡教不改,班主任把我的材料总结上报,我受到学校记大过的纪律处分,张榜公布。
我破罐破摔,还是满不在乎。
我成了班上乃至全校的“个别生”。
由于我在学校的恶劣表现,爸爸到学校来过几次,我开始认识爸爸的另一面。在外面,爸爸是一本正经的“国家干部”的形象,当着老师,给我大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我热爱农业。在学生宿舍,对我和同学讲什么:“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树立远大理想。”他讲那一套大道理很认真,也很投入,同学都戏称他是“革命干部”。
二.浪子回头
因为农校的前身是农场,所以在许多称谓上保留了农场的传统。比如班主任叫“队长”,校长叫“场长”,年级叫“中队”,年级组长叫“中队长”等等。到后来学校逐渐发展走向正规,这些老称谓才慢慢消失。
对于我们这些农校的“元老”来说,老称谓更显亲切。
农校有两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位叫丛选永,一位叫张维安。
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队长,他叫丛选永。
他是个特别祥和的人,时常面带微笑,很少激动,说话声音也不大,显然没有前一任队长厉害。
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和前一任队长不一样,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一种关切:
“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觉得你不是坏学生,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我说的对吧?”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这话让我心里一动。
“你有理想,喜欢文学,这是好事,你完全不用放弃。俗话说‘艺不压身’,将来工作中都用得着。”
“但你别脱离现实,你现在上了农校,就应当有新的理想。”
“马克思都说人是无法自己选择职业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留校给你们当老师。”
丛老师说他自己也是农校毕业,比我们大几届。
“别把自己的一辈子荒废了。只要你振作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你抱很大的希望。”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受到真诚。
我无法把丛老师十几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内容完全回忆并记录下来。实际上,与其说我是被丛老师讲的道理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的。
在丛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燃起了上进的希望。
在学校农场劳动的,还有从教育口转来的“右派”和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语文老师张维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年级时,我们在劳动时看见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男子在猪场挑泔水喂猪,这个文质彬彬的猪倌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劳动休息时我们和他聊天,他知识渊博,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谈古说今,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但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喂猪,他笑而不答。
二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上他的课没有纪律问题,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我们班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我们有时到教师宿舍找张老师
聊天。他没有架子,对我们亲切得像朋友一样。
“知道你们喜欢文学,你们都基础不错。听说有的人想当作家、诗人?”
我脸红了,不知他指的是谁。我们都忙着解释:
“不是,不是,就是有点喜欢。”
“其实作家很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尔基小学没毕业,鲁迅是学医的,也相当于中专。”
他笑着说:
“我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你们看我,还不是作家吧?”
我们也跟着傻笑。
“作家需要生活,这些你们现在可能还不懂,以后就能体会了。”
“但千万别混日子,我呢,在猪场就好好干活,现在就好好教书。”
他意味深长地说:
“好好念书吧!你们年轻,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丛老师和张老师的话以至诚动人,寓情于理,深深地感动了我。
老一辈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过: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如果没有二位恩师“从心里发出来”“打到心的深处”的教诲,我或许永远不会消除心中的不平和愤懑,最终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傻瓜。
压在我心头上的块垒逐渐消融,一度迷失的“浪子”,终于回头了。
张老师也夸奖我的作文。有一回张老师在班上朗读我的一篇回忆江南景色的作文,他那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写的;如同一支普通的乐曲经由小提琴大师用名琴出色地演绎,展现出神奇的魅力;我们都陶醉在其中。张老师念完后,有好几秒钟,班上静静的。
张老师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的美,不能仅注意辞藻的修饰,他引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给我们讲过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立志成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老师讲解这几句词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稀可辩。
张老师告诉我们,治学的态度应当是“不雷同,不苟异”,要独立思考。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六十年代初有一股翻案风,给曹操翻案,给潘金莲翻案。我们在图书馆的报刊上看到有关内容,很感兴趣。在给潘金莲翻案的问题上同学们看法不一,成了宿舍熄灯后“卧谈会”讨论的热点。有的说她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有的说她是淫妇,伤风败俗。我们争论不下,去找张老师评判,张老师说得很干脆:
“我觉得潘金莲再追求自由也不应该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没这一条,他爱谁都行;有这一条,我看她永远翻不了案。”
张老师的话一针见血,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的确,如果某种男女之情“自由”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人性为什么还要包容它?
“文化大革命”中,张维安老师受到冲击。“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张老师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篇大块头的文学评论。他的文章论述精到,行笔流畅,文采飞扬,在当时颇具影响。正当张老师由逆境转入坦途之时,他被诊断得了肺癌。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但刘校长极富演讲口才,他的报告幽默生动,我们特别爱听。
刘校长有胆有识,启用了一批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即包括张维安在内的一些人,让他们当上教师。这部分人不少是大学里的才子,教学水平非常的高。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刘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招降纳叛。批斗时让张老师他们陪绑。
虽然农校的粮食定量比较高,自己还有猪场,每个月能吃一次炖肉。对于我们这些活动量大的小伙子来说还是不够。在困难时期,饥饿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饥饿是什么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哦,那没什么,为了减肥我有时也会饿自己一顿的,是有那么点不好受,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多年的饥饿和食品匮乏,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一个遥远的噩梦:不再可怕却挥之不去,可以回忆却难以言传。
我们那时好像是一群饿狼,寻找任何可以放进嘴里吃的东西。收水稻劳动的间隙,有一样工作是要抓紧的:将一支稻穗放在手里来回地搓,搓出米后小心地把稻壳吹掉,然后将米粒倒进嘴里,那新米嚼起来味道很香。这种“手工碾米”的效率很低,一次最多也就二十几粒,那可是我们劳动时重要的加餐。
如果不是收稻子,我们也能找到加餐的东西,因为农场里有的是农作物。萝卜、白薯,从地里挖出来用手擦擦泥就吃;灌浆的玉米棒子,半青半紫的茄子,摘下来就大啃大嚼;周末几个人合伙在水田里捉青蛙,当场开剥,然后用铁桶架起柴火煮了沾盐吃,几乎连骨头一起咽;我们还烧烤过蚂蚱、知了,不是为了寻求美味,而是为了填充老是空虚的肚子。
如果饿得睡不着,同学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吃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会餐”,在美好的想象中咽着口水,慢慢入梦。
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