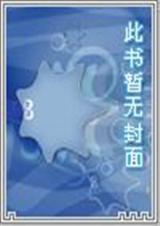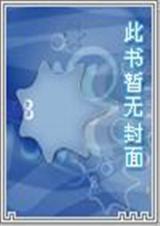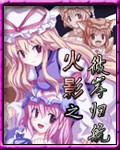母爱的阴影-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个字不差。
对于他来说,思想犹如吃饭一样简单,而且吃什么补什么。他的首要问题就是凭借嗅觉获得要吃的东西,而这只要有一只跟风的鼻子就够了。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他一下车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国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个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你爸爸说想活一百五十岁呢!”
“妈妈”说。
十分注重保养,看起来比他的年龄年轻许多的父亲一脸的自信:
“这是‘参考’上登的,科学家说的,只要保养得好,人人都能活到一百五十岁。”
祈望多寿固人之常情,看了报就给自己定指标的还真不多。
有一个笑话:五代时的王溥,别的已知足,惟独贪寿。找来瞽者算命,问寿命几何,瞽者说王能活到一百三四十岁。王十分高兴,又问:“这中间有什么疾病吗?”瞽者掐算说:“到一百二十岁时,春夏之交会闹点儿胃口,但没大事。”王对子女说:“听见了吗?记住到那年别给我吃凉的。”王溥因此被人讥为“寿痴”。
看来,说假话的人也爱听假话,欺人者更需要自欺。
三.明确的信号
二OOO年,新世纪开始,我的女儿大学毕业。正赶上计算机人才炙手可热的大好时机,所以顺利地当上了“白领”。
教师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宽松,我和妻子除了在学校授课,还做些家教,有时还到外校兼课,我还给一个教育网站写稿子。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到驾校报了名,卷入了“学车热”的大潮之中。
记得小时候“六一”节免费乘公交车,我总要站在司机后边感受开车的感觉;一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一边盯着司机换挡打方向盘;看司机能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操控得停走自如,真是叹为观止;以为除了开飞机开火车,开汽车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了。
所以,我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有当诗人,当工程师之类;都没敢梦想过开汽车。
六十岁左右学车的人,或许都和我差不多,是要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梦。
我学车时闹过不少笑话,过环岛时,教练发口令说:
“环岛直行!”
我一下子踩了刹车,惊疑地问:
“环岛直行,不是开到环岛里去了吗?”
“是转过去,直行!”教练说。
我口里念念有词:
“那就是先右转,后左转,再右转。”
把教练气得没办法。
2002年夏天,我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赛欧”。老四家也换了一辆新车,一辆白色的“赛欧”。
两个儿子家有了新车,爸爸照例要抒一下革命之情:
“老百姓买汽车,过去哪里有过,啊?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如今不得了,真是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啊!”
摇头晃脑,绝对的声情并茂,不过我们是听惯了。
秋天,“妈妈”要去趟南京(爸爸不愿意去),走之前和我说,她往返要一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由我和弟弟们轮流照顾一下爸爸。
“我们四个人安排一下不是问题,你就放心吧。”我说。
没想到过了几天,爸爸打来电话:
“无敌,你妈坐火车走了。她已经安排好了,平时老二老三老四他们早晚抽空来照看我,周末两天你来管。”
好一个“安排好了”!
要是在过去,我会默认这个安排,容忍这个“小小的”不公正;但这次我要说“不”。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我周末没空。”
“你来不了,我可以住到你那里去的。”爸爸还不想改变主意。
“你们不和我商量,我不接受这个安排。”
说罢我放下电话。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公正,我起码要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不公正。
我要“帮”他们改改不公正的“习惯”。
后来从老四那里得知,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爸爸和老三定的。打出“妈妈”的旗号,想必是以为我会避免与她冲突而不得不接受。为这么一件小事,爸爸还要动如此的心计,真是莫名其妙。
当我抽空去看爸爸时,他非但不解释,不认错,还在那里给我唱高调:
“街坊们都说咱们一家人和和气气,安定团结,是邻里的榜样……”
“你是高级教师,有修养,应当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嘛……”
我真想如梦中那样,照着他那张虚伪的脸狠狠地抽一记耳光。
四.感悟生命
“妈妈”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到医院做了胆囊摘除的手术。
先是说请个看护,后来还是决定让几个妯娌和从南京赶来的妹妹轮流在病房值班。妻子值班时我尽可能用车接送,否则她就要挤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
住院期间,儿女们跑前跑后,我的女儿还给“奶奶”带来了鲜花慰问;同室的病友都十分羡慕,跟“妈妈”说:
“你的儿女多好,你真有福气哟!”
“妈妈”指着妻子说:
“我的大儿媳妇是老师嘛,人最好,最老实了!”
手术很顺利,半个月之后出院,出院那天我开车接“妈妈”回的家。
看见“妈妈”平安回家,爸爸当着众多人的面,总结性地发言:
“这次你妈住院,乐乐(妹妹的小名)立了大功!”
众人都听楞了。
妹妹过意不去:
“也不是我一个人忙,大嫂,弟妹她们都挺辛苦的。”
过些日子我们去看她,“妈妈”给我们准备了“礼物”,给我的是一双皮鞋,给妻子的是一件衣服,我打趣地问:
“怎么,要论功行赏啊?”
“妈妈”回答:
“他们也都有。我这个人,不愿意欠别人的情。”
她说这话时带着几分的自得。
如同过去对我们说:“老三讲了,他是交朋友不交亲戚。”也是带着一种自得。好像是悟出了一条别人不懂,又颇值得自傲的人生真谛。
她还给我的“人情”——那双皮鞋,小,磨脚,穿了一次就扔在床下。给妻子的衣服倒还合身,好像是穿了几次。
2003年春节过后,晚上九点多钟,“妈妈”打来电话:
“你爸爸便秘又犯了,好几天解不出大便。你快来一下,带他去医院。”
我开车过去,把车停在楼下。怕自己开车路不熟误事,在楼下打了辆车。到了医院,值班的大夫护士都在,楼上楼下左奔右突之后,从药房领了吃的药和一瓶洗肠液。
我问:
“到哪儿洗肠?”
护士说:
“这儿不管,自己回家洗。”
“自己洗?自己怎么洗?”我大为不解。
“很简单,用洗肠器,外面有卖的。”
人家回答得正确而简练。
回家的路上,爸爸感触良多:
“现在的医院服务态度真差,和过去没法比。文化革命前,你婆婆(外婆)便秘,医院的主治大夫带上胶皮手套,用手给她一点点的掏,我亲眼看见的。”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了什么:
“现在改革开放,广大医务人员还是好的。这是个别的,个别的。”
说点儿真话他就不舒服。
用一句时髦的“数字化”语言来解释就是: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能自动地启动“纠错程序”。
春节之后的三月底,我的岳父不幸病逝。
他老人家得的是肺癌,从确诊到不治有半年多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岳父的子女们也都忙得不可开交。开车送他到医院检查,诊断;然后是转院,住院,陪床;到后来,那家医院又说床位紧,催着转院,这时别的医院已经不接收了。我们联系了一个临终关怀性质的养老院,正打算第二天过去,就在那天的夜里,接到了病危的通知。
我们赶到医院,妻子的弟弟妹妹也都赶到了那里。岳父大声地喘息着,已说不出话。我不忍看这个场面,退到了楼道,等我再进入病房,岳父已深度昏迷;不久,医生宣布病人死亡。
妻子和她的妹妹在哭,我们几个男性亲属给他换上准备好的寿衣,然后推到了太平间。
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肺癌扩散而能坚持半年之久,生命力可谓坚强;突然的雪溃山崩,又显示出生命的脆弱。
柳宗元诗道:
生死悠悠尔,
一气聚散之。
生命如气一样飘忽易散,这是悲观,抑或是达观?
我想起刚买车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我接女儿下班回家。入四环主路时,由于没有经验,我从引导车道一下子就并到了主车道,而主车道后面不远就是一辆疾速行驶的大型卡车。刹时间,刺耳的喇叭声,轰鸣声,挟着强烈的灯光和震动,排山倒海一样向我们压来;我正预备接受那致命的一撞时,那卡车呼啸着擦身而过,真是生死一瞬。我们都紧张得说不出话,几分钟后,女儿才问了一句:“您怎么这么快就并线了?”
在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生命的脆弱。
我看过一位探险家写的回忆录,说是在没有人烟的沙漠中,一只迷了路的小鸟扑到了他的怀里,已然奄奄一息;他切了一小块梨喂它,小鸟本能地啄了一口就死了。探险家郑重地安葬了它——这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信任人类的小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