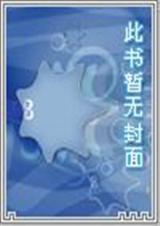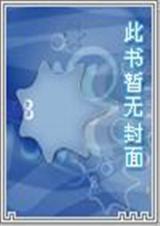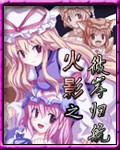母爱的阴影-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船员跳到岸边的岩石上,接过一条钢缆,系在船头。钢缆的另一头是百米开外的电动绞盘,船在钢缆的牵引下,缓缓地越过急流。
经过两三次这样的牵引,江面豁然开朗,武隆码头到了。
我收拾东西下船,用目光在岸上的人群中急急地搜索,凭记忆,寻找照片中见过的母亲和姐姐。
“无敌!无敌!”我听到几声四川口音的呼唤。
我随声音望去,是姐姐在不远处叫我,身边站着母亲,还有小外甥女。
我匆忙赶上前:
“妈妈!姐姐!”
就叫了一声,嗓子就像堵住,说不下去了。
“无敌!”
母亲的声音哽咽,也就这么一声。
间隔三十年的母子相认,一切都包含在这一声寻常的称呼之中。
姐姐接过我手里的东西,亲切地说:
“走吧,回家好好歇歇,你一路上辛苦得很。”
姐姐的家是武隆县邮电局的职工宿舍。
如果说重庆是座“山城”,那么武隆县城应当称之为“小山城”。整个县城依山临江,房屋错落有致,石板路纵横其中,上下的台阶曲折,路旁的竹子丛生,自来水管就裸露地铺设在路边,是地道的南方小山镇的景象。
每天早上,母亲为我磨豆浆做早点。那是一种南方才有的小石磨,我第一次看见用这种工具做豆浆。母亲一只手摇着磨,另一只手将泡好的豆子和水倒进磨孔,白花花的豆浆像瀑布一样从石磨边沿流下来。我过去帮她,母亲便放开手看我摇,说:“别那么快,要慢点,对,对。”磨完之后她熟练地用纱布滤出豆渣,把豆浆拿去煮。不一会儿,香喷喷辣簌簌的四川豆花就做得了。
母亲的饭和菜都做得非常的香。怕我不适应,做菜已然少放了辣椒,对我来说仍是辣得可以;但四川菜没了辣味也就没得了香味,这简直就是蕴涵了一条人生的哲理。
不知怎么,我原来想说的一肚子话全没了头绪,就想平静地过几天这样的日子。
我有时陪母亲上街,有当地妇女和母亲热情地打招呼,看到我这个外地人,自然要打听一番。然后是四川人那种辣泼泼的女高音:
“啊唷,这是你在北京工作的儿子!长的真像你嘛,蛮好的嘛!”
她们啧啧称赞,母亲平静地笑着。
母亲还不到六十岁,已显得有几分苍老,两只手因劳作而粗糙有力,干起活来麻利,家里收拾得干净而有条理。
对于过去那段伤心的往事,母亲简直是不忍回顾。
“我是要带你走的,你爷爷不肯。”母亲对我说;像是解释,又像是懊悔。
“你奶奶心肠好,是要留我。”
我问母亲为什么要走。
“你爸爸脾气不好,回南京经常打我…,我受不了…”她说不下去了,似有无限的苦痛。
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我命苦…,我命苦…。”她深深地叹口气,表情又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母亲痛苦的样子,我不忍心再追问离异的详情。
小时候,每当受到委屈,我想念母亲,也记恨母亲。怪她为什么不把我带走,怪她为什么不来找我。但脑子里“亲妈”的形象是个空白,连记恨都空泛而没有目标,后来就慢慢地淡忘了。现在,我理解了母亲;母亲的心比我的心更为痛苦。
母亲说,回了四川之后,开始把姐姐放在外婆家,在茶厂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因茶厂离家太远,为了照顾姐姐,索性辞去工作,靠打短工供养姐姐。母亲含辛茹苦,供养幼年失怙的姐姐上了大学;直到姐姐邮电大学毕业,生活才有所好转。几年前姐姐成了家,姐夫也是四川人,现在“南京华东工程学院”工作,是大学教师。
后来,是姐姐向我叙述了母亲多难的身世。
母亲生在四川农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年轻时到重庆“茶专”就学,毕业的那年,家境不好,为了还债,被迫嫁到了一个财主家,给他们生病的儿子“冲喜”,那年母亲才十九岁。那个“病夫”最终还是撒手而去,留有一男。夫家以收房为名将母亲赶出门,儿子不让带走,母亲经历了第一次生离死别。
被赶走的母亲先是回到了娘家,后到重庆某茶厂当“品茶员”。在此期间,结识了独自一人在“国统区”讨生活的父亲;这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父亲二十一岁,母亲大他四岁,二十五岁。
父亲是明白知道母亲的寡居身份的,因为他也对我说过,母亲曾嫁“反动家庭”,似有不屑之意。那么,既然是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结合,又为何“氓之蚩蚩”在先,“二三其德”在后,如《诗经&;#8226;危X》所讽:
乃如之人也,
怀婚姻也。
大无信也,
不知命也!(注)
姐姐是四四年出世,四五年有了我。以为找到了人生归宿的母亲,没承想面临命运的第二次打击。
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拉家带口回到南京。此时,吕家有女初长成,一十八岁曾相识。年轻漂亮的表妹使父亲觉悟起了“革命”精神,视妻子﹑子女﹑乃至爷爷和奶奶均为“革命”之障碍。母亲与小她十岁的现任“妈妈”有无直接冲突我不知道,但母亲之所以离去,一定是到了某种无法挽回的地步,是为了维护起码的自尊不得不做出的痛苦抉择。
然后父亲就带着他的表妹去了解放区。拉“革命”之大旗,做悖人伦之事,好不快活;把“别人”的痛苦,通通抛之脑后。
就在我来四川之前,爸爸还这样解释他们的离异:
“你妈是地主出身,就认钱。嫌我穷,整天和我吵,骂我是穷鬼,后来就带着你姐姐走了…”
我看过爸爸年轻时的照片,西服革履;论出身和家境,怎么也算不上是个无产者,自封“穷鬼”显然可笑。再说,爸爸其时二十五岁,可母亲已二十九岁,谁能相信,已然年近三十还带着一个幼女的母亲,离开“穷鬼”是为了再找一个“富翁”。
很显然,是这个“穷鬼”在撒谎。
撒谎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他们)并不光彩的行为。
遭遇两次不幸婚姻的母亲,不敢再尝试婚姻;但母亲敢于面对生活,于艰苦卓绝之中,把女儿养育成人。和她们短暂相处,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勤奋和志气。
有这样的好母亲,姐姐是幸运的。
相比之下,我没有姐姐幸运。
半个多月很快过去,我该回去了。
告别了母亲、姐姐和乖巧的小外甥女,我乘船顺流而下,到了涪陵。按姐姐说的,我购了去武汉的船票,下水船快,还可以欣赏长江三峡的美景。
因为“夜不过三峡”,船行到万县时停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航船在薄雾中驶向神秘的三峡。
船上的广播喇叭向旅客播送着景点的介绍,旅客全站到了甲板上,向两岸眺望。
三峡指的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船在峡谷中缓缓前行,两岸的山峰高耸,插入云中,如群龙不见首,忽隐忽现,迷迷朦朦。缠绕在诸峰之间的云纱千姿万态,一会儿矫似奔马在疾走,一会儿翩似惊鸿在轻飞,混茫之中使人意动心驰。
到了巫峡,神女十二峰更是气象不凡。那山峰和云雾在晨光的映射下,犹如九天神女现身;轻摆霓裳,便呈现出十二种妩媚,七十二种璀丽,令人神迷目眩。难怪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我正入神时,忽然觉得船前面的山也渐渐地近了;一扭头,只见客轮径直地向一座黑压压的山崖开了过去,而船头眼见得是三面环山,无处可行。正吃惊时,船已在山崖前掉头;峰回路转,眼前又是重峦叠嶂,水阔江平。
大自然真是一本奇书!这次渡乌江,过三峡,给予我心灵的感动,胜读十年书。正所谓“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刘禹锡有咏三峡的《竹枝词》几首,颇合我当时的心情: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青猿啼在最高枝。个里行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注:《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男子求婚时笑嘻嘻的样子;“二三其德”,指德行不一。
《诗经。啵纭N'蝀》篇,讽刺婚姻无德信。危X,音帝东,虹的别称,是爱情与婚姻的象征
八。“文革”体会
“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进行。
密云县的“文革”没有外地那种可怕的“武斗”,但“触及灵魂”的革命有时也让人的躯壳难以保全。
我在“密云师范”时,连续三年,每年有一个女生自杀;那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个还是在“文革”刚结束之后。
第一个自杀的女生姓柴,品学兼优,爱好文艺,而且容貌出众;被选为学生会文艺部的干部,还是发展入党的对象。“三夏”时,师生都下乡劳动,她和几个学生骨干留校,和工宣队军宣队的干部一起值班。三夏结束后我们刚返校,就得到她在家喝农药自杀的消息。
没有任何遗言,只听说那一天她给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
自杀的原因不明,公安局的人要验尸;她的母亲抱住死去的女儿不放,哭喊着说把她们娘儿俩一起拉走,公安局的人只好作罢。
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开会,校领导定调,工宣队军宣队的干部表态,说她是因为几次入党问题没有通过才自杀的,不要乱议论,干扰革命的大方向。
死了一个这么好的学生,教师们都十分痛心。她的班主任有一天上课时忽然失态,冒出一句:
“学习好有什么用,学习好的也死了!”
引得全班同学唏嘘不已。
我当时很不理解她母亲的所为,觉得验尸是能还她女儿以公道的唯一办法。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一位农民母亲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再说我们这些教师又做了什么,我们也不过是怯懦而沉默的看客。
另一个是毕业后自杀的,不是我教过的学生。她搞了个富农出身的对象,父母坚决不同意;为了纯洁贫下中农的血统,她父亲强令她与那个男子绝交,她一时想不开,就走上了绝路。
最后的那个学生我教过,是个沉默寡言的女生,在班上很不起眼。毕业后与同是小学教师的人搞对象,不谨慎,怀了孕。这在当时属“作风问题”,所在的学区让他们二人写检查,开大会批判。这女生回家,父母嫌她丢人,赶她走;她去对象家,对象的母亲也骂她,说她勾引了儿子。
这女生说不想活了,她的对象说两人一起死。于是买了两瓶农药,她是毫不犹豫地喝了,那个男的却犹豫了。对象的母亲连忙叫来生产队的拖拉机,大呼小叫:“快拉走哇,死哪儿也别死在我们家里!”
没等拉到卫生院她就死了,尸体送到了火葬场,她的母亲到火葬场又哭又骂,临走时把她的外衣脱下来拿走。可怜她是隆着肚子,穿着裤衩背心进的火化炉。
许多年过去了,每想到这三个逝去的年轻生命,我的心就不能平静。
是谁把她们推上了绝路?我们又能责怪谁呢?
她们都是有亲生母亲的人。
是什么压抑和扭曲了这些母亲的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