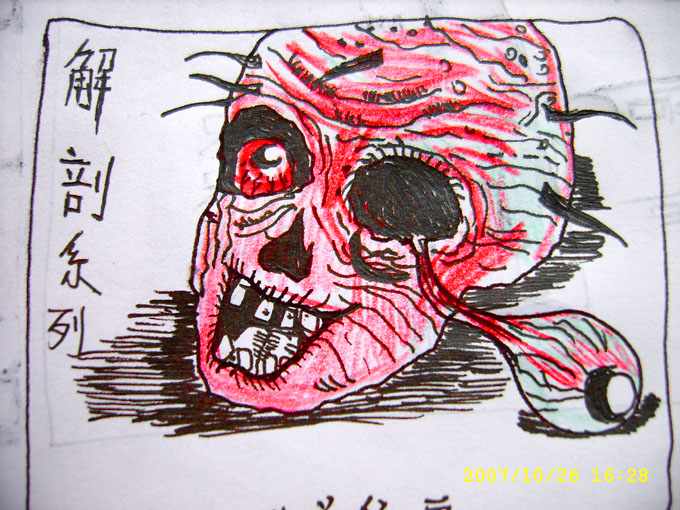年年年华-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学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监牢,凡是进来的人,都是用青春交换能够抵抗一切痛楚的麻木力量。
贺崇愚躺在草丛里,眼泪流下来,还没落到土地里就埋没入发际中,她依然是自己承接了这些眼泪,凉凉的感觉;她看着天空,心想生命难道真的就是一场这样的幻觉?城市里的水泥地,难道真的无法生长出爱的树木吗?孤单的人,难道真的注定柔弱吗?
卫嘉南的储物柜里虽然没有塞满垃圾,可是一直荒芜。自从贺崇愚下定决心以后,第一个礼拜天,她借了工具箱,一大早地穿着一身运动装,翻墙跑到学校里,偷偷地拿了门房的钥匙打开教室门。把他储物柜缺少的钉子钉好。第二个礼拜天,她用爸爸给她刷墙用的蓝色油漆,把那个储物柜重新粉刷了一遍,浅浅的天蓝色,让它在一排灰色的储物柜中看起来明显得不得了。
刷好了,再把写着卫嘉南三个字的名牌工工整整地贴上去。
第三个礼拜天,她藏了几块木板,先在柜子里的两面竖立的壁上钉上两个长条的木块,然后再把一块量好尺寸的木板架在上面,将储物柜分割成上下两层。上面可以给他放书本,下面可以给他放衣物,这样一来就方便了很多。每个礼拜一,她都会很注意他的反应,是不是不喜欢这样的布置。他的储物柜突然发生变化,在他们班的学生里引起过轩然大波,可是这样的风波好像一点儿也没波及到他本人。他很自然地开始使用储物柜,就像一直在用那么自然。
不过不到一个月,贺崇愚发现他有个不好的习惯,一旦换了衣服,钥匙必然遗落。看到他站在储物柜前摸了半天身上也一无所获的表情,让她觉得他也是个有孩子情绪的人;于是她又多配了几把钥匙放在他抽屉里,压在饭盒底下。一旦发现那里没有钥匙了,就补上一把,以免耽误他上课。
通过日记,她发觉自己一个学期里,一共配了七把钥匙。
她的苏依可真是个健忘的人。
于是他没有去追究是谁粉刷了他的柜子,她则继续通过新的方式,去给予他更多更多,不管是哪一方面。
她发现他喜欢吃荤菜,不喜欢蔬菜。学校食堂里供应的,又大多数是一荤三素,或者两荤三素。而且连鸡蛋都用来充当算荤菜,至于素菜,豆腐黄瓜也照使,好几天都不换新花样。十四岁的他个子拔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她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从妈妈那里学会了一种可以将肉做成不会坏的咸肉冻,味道很好,又不怕坏。只要一蒸就可以像普通烧肉那么吃,不蒸也可以当成别有滋味的荤菜。她为这个发现高兴了好久,于是把做好的第一个成品迫不及待地放到他的储物柜里面去。
在他愿意吃的为数不多的蔬菜品种里,有一种青椒,属于甜椒。用葱,蒜,酱油,糖做调味料一起煲,做出来以后颜色是暗绿,有点儿焦,青椒皮皱皱的,她看他自己带过,吃的数量颇多。在她的家乡青椒都是用来切片做配料的,像这样直接单炒她还真的没见过,回去和妈妈一说,妈妈说这里的人是有这么吃的,可是她不觉得那样有什么好吃,她还是比较喜欢地道的家乡菜。
在贺崇愚的央求下妈妈烧了一次糖醋青椒,她一向怕辣,于是准备了大杯的凉水握在手里,怀着上断头台的决心用筷子夹了一个,闭着眼睛咬了一个青椒的小尖尖。妈妈不解地笑道:“既然怕辣何必点名要吃呢,真是……”
可是一点儿都不辣,还有些甜,有些涩,但是完全可以接受。就连那些小小的籽也烧软了,可以轻轻地咬破,鲜浓的汁在牙齿和舌头间打滚。她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种东西,啊呜一口吞掉剩余的部分,马上又夹了一个塞进嘴巴里大嚼特嚼,可是这一个不同,辣极了。她准备的一大杯凉水都不够喝,她眼泪汪汪地问妈妈:“这些青椒真的是一个品种吗?”
妈妈说:“当然。”
她说妈妈骗人,“那为什么有的辣,有的不辣?”
妈妈笑她,“因为有的老,有的嫩呗,这丫头。”
“嫩的比较不辣吗?”
“是啊,那些烧软了的,皮皱皱的,就是还没长起来的嫩青椒;皮光滑的,硬硬的,颜色亮的,就是老青椒,会很辣。”
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他碗里的青椒皮都很皱,想必是嫩的居多,嫩的不辣,又甜甜的,多汁,味道果然比较好!难怪他喜欢。贺崇愚缠着妈妈问有没有方法可以只挑选到嫩青椒。
“那个没办法,我也挑不出来啊。”妈妈说完,回头又去忙了。
星期天贺崇愚挽着菜篮子去菜市场,在每个青椒摊子前面停留,只挑选她认为嫩的青椒,无视小贩暗中的抗议,凑了三十来个。回家关在小厨房里,按照妈妈的方法,先把锅烧得滚热,不放油,把洗好的青椒倒下去煸炒,等到皮发皱,有一点点焦的时候捞起来,倒油,继续炒,快熟的时候,加作料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怎么样?”
妈妈说:“好吃,嗯,嫩。”
她看着那三十来个皮皱皱的,软软的小东西,小心翼翼地全部装入保鲜盒,汁特别多,为了怕洒出来,她特别包了两层保险纸。
“你全部都带吗?”
“是呀。”
“一个人怎么吃得了那么多,留点儿给我们当菜啊。”
“明天我再炒好了。”她心不在焉地答应着,裹好保鲜膜放进手提袋里面。
“这丫头,学会跟我们玩小心眼儿了。”
妈妈说着,回自己的屋子去了。
她笑了起来,她是会玩小心眼儿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心眼儿。她有多少秘密,全都记录在那本簿子里,除了她之外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带着那一盒子的糖醋青椒她早早地到学校,然后剥掉保鲜膜把它放进他的柜子里面。锁上门以后,她又去检查了一下他抽屉里的备用钥匙,嗯,非常好,还在。
中午的时候她看见他在吃那盒青椒,一个都没有扔掉,吃得干干净净。他还真是爱吃这个东西啊。贺崇愚笑了,端着自己的饭菜从他身边走过,坐在离他不近不远的一个角落里开始吃掉自己的鸡蛋豆腐。
十四岁的男生们开始变声,教室里时常响起公鸭般的声音,比如上课上到一半,老师提问,一个男生站起来,义正词严地正说到高潮,忽然嘎叽一个降调,把下面坐着的同学们笑得不得了。
贺崇愚一边笑,一边茫然地想起她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听过他这个时期的声音,他总是抿紧了唇,无论对谁,不是吗?!
她好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就是那种最最自然的,毫不掩饰的声音。
一旦兴起某个念头,似乎就很难压制下去。她不知道该如何去让他说话,并且得到他的声音。恰好这个时候学校里一部分人为了学习外语,开始使用随身听或复读机,一个可以录下声音,一个可以四十秒反复播放,贺崇愚再次得到了启示。
她从已经是高中生的表姐那里借了小采访机,答应好她一个礼拜后归还。塞进磁带后,她开始想问题并模拟表演。
“对不起,可以借一下你的笔记看吗?”
不好,他肯定会觉得她是故意为难,因为有目共睹,他从来不记笔记。
“对不起,我有一道题不会做,能借你的作业看看吗?”
这样也不行,干吗别的那么多尖子生不问,偏来问他?
贺崇愚设想了几个问题,都被自己在下一秒钟否决掉,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妥,她一边背单词,一边不时地幻想第二天可能发生的情景,连妈妈推门进来都浑然不觉。
“你们快开校运会了吧?我们学校都开过了。”
妈妈是另一所学校的老师,贺崇愚忽然想了起来。
对了,可以要他报名参加校运会运动项目。
贺崇愚乐得蹦起来,把妈妈吓了好大一跳。
“这丫头,是怎么了?”
“没什么,要开校运会了,我高兴,嘿嘿。”
贺崇愚亲亲妈妈,第二天跑到体育组去借了报名表来,挨着个来问同学。
“你报个什么吧,长跑好不好?”
她一个个地问下来,不时偷瞟两眼角落里的他,他没什么反应,依然埋头看自己的书。
终于把这一组的人都问光了,只剩下了他。她走到他的桌子前,拿着报名表忐忑不安地站定,手伸到裙子口袋里按下录音键,然后试探地问了句:“打扰一下……”
他顿了两秒,抬起头来直视着她,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没什么表情。
“你可以在校运会上报几个项目吗?”
他的目光落到她拿着的报名表上,于是无言地伸出手,要那张报名表看。
原以为他会说“可以”,或者“那,我试试吧”之类的话的贺崇愚,只好赶紧递过表格,心里有那么一丝失望。
他拿了一支笔,在手指间熟练地转着,笔尖和笔头不时敲击着桌子,发出“嘣嘣”的闷响声音,最后,他捏着笔,在“铅球”上画了一个勾,写上一个名字,然后就还给了她。
自始至终,他还是紧抿着嘴巴,一句话都没说。
她慢慢地拿回表格,看着他低下去的头和后颈窝,浅浅的发根,忽然有很多莫名的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心头。
在家里,她反复地放着那四十秒的录音,除了她的两句“打扰一下”,“你可以在校运会上报几个项目吗?”就是那单调的,重复的“嘣嘣”的闷响,仿佛这就是他的语言,与人交流的惟一方式。
他为什么连话都不愿意说一句,哪怕是一个单字的发音……她做了这么多,看了他这么久,不要说一句完整的话,就连一个字,一个发音都听不到。
眼泪流下来,咸咸的,凉凉的,没等落到地面,她又一次承接了所有的委屈。
擦掉腮上的眼泪,她取掉耳机,算了,至少有这“嘣嘣”的声……就当这是他说的话吧,也许,这比真的听他说话要好得多,她可不想听见课堂上那样的公鸭嗓子啊。
第三年、流年
题记:
贺崇愚又笑了,是非常会心的那种笑。她回过头去继续看小说,身后十分安静,好像没有人存在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回过头,看到他果然睡着了,呼吸十分均匀,手臂弯曲挡在脸上,遮住眼睛,一条腿弯曲,另一条腿翘在那条上面,十分嬉皮的睡姿。
她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在他们俩共处的画面里,总是有阳光。细腻的阳光,轻轻柔柔地吻着这个少年和总是凝望他的少女,小心地收敛起强烈得足以灼伤人皮肤的热度。
贺崇愚把书轻轻地盖在他的脸上,蹲在他的身边看着他,过了很久才悄悄站起来,揉揉发麻的腿脚。
曾经有一个上午,十五岁的她是那么专注地蹲在十五岁的他的身边,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观察过他……
到了第三年,他们又面临着一次升学。联考之后,学生会向学校发起了一个提案,邀请一些家长来和学生们一同参加联谊会,算是紧张之余的放松。学校同意之后,列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