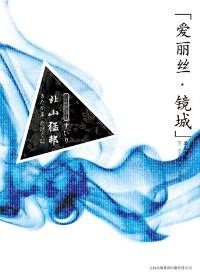青春裸奔事件:好梦不醒-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力民叔正躬身在禾场坪挖蚯蚓。他身边围着群嘎嘎的鸭子。力民叔是南瓜肚子,冬瓜腿,西瓜脸,瓜是枕头瓜。下巴上还长有一颗可恶的三角状黑痣,黑痣的中央竖一根弯弯曲曲的胡须。他提着鸭公嗓:里喇喇喇喇。没有一点要死的迹象。
我用手遮住鼻孔,呼呼的呼吸声此起彼伏,和心脏的跳动两相挥应,他们都让我害怕。我悄悄转过身,力民叔轻轻咳嗽了一声。我吓得拔腿就跑,鞋底咯响了几粒沙。
一慌,这条里弄和那条里弄长成了一样的形状,颜色也一样。我就经过了更多人家。各家各户的堂屋门口黑脑袋一簇一簇,在吃饭,在吹牛,在讨论什么,有一些话题他们争来争去也毫无结果。
我怀疑他们在讨论我。远远的听到我脚步声,他们都机械地把头甩过来,脖子伸长,脖子伸长是为了转过脑袋,好奇的打量我。我放慢脚步,眼神随着地表游动,他们的眼睛像灯笼,黑眼珠高高的突起,眼袋处挤出了皱纹。
有人问:“吉安胡子,下午做了什么?”
我说:“我在家里睡觉。”
经过另一户人家,又有人问:“吉安胡子,下午做了什么?”
我说:“我在家里睡觉。”
……
莫非,力民叔的鸭公嗓早已把我的贼名传遍整个村庄。否则,过去从未有人问过我这么多相同问题。
我愈加害怕了,怕得要死。不出几天,我的贼名势必传遍村庄的每个角落。从这个村庄传到那个村庄。到时候,山也知道,水也知道,树也知道,庄稼也知道,经常玩耍的晒谷坪也知道,每一条道路,每一间房屋都知道我是贼了。
到吃夜饭的时候,我却不敢回家。
找不到黑狗,我就爬上晒谷坪。我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石头白天裸露在阳光里,此刻正散着余热。温得我屁股很舒服。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坐着的确舒服,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贼。贼名独爱热闹的地方,喜欢钻进别人的眼睛。在自己眼里,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仍然一个样。见到有人,贼名就不再安分,它爬到我头顶,不停地跳,摇手。它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它,我也就从别人眼里看到我是贼了。但是一到无人之地,这种意识随即消失不见。
所以我特怕碰到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和我一般大的不怕,比我小的不怕,不认识的人,外国人就更不怕。
倏地,对面,三青家的晒谷坪,旁边的野草沟,扎着的那棵稻草树,旁边,顶上,有几户人家的灯火从那里射出来。空气暗的暗,明的明,一道一道。明与明的间隙,一个黑影钻出,微微一移身子,挪人明里。我定睛一瞧,南瓜肚子,冬瓜腿。我揉揉眼睛。发现还是力民叔。而且我发现的时候那身子已开始朝我移动。我吓得拔腿就跑。
1983年,自我呱呱坠地。我们村子的中央就是一条河,其实是一条臭水沟,就叫河吧!河道两迷宽,千米长,发源自一户人家的屋檐下,流入一口池塘。河两岸有石凳,是一些平滑的青石板,平是人为选择,滑是屁股功劳。河道虽窄,却未曾枯竭过。不过水流不大,水源是各家各户的的洗澡水,洗脚水,洗脸水,还有狗尿,牛尿,人尿。人尿是小孩屙的,他们憋了,就跑到河岸上,捉出小鸡鸡,对准河水哗啦啦的屙。
那一天,乘着夜色,是朦朦胧胧的夜。在这样的透明度里,河道有时像能更道。它看到我做贼,就微微移一下位置,躺到我脚板下。我一脚踏空,“啊”的一叫,“扑嗵”一响,摔进河水里。星星也跟着摔了进去,被一圈一圈的涟漪载着一漾一漾。河面上浮满了鸭毛。河水湿滑,温热,而且有几股侵入我嘴,咸的甜的,似乎还有苦的,已经没法辨认。淤泥想湮没我的身体,却被硬邦邦的河低撑住。我张大眼睛,岸壁的石罅里,黑黝黝的。你能想到的一切恐怖东西,都从那里探出头来。圆溜溜的脑袋;梭镖状的巫山鞭;阴气浓重的虎耳草,奇形怪状的露尸鬼,还有长脖子的女鬼……。。。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仿佛吞下个豹子胆。天上的月亮没吞,所以吓弓了腰。而且大气也不敢喘,而且把满夜的辉煌也泻出了肚,而且背靠着一朵笼着光边的剔透云朵惶悚。任凭众星星一齐围着它闪闪示威。显然一个胆小鬼。狗的咆哮随至踏来,伴随着一股冻骨的急风,小孩凄厉的叫声。连夜的静谧都开始窸窸窣窣地放肆,这声音在大白天惟有种胎死腹中。我一歪头,看到草从里有一条四脚蛇也爬了出来,四脚蛇是蜥蜴的俗称,平时捕食昆虫,现在在我的眼皮底下大口大口地嚼食月光。真要人命!
我惊恐的朝岸上望去,不见力民叔影子。
黑狗说:“哈崽,你跑干吗?”
我回过神来,朝他啐一口口水:“你娘卖拐的,我还以为是力民叔。”
黑狗拉着我的手,我一只手攀住岸上的石头,爬上去。
回到家里,爸妈没有打我,妈妈只骂我:“仔仔,怎么掉到河里去了。”大概,我做贼的事还没有传到他们耳里。
可是夜里,梦里,我梦到所有我认识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都站在我家屋旁的塘堤上,冲我大喊:抓贼!抓贼!声音仰天咆哮,似水牛长哞,似大炮轰鸣,似雷霆破空,一波盖过一波,毫无间隙,闪电般朝我劈来。我关上门,躲进被窝里,不行;就躲进柜子里,不行;就躲进地窖里。声音还是震耳欲聋。
而且力民叔的声音在这股声音中间,似笙管的声音超越众声而上,捉住我的耳朵。我以前只觉得他像如莱佛,如今梦里却是如莱佛。他的眼神像锥子,是鱼雷。鱼雷是用来对付军舰的,它不在海洋里游弋,却向我破空而来,要把我砸死。
我“啊”的一声,吓了醒来,身上汗津津的。
河岸上的家
大雨划过后的天空,不久后便渺无痕迹。惟有地面的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我从未听人说过这条河的名字。也不知道她途经多少村庄。只是她在罗子坝那一段我相当熟悉。不必说“S”形的流姿,夹岸簇生的芦苇,灯芯草从水里探出的小脑袋;不必说月儿弯弯的石拱桥,桥端的柳枝毵毵下垂,草熏风暖任人往来;不必说如梦静躺的渔船,渔人扣弦而歌,鸬鹚举头四下张望。单是那鼓噪的蛙声,和河畔的蝉鸣,我怀疑这鼓噪的蛙声,和河畔的蝉鸣,足够让整个夏季,沉睡不醒。
在黄昏,下午,在烈日化着柔阳的所有夏日。在石拱桥上,光着膀子的小毛孩用裤衩逗着鸡鸡,白花花的阳光擦洗着翠生生的屁股,纵身跃入河水。蛙式,仰式,自由式,蝶式,叫不出名字式,扎猛子个个擅长。闷一口气可游到十丈开外的渔船下,趁渔人低头小寐片刻,奋臂摇颤渔船,吓得鸬鹚扑棱直飞,头顶炊烟扬风而去。只是那竹枝体态的水蛇实在赅人,它尖塔的双唇撑开,猩红的舌头似摇荡的单摆,见有动静就鱼雷一样游弋于水面,细密的鳞片却牵动出鲜明的涟漪,黑晶晶的眼睛盯住人不放。所以我大抵埋伏在河岸远处的田埂下,青草做屏,蓝天当盖,用弹弓载着细小的石粒输去,弄得渔夫焦头烂额,方才罢休。
河道南岸有一个村庄。就是沿石拱桥南去有一条田塍相接的路,左拐,不远处是一栋低矮的土坯房。青黛的屋瓦裸露在天日里。堂屋的大门墙上,用石灰刷出一方长方形方块,上写有“人民公社大食堂”字样。一端的墙壁因为古老倾斜而开出一道岔来,风雪霜寒都能从这里吹将进去。檐鼠在这里夜游;壁虎在墙上赛跑;苍蝇的舞姿牵动蜘蛛的眼神。就是这样的房屋,随处可见的房屋,却能引来一村的孩子到这里神游。我们玩踢棍子,我们玩捉迷藏,这都是一个天然的好藏身之处。当瘦小的身子躲在门角,床底,猪栏顶上,经验再丰富的人也不易在黑暗里发现你。我童年的快乐在这里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永远不可磨灭。在我眼里,它是一个天大的游乐场——你可能不觉得它有多大,我也没觉得它有多大。但是在这里,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玩得肆无忌惮,从来不用惧怕爸妈的训斥会破空而至。多年以后的我呈现在我的记忆里,我横卧在猪栏顶上,那里堆满了金黄的稻草,我就卧在稻草堆里,稻草堆里撒满了乌黑干枯的老鼠屎,它们一粒粒暴露在我的视野里。我的身体就压在鼠粪上面。但是我不害怕它们。在那个年龄,它们根本引不起我一点畏敬。我的身体纹丝不动,任凭猪在栏里嗷嗷直叫,任凭我的伙伴(敌方)用棕榈树叶扳子敲打着猪栏的门框乱喊——我看到你啦!我知道他是在瞎猜,瞎猜。
多年以前,我住在这里,和它朝夕相处的亲密接触。多年以后,当我的记忆蒙上了一层细雾。我忘记了这栋房屋究竟朝向何方。朝东朝南朝西朝北,凭我微弱的记忆已经无从判断。我记不起来——东升的红日能不能在堂屋的中央洒下火红的光芒?我是否曾经站在这束光芒里,清亮的瞳仁为之闪亮。
我只记得屋前的禾场坪地面用煤屑灰铺就。中间有一棵参天的梧桐树,是鸟群栖驻的好地方。常来的麻雀居多,喜鹊偶见。有时飞来几只乌鸦。不过乌鸦的叫声阴森鬼魅,听人说那是不吉祥的预兆。记忆里的月亮总是升起来,禾场坪凉爽干净。白天破好的苇眉子堆在地上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矮凳上面,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们的怀里跳跃滑动。我们这些毛小孩,就在她们的四围跳跃乱蹿。
有一个老人,拖着或长或短的月光影子,手里提一根旱烟筒,光着赤膊,穿着短裤,脖子上挂一块侵水的手帕。另一只手握一把破败的蒲叶扇。在禾场坪逗一个圈子。看哪方有风,风大,便搬一把竹椅坐下。吧嗒吧嗒边抽烟,边给我们讲故事。他背后的伴奏是池塘的蛙声亩亩传来,和蝉的鼓噪,以及我们的懵懂发问。常常一个晚上,在他的嘴唇频频翕动间,一溜烟就跑掉了。在那个心未沾染更多东西的年龄,大人只要稍稍花点时间,我们的快乐便成倍增加。我们的心不甘年龄和现状的束缚,只要有机会,总渴望翱翔于未来和自己无法涉足的光怪陆离世界——而把眼前的一切彻底忘却。只注意到月落乌啼时分,眼皮乱颤,长脚蚊开始出来捣蛋。但老人还一副并不善罢甘休的样子。显得十分遗憾。
这便是我干爹了。
我不知道干爹为何待我那样好。也许是我喜欢他所以他就喜欢我,也许是他别无亲人的缘故,也许是我天性就千般可爱。可是可爱的我为何除他之外就别无其他人像他那样喜欢我。这问题曾经陪伴我度过好一段时光,依然不知其谜。不知其谜。我问过的所有人得到的答案都不足够让我信服。我的疑问似嘹亮的歌声遍村缠绕。
我怀疑。如果不是他佝偻的背无法支撑他的身体同我一起玩耍嬉戏,他绝对不会一味的只满足于用故事把我陶醉其中。大多时候,他翘着二郎腿。我就坐在他脚腕上。他脚腕上勾的弧线因为我重心的下垂而自然拉直。我只好爬到他大腿上。他的腮帮子鼓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