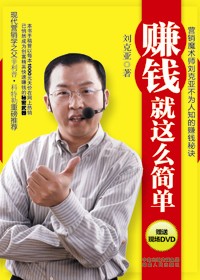就这么嫁给了他-第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雷教授(11)
“我很喜欢你的回答,教授,”母亲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不想干涉你们的事,我相信我女儿的眼光。我只有一个请求,请等到芙洛拉大学毕业后再谈婚论嫁。中国大学的校规普遍是不允许学生结婚的。你也在大学教书,我想你肯定不赞成哪个女学生为了结婚而放弃学业吧。”
“当然不,夫人。”
我看得出雷教授犹豫了一下,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15
饭后,我送父母去伦敦的酒店。其后几天我陪着二老或游览街景,或探望亲友。我们都没有提到雷教授,但越是这样,越说明父母不赞成,而我心里也越不安。
雷教授只打过一次电话,对我说圣诞快乐。
在伦敦我过了有生以来最忧郁的一个圣诞节。
父母逗留的最后一天,母亲去见几个老同学,我与父亲去酒店对面的Region公园散步。
父亲终于说,“小宓,那个雷教授看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青年,但作为父母,我们不得不多从现实的角度考虑问题。你觉得你真能同洋人一起生活吗?”
我默然。这正是我自己一直不能确定的地方。
“即使是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人,还是会与华人结婚。我也见过一些跟洋人的,可幸福的很少。因为结婚,共同生活,会涉及很多生活细节上的差异,这些细节差异,大到宗教信仰,子女教育,小到吃鸡蛋的方式,早上洗澡还是晚上洗澡,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你们的生活、情绪,进而影响彼此的感情。而且,这一过程跟发现对方有外遇不同,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它不提供一个可以将婚姻的失败归罪给对方的借口。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双方互相折磨的过程,一个让你对自己在过去一生中建立起来的生活信念产生怀疑的过程。这样一个失败的婚姻,会让人对婚姻本身失去信心,乃至对生活失去信心,对自己失去信心。”说着,父亲转向我,“小宓,你真的准备好过那样的生活了吗?”
我无言以对。一时间,我真的被父亲描述的情景镇住了。我从未想到过婚姻生活可能会变成那样,我一直以为现代婚姻应该是好聚好散的。
“另外,以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只能给你提供较为清贫的生活,住学校提供的宿舍,或在市区近郊买一栋小屋,养养花,种种草,可能还有一只狗两只猫。但即使这样的一间小屋仍需要有人照料,打扫,总得有人做这些事。当你的教授丈夫沉迷于他的研究中,也许你得承担起大部分甚至全部家务,洗衣服,煮饭,有了孩子也只能自己带。在Shopping Mall大打折时和其他主妇们挤在一起找便宜货,偶尔去一次饭店算是生活中的大事了。你来往的圈子将是其他整日操劳的教授太太,除了学校聚会你没有机会参加其他舞会。没过几年你就会变得和英国大多数家庭主妇一样了。”
我伸手几乎要捂住耳朵,但手在胸前停下,抱住双肩。
当时我们站在一个小山坡上。虽说是冬天,草坪仍是绿的,树木有些已枝叶凋零,有些却还郁郁葱葱。黄昏将至,远处的树和草迷离成一片灰绿色,尤显寂静苍凉。
“你真的愿意过这种生活吗?”父亲问。
“我不知道。也许事情并没有你说的那么糟。”我想起秦琪的话,“即使是,我也不愿想那么多。我爱这个人。难道你愿意我嫁一个我不爱的人吗?”
“女儿,相爱与相配并不矛盾。我希望你爱一个能让你幸福的人。退一步说,如果那小子是个华人,我愿意费点儿心思让他变得有能力娶你;可他是个洋人。他甚至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我希望至少在自家人里大家都能说中国话。难道你愿意在生活中一直讲英文而不是自己的母语吗?”
我抬起头看着父亲。虽然我并未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确实感到不便。
父亲看出了我的反应。“你再好好想想。至少找个黑头发黑眼睛能说中国话的。”
晚上,母亲回来,看到我的脸色,笑着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说,“怎么,被爸爸教训了?”
我撇了撇嘴。“他给我描述了很多恐怖的情景。”
母亲摇头笑道,“你爸爸把商场上谈判的那一套都用上了。我也猜得到他能说些什么,那些话其实并非夸张,对你也很有实际参考作用。如果你觉得自己都能应付,我不会反对你们的事。但是小宓,你真的爱那个人吗?”
我的身体战栗了一下。“我想……是的。”
“你想?”母亲叹息般地笑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希望至少到你毕业后再考虑结婚的原因。我要等到你真的确定爱一个人,才能将你交给他。”
16
父母亲走了,我的心情并没有好转。父亲的话常常在我心里回响。我真的爱他吗?我真的愿意过那样的生活吗?
我从机场驱车来到雷教授的住处。
按了门铃,没人回应,我于是用他给我的钥匙开了门。
他正在后院弄花草。
看见我,他用手臂环了我一下,因为手上有泥。
“他们走了?”
“是的。”
“你还打算嫁我吗?”
“你还打算娶我吗?”
他笑了,是阴郁的笑,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那样的笑容。我害怕了。
雷教授(12)
“教授?”
他看了我很久。“你居然还在叫我教授。”
“对不起。”我说。
“还对我说对不起。”又是那阴郁的笑。
我说不出话,忽然感到十分委屈。所有我爱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折磨着我。泪珠大颗大颗滚落。
“不,不,不要哭。天哪,我爱你。我爱你。我想让你快乐的。”他不顾手上的泥,将我紧紧抱住。
我依偎着他,脸贴在他心口,他有力的心跳让我渐渐平静下来。我在心底叹了口气,至少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放开我后,他笑道,“你看,我把你名贵的大衣弄脏了。”
“啊,你在取笑我。”我假装生气,心里一点儿也不介意。我脱了大衣,借了他的夹克衫,同他一起在英伦冬日难得的暖日下,摆弄那些植物。
其后的一段日子,我们相处得十分甜蜜,似乎为了弥补前一阵的疏远。我甚至向他学习做三明治,同他一起去超市购物。然而我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我猜他也是这样。在超市里看见中老年洋妇,拖着肥胖的身躯,在狭长的走道中寻找打折物品。想起父亲的话,我不寒而栗。事实上,这些话一直幽灵般在我脑中游荡,驱之不去,以致后来我只要看见任何邋遢妇人,都会惧怕这是我未来的映像。
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在萦绕着淡淡忧郁的平静中过去了。
17
春假有一个月。我和秦琪都很高兴,因为国内的学校是没有春假的。秦琪利用这一假期周游欧洲大陆去了。她一个人去的。事先她曾问我有无兴趣,但也笑着说,“我想你舍不得雷教授的。”
我被她说得脸红。但我无法否认,毕竟我在英国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我和雷教授在湖区过了两周。第一周极为美妙,但是周末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插曲。
我们住在温德米尔湖畔的一家B&;B(编者注:bedandbreakfast的简称,一种旅馆)中。虽说是B&;B,但房间十分整洁舒适,旅店女主人也亲切却不饶舌。我们的房间窗户正对着湖,因为电话预定房间时,我们强调一定要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黄昏,坐在窗台上看着红日潜入金色的湖水,我感慨,“现在我知道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多么重要了。如果我去意大利旅行,我也一定会坚持要这样的房间的。”
“将来等我退休了,我希望能在这里买栋小屋,背山面湖。我们可以天天享受这样的美景。”
看着湖水,我心头忽然涌起一股乡愁。“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念上海。”
“你在想上海?”雷教授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我。
“是的,就刚才。”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儿心虚。在此时此地谈论上海,确实是太煞风景了。
“你是想家了吧?”
“我是很想家,但是,我也真的想念上海。也许你难以理解,我喜欢上海的生活。你真的一点儿也不愿考虑去上海工作吗?”
“在英国和上海之间,你更喜欢上海?”雷教授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着我。
“是的。”
他努力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我可以理解你喜欢上海,毕竟那是你的家乡。可是在A城住了大半年,你仍喜欢那个拥挤嘈杂脏乱不堪的城市,我实在不明白。”
我从窗台边跳了下来。“教授,”我说,“我喜欢热闹繁华的地方,而拥挤嘈杂脏乱不堪的上海对我来说恰恰够热闹。而A城,一个晚上八点以后店铺都关门,街上几乎看不到人的小城对于我来说未免太闷了。”
他看着我,默然无语。他的目光是冷静的,而我恨这冷静。
于是我不依不饶地又说,“我的品味就是这样差的。怎么样,你是否打算重新考虑一下你的求婚?”
如同平静的湖面上忽地打过一个闪电般,他眼中闪过一丝愤怒。“谢谢你的提醒,”他说,“我会考虑的。”
我一时下不来台,只得躲避。我来到街上,走过沿街鳞次栉比的B&;B和小酒馆,拐过弯,顺着坡面下到湖边。
日落以后,天色立时幽暗,白天美丽如蓝宝石般的湖水显出几分阴郁。站在湖边,我忽然明白了,我与雷教授之间是不可能的。父亲是对的,尽管他的话有失偏颇,但正好适用于我们的情形。雷教授像很多西方社会的人,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对中国,对中国人,始终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我忽然奇怪他究竟爱我什么。他爱我,是的,这毋庸置疑,不然他怎会暂时搁置他脑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和种族优越感,同我这黄肤的东方女子交往呢。可是,他怎么会爱上我?他又能爱我多久?我抱着手臂,心随着从湖面吹来的越来越冷的风,渐渐凉了。
那天在湖边站了太久,我着凉了。头一次经历洋感冒病毒,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晚回到房间,我就感到异常疲倦,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发现喉咙竟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其后我在床上躺了一周,雷教授体贴地照顾着我,但我很拘谨,已无法像对待情人一般对待他了。
有趣的是,我们都有随身带几本书的习惯。有时我靠着枕头看书,雷教授坐在窗边看书。我的头一直发沉,书上的英文字又印得很小,看不大进去。于是我开始常常想到秦琪,想她一个人不知到了哪里了。一个单身女子,虽说为人十分机敏,但终究是一个人。我担心着她,不由自责起来,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不知我下辈子还能不能活得心安。
这样过了一周,我感到渐渐恢复,便提议回去。他也需要为新学期做准备,于是我们离开了湖区。雷教授本来要把我带到伦敦,但是我执意不肯。
18
开学后又过了几天,秦琪回来了。我在教室碰见她,她像老外那样,给了我一个大熊抱。不仅她的肌肤在南欧的艳阳下镀了一层金,性情也仿佛沾染了南欧人的热情。
周末秦琪召集我和其他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