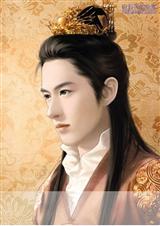丁香花-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也没有想到横波夫人出于君家。”龚定庵笑道,“真是巧不可言。”
“还是没有想想的好。”顾千里也很豁达,“想到了有忌讳,就没有这样的好词了。请往下念!”
于是龚定庵念下半阕:
“记得肠断江南,花飞两岸,老去才还尽;何不绛云楼下去,同礼穹天钟磐?青史闲看,红妆浅拜,回护五宗肯;漳江一传,心头蓦地来省。”
“结句好!真正是史笔。”顾千里说,“这首词,如果没有白牌,就不能这么好。”
“是啊!‘漳’字在牌中就没有。”
“‘漳江’指谁?”
“指黄石斋。”龚定庵说,“这个典故,出在余淡心的《板桥杂记》上。”
《板桥杂记》专记明末清初的秦淮风月,燕红料想这个典故与秦淮“旧院”有关,便不再问,要问的是另外几个不明白的典故。
“‘五万春花’指什么?”
“京师广和楼戏园,有一副长联,叫做:‘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五万春花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睡昆仑。’相传是龚芝麓所作。”
“‘绛云楼’是钱牧斋的藏书楼,我知道。”燕红又问,“‘同礼空王钟磬’作何解?”
“那是指柳如是。”
“这首词当中,有好几个故事在内。”顾千里为燕红解释,“龚芝麓进京,钱牧斋特为到江宁去送行,龚芝麓在秦淮河房张宴,名士美人,一时俱集,是有名的盛会。龚芝麓赋诗,‘杨柳花飞两岸春,行人愁似送行人”传诵遐迩。下半阕,‘记得肠断江南,花飞两岸’就是指这个故事。”
“龚芝麓的诗,确是好!‘行人愁似送行人’,是说送行的人舍不得他,他也舍不得离开送行的人。”说着,燕红别有意味,看了龚定庵一眼。
“也不光是如此。龚芝麓别有寄托,他是明朝的官,入仕清朝做了‘贰臣’,是迫不得已。这愁不尽是离愁,送行的人为他失节而愁,他自己为一世清名付之流水而愁。”
“不说他的失节,是因为顾眉生的缘故?”
“他说:‘我原要死,是小妾不肯。’那是托词。‘老去才还尽,何不绛云楼下,同礼空王钟磐?’就是说这件事。钱牧斋跟柳如是在绛云楼下,设佛堂同礼空王;龚芝麓与顾眉生,亦可如此。‘老去才还尽’是不忍说他失节,只说才气已尽,就做官亦不能起什么作用,这是定庵的恕词。”
“那么‘青史闲看,红妆浅拜’,就是指顾眉生了?”
“是的。”
“‘回护吾宗肯’呢?这个肯字怎么解?”
“肯就是‘惠然肯来’的肯,作可字解;不过句法是个问句,就变成‘我岂肯回护我的同宗龚芝麓?’”顾千里转眼问道,“定庵,我没有曲解吧?”
“是的。不过要跟下两句合看。”
“不错。”顾千里说,“下两句是说明不肯回护龚芝麓的原因。‘漳江一传’指明史黄道周传,他就是黄石斋,福建漳浦人。为人刚方严冷,不畏权幸。相传他路过秦淮,有人要试试他是否真道学,把他灌醉了送上床,一觉醒来,‘软玉温香抱满怀’,黄石斋居然就是柳下惠。所谓‘心头蓦地来省’,意思是忽然想到黄石斋,拿他跟龚芝麓来比较,即令真的是‘我原要死,小妾不肯’,亦总由龚芝麓为美色所惑,如果是黄石斋就绝不至此。”顾千里再一次征询,“定庵,是这样吗?”
“多谢,多谢!”龚定庵笑道,“我这首词并不好,经你一解,倒仿佛很像个样子了。”
“好的是词旨温柔敦厚,言讽而婉,婉而能深。”顾千里说,“江左三大家,论学是钱牧斋,论才是吴梅村,论情深不能不推龚芝麓,他虽事新朝,照应了许多朋友、后辈,光一个陈其年就累得他半死,陈其年没有龚芝麓,他的《湖海词》哪里会有几千首之多。”
这一谈到顺康年间的文坛,可谈之事就多了,诗牌亦就没有再打下去,一直到开饭,方始打断了这个话题。
第三章
宝蓝湖绉的小棉袄
饭后顾千里告辞,龚定庵想到苏州还有几个好朋友未能晤面,特为挑灯写信致意,写到一半,忽然一阵似兰似麝的香味,飘到鼻端,抬眼看时,是燕红站在他身边。
她已经卸了妆,松松梳一条辫子,身上穿一件宝蓝湖绉的小棉袄,下面是散脚的玄色软缎夹裤;尽洗铅华,肤白如雪,一双丹凤眼,两弯入鬓的长眉,神闲气静地在看他写的信,不由得让龚定庵想到“秋水为神玉为骨”那句诗。
“你还要写多少时候?”她问。
“快了。”
“此刻二更还不到;你四更天才走,不如睡一会儿。”燕红又说,“我已经交代过了,到时候会来敲门,你睡着了也不要紧。”
“咱们一起躺着说说话。”
燕红点点头,先去铺床;龚定庵很快地将信写完,由燕红服侍着卸去外衣,并头睡下,同盖一床棉被,在枕上细语。
这时候她说的都是苏州话——苏州话有特殊的语气、语汇和语助词;腔调软中带脆,抑扬徐疾之间,有如莺啭,最难得的是,苏州话永远“年轻”,五六十岁的老妪闲聊家常,如果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每每错当做十七八的女郎在说话。
因此,太湖周遭各地的人,到苏州光裕社去学说书,先要学苏州话,像一匹生绢,千锤百炼,炼得其熟如绵,方算合格。生硬的苏州话,听了能令人毛骨悚然;北里中扬帮冒充苏帮,一开口便露马脚,“清倌人”黄熟梅子卖青,道是:“奴是的的刮刮的清水货噢!”这些话常为人当做开玩笑的材料。
燕红的苏州话,其实已经及格,但她总觉得不够地道,所以平时不肯说,如今罗帐昏灯,喁喁低诉时,苏州话不妨出口,当然龚定庵亦用苏州话交谈。
谈的是杨二,既怕他仗势欺人,又怕他利用山塘的姑娘说媒,纠缠不休。又谈她以后的生涯,打算摒绝箫管,好好在诗词上下些工夫。
“这一点,我不是扫你的兴,作诗填词,在你不过怡情适性,要想做得好,就要下苦工夫。只字不妥,寝食难安,你就老得快了!再说诗人所写之情,是惘惘不甘之情,这也不是福相。”龚定庵又说,“最近看到一部《绣像红楼梦》,宝玉的题词是一首《西江月》,开头两句叫做‘无故寻仇觅恨,有时如醉如狂’,你如果没有那么多秋怨、闺恨可写,而刻意要去找诗材,就会走火入魔,变成那种样子。”
燕红当然有些扫兴,但细想一想,却是好话,因而问说:“那总要有件事做,才能打发关起门来的日子。”
“写字。”龚定庵脱口说道,“我家妇女,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会写字的,写得最好的是我妹妹。”
“听说吉云夫人也写得很好。”
“她也不错。”
这一下,燕红生了好胜之心:“好,我也要把字练好了它,你到上海替我找些好帖寄来,别忘记。”
“不会。”
这自然是极难为怀的一刻,因此对薛太太所预备的丰盛的早饭,龚定庵颇有食不下咽之势,但禁不住她母女殷勤相劝,勉强吃了一碗鸭粥、半块油酥饼。其时阿兴与顾家派来的四名轿班,早已饱餐,点起明晃晃的灯笼,等他上轿,已有好一会,不能再留恋了。
等他站起身来,薛太太识趣,知道他们临分手时,或许还有些体己话要说,便先避了出去,顺手将门带上。果然,燕红执着龚定庵的手说:
“如果有好消息——啊,”燕红有些不安,“我不该说‘如果’,一定有好消息来,那是什么时候?”
“会试放榜,在四月十一,不过前一天就可以知道了。报子抢‘头报’,日夜赶路,大概半个月的工夫,报到江南。在四月底你一定有消息。”
“当然是好消息。不过——”燕红踌躇着。
“怎么,你有话说啊!”
“你放心去吧!”燕红忽然又变得放得开了,“一路上自己保重,只当游山玩水,潇潇洒洒,不必过于赶路。”
“我知道。”定庵说,“你也保重。”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上了轿,轿帘一放,门外即是天涯,龚定庵回忆着这宵的光景,不知不觉地作了一首《洞仙歌》,回到船上,剔亮了灯,把它写了下来;然后取出词谱,改正了几个不谐声律的字,命阿兴誊清了。写的是:
清斋灯火,已四更天气,吴语喁喁也嫌碎。喜新居静好,旧恨堪消。壶漏尽,侬待整帆行矣!从今梳洗罢,收拾筝箫,匀出工夫学书字,鸩鸟倘欺鸾,第一难防,须嘱咐,莺媒回避。只此际萧郎放心行,向水驿寻灯,山程倚辔。
“大少爷,”阿兴问道,“这里头的话,到底是燕红姑娘说的呢,还是大少爷你说的?”
“问得好,你倒有长进了。”龚定庵先嘉奖了一番,然后说道,“里头的话,也有我说的,也有燕红说的。”
“怪不得看起来不大清楚。”阿兴建议,“最好在题目上说明白。”
“言之有理。”龚定庵略想一想说,“题目就叫‘云缬鸾巢录别’。”
正在灯下为顾千里写信时,龚太太来了,月华捧着她的水烟袋跟在后面。
“娘还没有睡?”龚定庵急忙站起身来,扶着母亲在红丝绒的“安乐椅”上坐下。
龚太太叹口气。“为你的事,”她说,“哪里睡得着?”
龚定庵大为惶恐。“不晓得娘为什么事生我的气?”他急急问说。
龚太太向月华作了个手势,她便取根纸煤,在美孚油的洋灯上点燃了,连水烟袋一起交到龚太太手里,接着转身出“大少爷”的书房;临走时向龚定庵使个眼色,却又一扬眉,暗示他的秘密发作了。
“呼噜噜、呼噜噜”地,龚太太吸了两袋水烟,方始开口:“听说你结识了一个勾栏女子?”
“是的。”龚定庵坦然承认,“姓薛,名叫燕红,山西蒲州人,是薛稷之后。”
龚定庵第一次听说薛稷其人,还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唐朝人,曾封晋国公,书画皆有名于天下,宋徽宗的“瘦金体”,就是薛稷的书法化出来的。龚定庵为了妆点燕红,故意把薛稷抬了出来。
第三章
迫切期待的意味
“倒不是薛涛的本家?”
龚太太原是句讽刺的话,龚定庵却正好作文章。“她虽不是薛涛一家,不过也有相近的地方,好人家出身,有诗才。不过,”他加重语气说,“人品比薛涛来得高。”
“从何见得?”
“‘王侯门第非侬宅,剩可五湖同去’,她一心只想从良,不像薛涛那样历事西川。”
“她从良,是要跟你?”
“是。”
“她怎么说?”
“‘便千万商量,千万依分付。’”
“你在念的什么?”龚太太微有愠色。
“喔,”龚定庵陪笑说道,“是燕红的一首《摸鱼儿》。娘,要不要看看她写的字?”
“我不要看。”龚太太凛然拒绝,“这种人最会混水摸鱼,你小心上钩。”
一语刚终,窗外“噗哧”一声在笑,当然是月华,这一下,龚太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