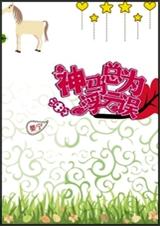浮云-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等人类经典表演,理论联系实际,我就有了收获:首先,确定了老马说的是实在话,人的价值和意义,确实要放到群体中才能体现出来。咱们设想一下,纵使一个人坚决与人民对立,满脑子“为党说话”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可他要是不入社会群体当官,或者把他扔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让他自生自灭,他脑子里的那点东西,自然就没任何作用。其次,这个群体一定是人的群体,而不能是其它动物植物。因为当他瞪着眼睛指责花草树木或狼豺虎豹“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时,这些玩艺绝对没可能如他期望般地尿他,被撕成碎片,倒是有可能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了有社会意义,我义不容辞地就加入了群体。
群体是被量化的,一个人不是群体,两个人也不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才能叫做群体。群体之中,人也不同,有朋友,也有敌人;有权贵,也有平民。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人都喜欢和趣味相投的同类在一起,这就在大群体里形成了小群体,这个小群体,俗称“朋友圈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009 绰号源远流长
我的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叫作“老狗”。
很多红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听到我这么说,经常会以为我是“关爱、保护动物协会”或者是类似此类机构的成员。他们的理解是:可能在某年某月某日,小三子突然爱心大发,从街上捡回来了一条奄奄一息的、行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流浪狗,然后,以朋友的身份善待之、关爱之,喂其牛排喂其奶,并准备替它隆重养老送终。洋鬼子们把这种仁慈的基督思想用在我身上,实在有点操蛋。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们都误会了,我根本就没修炼到满大街走着叫花子却去善待畜生的崇高境界,除了想吃肉,我从不愿意和圈养的禽兽们打交道,更不会像如今某些阔小姐、阔太太们那样,或杏眼圆睁或柳眉倒竖、或和蔼可亲或仁慈善良地把为她服务的保姆哄进地下室,然后对赖皮狗们、波斯猫们甚至小猴、小猪、小鸡之类的扁毛畜生展现出春天般的温暖,把它们当成比亲生孩子、乃至比亲夫还重要的家庭成员,一口一个“小亲亲”啊、“乖心肝”啊地温柔呼唤,并与它们亲密无间、同床共眠。郑重说明一下:“老狗”不是狗,它只是一个人的绰号,就如某些同志被别人叫作“猫三”、“狗四”或者“王八蛋”一样,猫不是真猫,王八蛋也不是真王八蛋,仅此而已。
绰号是个很常见的东西,这玩艺不仅中西贯通,而且历史十分悠久。据某些同志们吃饱饭后考证:在天朝,绰号最早见于汉代,如严延年、郅都、董宣等仁兄,由于他们用法严酷,世人便分别称之为“屠伯”、“苍鹰”、“卧虎”。
由此可见,给人取绰号,不是一件空穴来风的事,你得“由于”点什么。一般来说,其依据,大致上是一个人的体征外貌或个人习性。体征外貌很直观,取这类绰号,不用太耗费人的脑细胞,像身材胖的,直接可以叫作“某胖子”;个子高的,直接可以叫作“某长子”;稍微缺德一点,也不过是“大肥猪”、“细麻杆”,诸如此类。根据智商测试原理判断,给别人取这类绰号的人,文化素质一般都不怎么高,基本属于大老粗级别。但我个人认为,这种判断只普遍适用于至今还拿刀拿叉的那些不开化的西方老外,若用到咱们中国人身上,是大错特错。
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类似级别的大老粗,在咱们天朝数量是极少的。我不是吹牛,诸位不要忘记,小时候老师就很认真、很自豪地告诉过我们,咱们天朝是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照耀全宇宙。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耳濡目染之下;就算是只顽猴,也该学会沐冠了,何况是最高级的动物——人?因此,我经常毫不谦虚地对老外们说,天朝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文化素质想不比你们高都不行。经常气得他们直耸肩翻白眼。
文化无疑是个好东西。有句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可见连流氓沾上了文化,都会牛气很多。且不论别的,就拿给别人取绰号来说,文化素质高的人就显得与众不同。我跟你提一个人,不知你有没有久仰过,总之我是久仰过的。该同志姓施,大名耐庵,元至顺二年、也就是近七百年前的进士。所谓“进士”,套用今天的话,大致相当于全国统一高考加全国公务员招考联合考试被录取的佼佼者。考试成绩能这么好,无疑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你怀疑他考试作弊是没有依据的,这位有文化的仁兄已经写了一本书,现在被列入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书名叫《水浒传》,有空你可以认真拜读或随便翻阅一下。在这本书中,撇开那些鸡零狗碎的甲、乙、丙、丁们不算,单是盘踞在水泊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个反政府武装头脑,就被施兄一个不拉地全安上了绰号,且形象之逼真,不要说一般人能想得出,就是二般的,也未必能够胜任。
你若没有看过,我可以跟你介绍几个:
第一个:赤发鬼刘唐。
咱们天朝大汉子民都是蒙古人种,其特征之一,是满头黑发。可刘唐同志跟咱们不一样,他老兄满头红毛飘飘,还是纯天然的,与美发店里的化学品毛关系都没有,怎么洗都不掉色,简直帅呆了,酷毙了。鉴于该同志有很大的混血儿嫌疑,怨不得施兄这么称呼他:赤发鬼。赤发鬼者,红毛鬼子是也,还真是个外国人。要是搁在今天,铁定就是漂亮妹妹们你争我夺的火热对象。
第二个:矮脚虎王英。
王英同志比较不幸,可能得了侏儒病,也有可能是先天性遗传或者后天营养不良,总之,他老兄憋死了也不长个。也难怪,当年医疗、生活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也没有什么“增高鞋”、“增高药”、拉高手术等真真假假的所谓高科技玩艺可以帮他,加上施兄也可能比较损,喜欢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就让他和“行者”武松的哥哥“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并列。
直观的尚且如此形象逼真,以习性冠之的,就更不得了了。你看,“浪里白条”张顺:一个人居然能像飞在浪花里的白条子鱼,连鬼都知道此人必定是游泳高手,上奥运会没准就能为国争光拿块金牌回来;还有,“花和尚”鲁智深,一向戒律森严的和尚带着这个形容词,一听就知道该同志向来无组织无纪律,不拿规章制度当回事。
鉴于该书人物数量实在太多,我的目的又不是写《水浒人物绰号考》,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自施兄之后,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扬光大到现在,国人取绰号的水平,又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且不说脸上长点雀斑儿、麻子的,随随便便就成了“小数点专家”、满天星”;走路一瘸一拐的,成了“莲花摆、踏不平”,这些个已经太普通,实在不足为道。我有个小学同学,由于其父母积极响应本朝太祖“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号召,心甘情愿、满腔热血地被下放到了农村里,泽被所致,他也跟着去了农村上学。可是,到了农村没有多久,他就得了个绰号:公猪。由来很简单,只因该同学和我一样,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受军人的影响颇深,有点儿军人的习惯——你知道,军人为了行动利索,都习惯把衬衣束在裤腰带里。可是,我同学所居住的那个农村里,是没人有这种习惯的,他们习惯的是:用一根绳子系住公猪的腰,然后牵着它,到处去给母猪配种。
把皮带比作绳子,够绝吧?连农民兄弟都能玩出这么漂亮的水平,咱们天朝哪还有什么大老粗!
这种取绰号的方法,在语言学上,叫做“类比”。
010 让我起了怀疑
不过,我朋友“老狗”这一绰号,有点特别。因为其人无论是体征外貌或个人习性,都与任何犬类物种毫无相似之处:他不狂吠,不咬人,也没有尾巴可夹可摇。我曾从语文学、比较学等多个角度分析,居然一直都无法推测出该绰号的由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却有寻根探究的习惯。为了答疑解惑,我不耻下问,诚心诚意地向“老狗”请教。一开始这家伙还跟我卖关子,笑而不答,等我掐住他的脖子往他喉咙里灌酒时,他才终于开了口。他告诉我,原因十分简单,只因为他生肖属狗。
“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真他妈有创意,谁给你取的?”
“还能有谁?都是你们这些城里人呗!”他说他原本没有这个绰号,是在进入集团公司上班之后,才被同事给叫开的。
“老狗之前呢?之前你的绰号又是什么?”
“以前我没绰号。我们山里人,个个都实在得很,不像你们城里人,一肚子花花肠子,吃饱了没事干,动不动就给别人取绰号。”
“你就扯吧,怎么可能会没有?”我根本不信。
“不骗你,在我们地方上,都是谁家老大、谁家老二地叫。像我吧,我爹的名字叫郑奎,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大家就一直叫我郑奎家老二。要是在人少不会搞混的场合,直接叫我郑老二。”
“郑老二?这么说,你要是姓孔,岂不就是孔老二了?靠啊,鸟事没干成一桩,转眼倒变成了圣人,也太牛逼了点儿吧?”
“在我们村子里,哪会有人姓孔?再说了,孔老二有个啥牛逼的?我虽然不知道这家伙是哪里人,可也不是没听说过他。在我们村后山的斜坡上,到现在还刻着‘打倒孔老二’五个字呢!那字老大老大的,老远就能看见,自打我小时候起,就刻在上面了!”
“老狗”姓郑,这个我知道。我还知道,他们村子里的所有男人,统统都姓郑。“老狗”告诉过我,他们村是个族村,村民们个个打断骨头连着筋,每个人身上流淌的,都是同一个祖先的血。村名也反映了这点,他们村的名字,就叫作郑家村。
郑家村是个典型的小山村,而“老狗”,则是个典型的山里土著。他出生在大山间,生长于大山里,一直到了二十岁,也没离开过大山。
对于大山,我这个所谓的“城里人”,一直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很多文学作品里,只要一写到大山,作者就会按捺不住激动,开始尽情地抒情。比如“雄伟壮丽的大山啊,我魂牵梦系的伟大母亲!您以无比宽广无私的胸怀,哺育出了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再比如:“巍峨连绵的群山啊,生我养我的母亲!绿树是您的秀发,黄土是您的衣襟,您用甘甜的乳汁,抚育了我们!”。诸如此类的句子,实在数不胜数,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我时常沉浸在感染力如此之强的文字里,若还不能激起对大山的神往,简直没了天理。
不过,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的阅历不断丰富,我的思想开始渐渐地有了改变。
从死读书、读死书,到跳出书本放眼看世界,这是受教育者人生的一个基本过程。当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山民都毫不犹豫、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文人们所吟唱的曾经无私哺育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