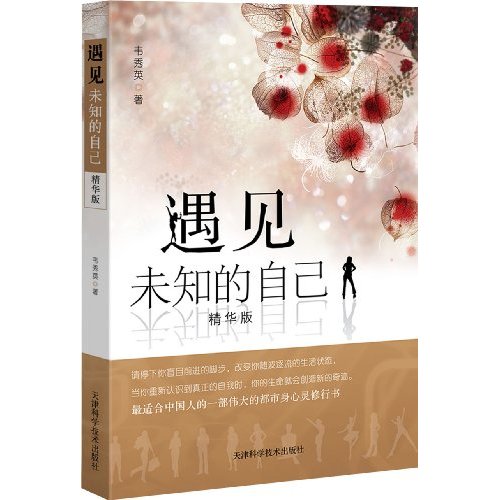自己的菩提树-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春风的吹拂下,有气无力地摇曳着那一丛丛弱不禁风的瘦弱身躯,随时入耳的是一阵阵低拂地面的“簌簌”声,此种情形,仿佛是那些生命已不复存在的苍枯衰草,在向我这个陌生人诉说着这方城墙故地的现世凄凉。
我一个人身感孤独的站立在这段古城墙脚下的寒风中,当自己亲眼注视着这段高低起伏、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古城墙残体,又低头俯视自己脚下所踏的这片让人心碎的凄凉之地时,这一切让我从内心深处悲痛的感受到,它与抬头所能望见的四周现代化的高大建筑,是多么的极不协调和格格不入,这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现在所站立的地方——是否是我们的首都北京之地。
我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瞅瞅时间,离与故乡学兄相见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那就多同古城墙相处一会儿吧!”我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对自己说道。位于离我所在地的不远处,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年青人,倚坐在这段古城墙北端的石质附栏上,手里随意的翻阅着一份报纸,看他那神情有几份的关注,时不时的还会偶尔抬起头来向古城墙望去,那样子像是在沉思着什么似的。我缓缓走上前去同他客气的打着招呼,并向他询问着关于这段古城墙的各种情况。年青人沉思片刻后用手习惯性的扶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随后声音低沉的指着古城墙告诉我说,这是明朝古城墙的遗存,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了。“这里所能看见的这独立的一段,是现存明朝古城墙中最衰败的一部分。”年青人见我十分关注的样子又补充着说道。这话他刚说完就站起身来合起了手中的报纸,伸手用手指指南边不远处的一座非常显眼的高大精致古建筑说,那就是整个明代古城墙的东南角楼。我顺着年青人手指指引的方向遥遥望去,一座高大雄伟的中国传统式古楼阁建筑矗立在不大远处的阴沉天空下,尽管天公今天有几分的不作美,但暂时的阴沉却掩饰不住那高大雄伟角楼的庄重身资。站立于此地远观那东南角楼可谓飞檐峭壁,棱沿重叠,“凹凸”字型的防卫墙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各个角楼的侧面上,都规正有序的布设有大小相同的防御射箭垛口,整个东南角楼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处处都显示着我国古建的精、奇、绝、美等民族特征;数只灰白相间的鸽子展翅盘旋于整座角楼的上空,声声“咕咕”的鸣吟,更是别有悠扬古幽之风韵;那防卫墙之上,数面安插于内的鲜艳红旗,在性格嬗变的春天风姑娘的吹拂下迎风招展,让人观之大有“战旗招展助军威”之气势。眼前的此情此景,使我的耳边仿佛有那震耳欲聋的百万雄师的呐喊声和滚滚如雷的战鼓声,此时我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了——古时那金戈铁马两军威武对阵的宏大场景。
那会儿站着向我指引东南角楼的年青人,仿佛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事,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手机,用拇指在晶莹的数码键上熟练的按动了起来。我没有再打扰的同他搭话,而是自己一个人默不作声的向眼下这段衰败的古城墙根走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心中微微一颤,一种想同这段古城墙更亲近些的想法便油然而生,这时候我又似乎感觉到那种冥冥之中的神奇力量,又在向我做出神秘的召唤了。
顺着这段古城墙的北端循步向前,我张开的右手亲密无间的触摸着层层重叠的古城墙墙体,这些构筑了古城墙雄伟墙体的一块块古砖分子,其体积和重量都要比民间传统的手工古砖大得多。循着上下一行行错落有致的古城墙大砖看去,它们所构成的几何图形,给人以厚重古朴之美感。在我肉眼所能看到的古城墙的正侧面,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风化和诸多历史事件的人为破坏,它现在所呈现给人们的是自身已经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残缺墙体。有些时候,我甚至不忍心也不愿意直视这段高低起伏、千疮百孔的古城墙墙体,尤其是看到它那赤裸裸的“内脏”暴露在外的时候,我尚不太麻木的内心深处,时时都能感觉到处于如此厄境中的古城墙,在向我悲痛的诉说着自己惨遭不幸的血泪史。每当此时,我的内心深处总是隐隐的感到有种痛彻心肺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自己真的是有些杞人忧天了。顺着古城墙根循行的脚步,不知什么原因无论怎样都快步的迈不起来,地面上的脚步时行时停,所行的是这里高低起伏崎岖不平的难行路,停的原因是心中时时涌现出关于这段古城墙的沉重思绪。
当我的注意力沉溺于思绪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一个神秘乞丐的神秘出现,才把我从沉思中解救了出来。这个衣着褴褛双脚赤足,面部肮脏且带浮肿的男乞丐的言行举止,让我深深的感到吃惊。只见他双手合十脚步快捷的从我的身边悄然“漂”了过去,而且还是口中念念有辞,我仔细的听了,虽然他的声音有些低沉,但我还是能够听辩清楚的,让我更惊奇的是,他居然念叨的是同一句:“城墙,城墙,给我一块砖……”因想再听听他还念叨些什么,我也本能的加快了自己的脚步,紧随于这位神秘人物的身后。没有想到的是他却没有“漂”向很远,而是在这段古城墙第一个墩座的拐角处停了下来,接着便是盘腿打座坐在了满是脏乱垃圾的地面上,双手仍是合十的“修行”了起来,那种有些滑稽可笑的姿势倒是极像虔诚的佛教徒。我从他的身边轻盈的经过的时候,他居然“修行”得如同我不复存在一般,口中仍念念不忘的念着那像是佛教经文的“城墙,城墙,给我一块砖。”
我又向前行走了几步,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神秘的乞丐,他仍在静坐在那里做着属于他自己的“修行”。此时,我的脑海里就由不住的想,他为什么会反复的念叨那样的同一句话,大概是他看到古城墙正同他一样遭受着悲惨不幸的命运,而为这段同病相怜的古城墙做虔诚的命运祈祷吧!至于我这样的想象,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我又想不论是处于哪个方面的考虑,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很尊重眼前这位神秘人物的。在我看来,我们彼此之间只是生命的状态不同罢了,而对于这段衰败古城墙的情感感触,只是彼此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告别了神秘的“修行人”,绕过一个接一个的古城墙墩台,不知不知不觉间,竟到了这段古城墙的最南端。这里是该段古城墙与南边不大远处的东南角楼,间隔了几百米距离的断裂处。为什么在这里会有这样的断裂呢?据那一会儿看报纸的年青小伙子说,此处的断裂是清末政府为了修建京奉铁路,而不得不破坏当时整个古城墙的完整性。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是否可靠,还有待于我进一步的查阅相关资料证实,但就对于现在而言,这也许是比较可靠的答案吧!这段残缺古城墙南段的断裂处,纵横交错的硕大古砖参差不齐,错落的突现出极不规正的豁豁牙牙,给人以沧桑衰败之感。这里最显眼的是那完全暴露在外的古城墙“血肉”——敦厚宽博深砌的古城墙夯土。这有着数百年深厚历史沉淀的夯土,却有着异常的结实的身躯,这些无处不在的夯土,填充于整个古城墙古砖所构成的坚固内槽中,其厚度则是随古城墙的高度而定。迎面观之,无不被这古城墙的坚实“血肉”所折服。再留意的观察,这里断裂处的外围,被铁制的栏杆圈包了起来,我想这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故而设此用于禁止游人攀爬吧!略带寒意的春风,轻轻的拂过我的脸颊,我的身心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风中所裹带的缕缕春馨。尽管这里有着铁栏杆的外围,但我还是决定要攀爬上去,亲身与那敦厚深砌砖土相间的古城墙残体,进行心灵深处的人墙对语。
当人的思想有了某种动力的时候,身体也会随之而变得敏捷了起来。就这样我没有费吹灰之力,便顺利的翻过了栏杆爬向了这断裂处古城墙的顶端。站立于这段古城墙的最高处,我的眼前顿时心旷神怡的开阔了起来,低头俯视四周更能感觉到它的敦厚宽大,转身行走在被风雨风化了的夯土表层,脚下有一种自然软绵绵的感觉,如同初夏赤脚行走在绿意盎然的草坪中一般。这里古城墙顶端的纵横幅度之大,说他敦厚宽广一点儿也不夸大,我曾亲自渡步测量的结果是夯土横宽要高达20步之遥,就是古城墙里外砖砌的坚硬外壳部分也有6步之距,更别谈整个古城墙的纵长了。这样浩大的工程,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啊!诸如这样的疑问,我的内心深处无数次自己默默的问着自己。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仿佛涌现出了——昔日无数筑建古城墙的工匠,一声声齐心协力夯土打夯时的嘹亮号子声,还有那在烈日炎炎下,受巡工官兵监视下的汗流浃背的民工辛勤劳作的忙碌身影。正是他们用自己一点一滴的血汗,筑起了这在当时为防御外敌侵袭的坚固古城墙。这样看来,只有真正的劳动人民,才是推动整个人类历史的车轮前进的真正动力,无疑劳动人民更是承载伟大人类文明的人。
一阵春风又起,邻近古城墙的垂柳的柳枝随风飘动了起来,我用手轻轻的扶着这棵在春风中摇曳的柳树,无意中欣喜的发现,它飘动着的柳枝上有了几分新绿,我心中知道,又一个春天真正的来临了,但同时我又抬头遥望着这段衰败的古城墙,心中不由得又自己问自己——真正属于它的春天什么时候才会来临呢?
二零零七年仲春于北京水木清华园 。 想看书来
洪洞这个县
我在故乡山西洪洞,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我不敢说为故乡做了贡献,但我却庆幸自己,是这古老三晋名县大河中的一滴水珠。确实是这样,生我养我的地方,是在这个县称作南垣的乡下。它的一年四季,没有都市的喧嚣繁华,更没有车水马龙的如织人流,有的是勤劳朴实的乡亲,还有那让人费足了眼神儿,望也望不到边际的庄禾。
当我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受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的认识了各种农具——钎、镢、耙子、锄。这用作学问人的话来说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村外离泽源渠很近的下湿地,常年都有一片一片的泊水,夏天这里就会有成群结队的蝌蚪,尾巴一摆一摆地潜游在水里,我就常常站在旁边手扒着树干,一个人对着那泊水发许久的迷瞪,迷瞪这些带尾巴的小黑点,如何就能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蛤蟆,更迷瞪神奇的大自然创造生命的奇妙。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也是那泊水黑色精灵中的一只,恍惚里长出了前后腿,居然也成了“呱呱”乱叫的小青蛙。泊水四周的草丛里,潜藏着的蟋蟀们,拼了命咿咿呀呀地唱着这方大地的繁歌,仿佛是在提醒着忙碌的人们——它们在这大自然中的存在。我金色的童年,便在这恍惚的想象和蟋蟀们的繁唱中长大了。童年记忆中的故乡,便是幼稚的眼神所能望及的地方。
后来我稍稍长大,受了多年不识字苦的母亲,便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学堂。在学堂里,我和同去的天真无邪的伙伴们,每天像快乐的小鸟儿一样玩耍、学儿歌。那时侯,记忆颇深的儿歌,倒不是学堂里先生教的,而是在去学堂的路上,路过村东老井的附近,那里的槌布石上成天的坐着一位盲婆婆,盲婆婆的嘴里,总是有一句没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