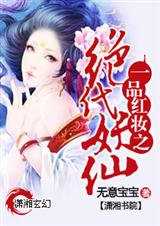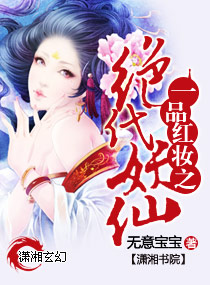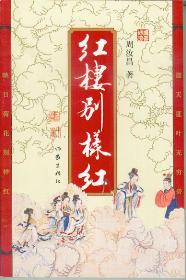周汝昌再品红楼:红楼别样红-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解其中味”,能解者即是脂砚,是女流。
——即此又确凿可证。
还有良证吗?
《甲戌本》正文刚出“还泪”之说,脂砚即批道:“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这是什么话?不就是讲解“谁解其中味”吗?
“还泪”二字方出,她就批示:“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
平儿之言“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诚哉斯言。妙极之!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两诗对应
上一篇《一诗两截》,揭橥几层妙谛。如今再续此篇相与发明辉映,以见“一芹一脂”配合的灵心慧性,晓示后人。
这第二首七律见于《庚辰本》之第二十一回前——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这诗也不难懂,但讲起来要多费话了。
先说当中两联,是与《甲戌本》那首的“两截”次序倒了前后。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首诗的中间两联,说的就是《甲戌本》上那首七律的“两感”内容,可是次序正好颠倒了一下。“是幻是真空历遍”,就是“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茜纱公子即以贾宝玉喻指作者雪芹;而“脂砚先生”之又即那位泪重的“红袖”女子——此女爱着红裳,故《红楼》总写她是“凭栏垂绛袖”,“红袖楼头夜倚栏”:这无第二位,总是专喻湘云之“红香”是也。
顺便一说:“红袖”对“情痴”,名为“借对”,因“情”内有“青”,故与“红”对。今此联又以“茜”与之为对,而此情痴(茜纱公子)又正喻指作者:君不见第二回即大书“情痴情种”之义,而第五回又大书“开辟鸿,谁为情种”乎!
勾连回互,妙谛无穷,人犹不语,则奈他何哉?“情不情兮奈我何”,是脂砚仿项羽的话:“虞兮虞兮奈若(你)何”之句法,“情不情”乃玉兄之评语也,故脂砚说:玉兄玉兄,你讲情讲得那么微妙,但不知你将如何为我下一个评语呢?——如何“处置”我的品格身份?
此诗即出脂砚之手,借一个“先生”字眼,蒙蔽世俗也,与“叟”略同耳。
重读海棠诗
第三十七回探春萌意、创建诗社,适逢贾芸送到海棠,遂以海棠名社。但此棠已非暮春的红妆绛袖,却是秋容缟袂。探、钗、宝、黛,各作了一首,然后湘云次日赶到,补作了二首。论者以为每人咏棠,皆寓自己的情境。这种见解对不对?窃谓还可重新讨究。
即以探春领头开篇的词意来看,借花写人,亦无自况之笔: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消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岂是探春的写照?结句“多情伴我咏黄昏”,是写他(她)而非写己甚明。再如黛玉的“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明是讥嘲刻薄别人,岂有如此“自寓”之理?馀可类推,不必备举。
那么,这六首七律,究应如何解读领会呢?
拙见以为:六首诗名以海棠为题,实皆咏叹湘云一人,湘云才是海棠社的“主题”。如此说,或有质疑,未必同意。何以解疑?关键只在宝玉那首诗,最是先要读懂。其诗云: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远笛送黄昏。
这首诗,就是字面咏海棠,句里咏湘云。但欲证此义,还须与香菱的第三次咏月之句合看——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
博得嫦娥应借问,何缘不使永团圆?
试看两诗,字字呼,句句应,一丝不走。影,冰之形也;魄,玉之魂。砧,两处相同;笛,双吟一致。晓风之愁何谓?即“鸡唱五更残”,宝、湘二人先后遭难,被迫分离,时在“晓风残月”之境况中。宿雨,又即菊花诗中“昨夜不期经雨活”之关联语也,谓湘云在苦难中幸获绝处更生。“独倚画栏”,正即“红袖楼头夜倚栏”,尚有何疑!?至结篇一句,“清砧远笛送黄昏”,则是嗟叹千里之外,遥念离人,惊秋砧而怀故旧;无以排遣,长笛抒念——而此笛声远为水上渔者所闻,因而牵动了宝、湘船上重逢的传奇悲喜剧——无一句是泛词虚设也。
于此,又会有问者:既然是咏湘云,怎么颈联却先出来“太真”“西子”二喻呢?岂非“文不对题”了?殊不知,这正是烘云托月、实宾虚主之手法。出浴杨妃,其影也;捧心西子,其神也。此正以钗、黛二人旁衬湘云,亦即正是“兼美”一义的点睛之笔了。如果拘看了那两句,以为是写钗咏黛,那么下面的倚栏砧笛,就无一字贴切了。
这个关键若已明白,则“胭脂洗出”等句,唯有湘云足以当之,一通百通,无复滞碍。此外也只有黛玉的“偷来梨蕊”、“借得梅花”是取笑、讥诮湘云的语调,更无别解可言了。
读懂了宝玉的诗,则探、钗、黛三人的诗亦即可解。综合其要害之句意,计有以下令人震动的“隐”迹可寻——
第一,湘云落难之后,为保自己的节操,不为邪恶所辱,曾将衣服密缝,不可解卸,证据是“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黛)。其次“莫谓缟仙能羽化”(探),也半露此情。
第二,她以节操的纯洁作为答报宝玉的真诚信誓,所以屡有“花因喜洁难寻偶”(湘)、“玉是精神难比洁”(探)、“欲偿白帝凭清洁”(钗)等句反复咏叹。而“缝缟袂”正是为保身的手段。
第三,她是死里逃生——死而复苏的幸存者。“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钗),明写湘云在难中拒施脂粉,欲图自尽,而幸被救活:“招魂”(钗)、“羽化”(探)二处语义最显。
第四,此可与菊花诗之“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犹喜带霜开”(宝)合看,语义尤为显明。是以,此处又云“苔翠盈铺雨后盆”(探)、“宿雨还添泪一痕”(宝)。两诗呼应,皆非泛设闲文。
第五,湘云在难中是被幽囚在一楼阁里,故有“独倚画栏如有意”(宝),“倦倚西风夜已昏”(黛)之句。
然后,再看湘云自咏的二首,那就更为意趣隐耀、处处照应的妙笔了。“自是孀娥偏耐冷,非关倩女亦离魂”——曾一度死去,“离魂”与“招魂”相对应也。“耐冷”与“喜洁”词异而义通也。
此外仍有二义可言:诗中屡有“默默”、“娇羞”、“不语”等句意,应是湘云于灾难中不屈之表现,即拒绝交谈,不出一语。与自缝缟袂为相应,坚毅自全,可钦可重。
至“蘅芷阶通薜萝门”之所指,分明是自言聚首大观园时寄居蘅芜苑,而日后播迁,竟至于郊西重会——即敦氏诗“薜萝门巷足烟霞”之雪芹山村隐处也。
红院无联却有联
宝玉展才,为大观园题联四副。令人感到有些奇异的是这四副联中只有三副是属于“四大处”的,即有凤来仪(潇湘馆)、浣葛山庄(稻香村)、蘅芷清芬(蘅芜苑),而怡红快绿名列“四大处”之内却独不曾题联。这是何故?雪芹处处有其笔法用意而常人不易窥破,亦不肯深思求解,遂成“疑案”。
也许有人认为:怡红院日后即成为宝玉的住处,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联之故也。这话也有道理——因为当时题联是为了给元妃看,要“应制”“颂圣”,这也无法双关自寓。
确乎这是一个难题,不易破解。但我又想,难解之点,还不止此。试一开列,请君细想——
一、“四大处”第一处最重要,匾曰“有凤来仪”,明指妃嫔之临幸无疑,可是联语却偏偏与匾与妃无关,两句话专扣“竹”之绿与凉,借茶、棋而托衬——都是消闲的泛常词义(并不“应制”)。
二、后来这“凤”居却成了黛玉的“茶”、“棋”之地。然而黛玉并不着棋,茶事也不是她的特征。(“茗烟”倒是宝玉的书童。)这都怎么讲?
三、再看四联中唯一“颂圣”的,是“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然此处却成了李纨之所居。那匾只是“杏帘在望”——是说酒店村肆。可谓“谁也不挨谁”。
四、及至为“清芬”题联了,则又特标“香艳”二字,与“应制”尤为违隔。“吟成蔻才犹艳,睡足荼梦也香”,这哪儿像“应制体”,简直太“离谱”——“大不敬”了!可是也未遭贾政的嗔斥。
这像是与宝钗暗暗关联吗?也不像!真是奇极了。说心里话,我至今还是不明白这些地方的笔意何在,深望高明大雅给我指点。
这样,只剩下宝玉面试的四联中的另一联:“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这是题“沁芳”溪亭的,故以“水”为关合之点。然上下句本是分属花柳红绿的,而“红”隐不露,以意会之即显。这样,也许就可以“代”题“怡红快绿”了——即可作怡红院之联了,故不再另题。此解妥否?
沁芳,实即“悼红”之变换美化婉语也,而有“红”则怡,失“红”则悼,二义相辅相成也。我觉这样解是可以“通”得过的。
面试而题的四联,有后补的没有?不得而详。只黛玉自言她补了许多,且舅舅都用了——这也大奇!从未听说贾政和她有什么话说,又怎么会采用她的题句之理?所以藕香榭那一联到底是谁撰的?竟不可知。但此联特由湘云口念,史太君耳聆——而恰好史家早先也有此型水榭“枕霞阁”!这儿“文章”就奥妙无穷了。
“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写竹桥”。芙蓉是荷花。“菱”、“藕”在书中又都有人名可关合:香菱,藕官。芙蓉又有木、水之分,如黛玉、晴雯的象征都是木芙蓉,秋花也,与荷莲非一。是以影破桨归,是夏日荷塘之情事。“藕”不指那白色根茎,是指荷花,古时说的“藕花”即荷花,是成语,不是“代词”。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衣,独上兰舟……”是联之上句所由来也。
诗曰:
四大题联却只三,沁芳花柳义须参。
藕香更待湘云诵,妙谛纷如五色蚕。
沁芳亭对联
因贾政命宝玉题咏园景,宝玉方得大展文才。以对联论,雪芹给他安排了四副:沁芳桥亭、有凤来仪、浣葛山庄、蘅芷清芬四处——独遗怡红快绿,不言有联。其前,宝玉所见秦氏屋中一联;又有尤氏正房联,与题园无涉,却于藕香榭又单出一联,由湘云念与史太君听。综观这些联文,我以为还是独推沁芳亭那一副,首屈一指,无与敌者。
这副联,大方,自如,文采,境界,可称四全,无一点儿堆垛纤巧气味。笔力振爽,对仗工致,无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