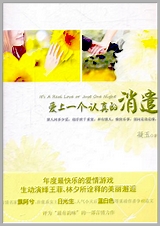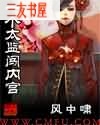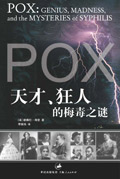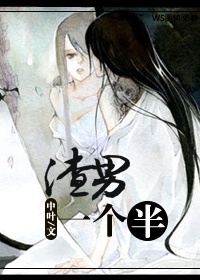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乃グ埽臀揖囊黄度缦吹幕牧共煌遥庾鞘衅鹚阑厣钠笠殉跸远四摺?斡嗉偃眨液屯С隽搜C牛ǔ4有∠镒哟┕ぷ徘嗵Γ乒显斜冢找艋锎隼吹呐蒙胄腥巳艏慈衾搿K罩菅趟午浚识玻彩е撩坪屠淝澹赖男稍黾恿苏庾鞘械亩小N叶潦榈拇笱В卸啻ε访婪绺竦慕ㄖ笱街獾男〗值郎弦擦阈巧⒙渥偶缸山烫眉把蠓浚庑┙ㄖ退罩菀还岬姆矍谨焱呒恍鳌5还茉跹液粑降氖蔷晌幕皇切挛幕钠ⅰ�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作家讲演。在一次系科召开的新生座谈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到我们学校讲演,如果远处的不行,能否邀请苏州的陆文夫老师和我们同学见见面?其他同学随即附议。主持会议的老师说,请陆文夫老师可以想想办法,外地的作家等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找机会。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和同学兴奋地期待着。
就像在乡下等待电影放映一样,我等待着路过的作家,等待在不远处的陆文夫从小巷深处走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一九八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停课到学校大礼堂听陈先生作学术报告《戏剧漫谈》。那时还不流行讲演一词,一九八一年三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苏州文化的了解,仅止于园林、刺绣、评弹和唐伯虎等常识,因为爱读小说,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以前有个叫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2)
苏州给我最初的印象破败而狭小。这座城市如同几个拼在一起的小城镇,砖瓦、小桥,甚至连流水都是旧的。它曾经繁华,但给人的观感有不少衰败杂乱的痕迹。我在前面说,这毕竟是繁华后的衰败,和我经历的一贫如洗的荒凉不同,而且,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气象已初显端倪。课余假日,我和同学出了学校门,通常从小巷子穿过,踏着青苔,绕过断垣残壁,收音机里传出来的琵琶声与行人若即若离。苏州烟水缥缈,朦胧而宁静,但也失之沉闷和冷清,评弹的旋律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动感。我读书的大学,有多处欧美风格的建筑,大学围墙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着几座旧教堂及洋房,这些建筑和苏州一贯的粉墙黛瓦极不协调。但不管怎样,我呼吸到的是旧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气息。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作家讲演。在一次系科召开的新生座谈会上,我提出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作家到我们学校讲演,如果远处的不行,能否邀请苏州的陆文夫老师和我们同学见见面?其他同学随即附议。主持会议的老师说,请陆文夫老师可以想想办法,外地的作家等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找机会。这样一个承诺让我和同学兴奋地期待着。
就像在乡下等待电影放映一样,我等待着路过的作家,等待在不远处的陆文夫从小巷深处走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一九八二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停课到学校大礼堂听陈先生作学术报告《戏剧漫谈》。那时还不流行讲演一词,海报和主持人都把此类讲演称为“学术报告”。陈白尘先生当时的身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陈先生从后台入场的方式很特别,他先是挥手,然后双手作揖走到台前,在持续的掌声中入座。陈先生是那种一讲话就能够给人震撼的作家,他的从容、大度和无拘无束都是我后来很少见到的。陈先生开场白云:我不怕讲错话,我也不怕有人给中央写信。他好像还说,有人写信了,但王震同志肯定我。他尚未进入主题,我们在下面就开始死劲鼓掌,会场气氛异常活跃。
在两个多小时的讲演中,陈白尘先生介绍了雾都重庆的“剧运”,又点评了新时期的戏剧创作情况,举重若轻,幽默风趣,不愧是一代讽刺剧作大家。当时的校刊新闻说,“他在谈到近年来的戏剧创作时,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党正确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剧坛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又严肃批评了文艺界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以及文艺领域里的其他一些不正常现象”。陈白尘是在二十多年前讲演的,他怎样歌颂又如何批评,我完全记不清楚了,记忆犹新的是他的气度与开场白。
人琴之戚(3)
八十年代初很少人有照相机,我也就毫无可能站在陈白尘先生边上合影了。我对陈先生的敬重,还源于我对他的散文集《云梦断忆》的喜爱。我在后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和《询问美文》的写作中,都把这本书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述的对象。陈白尘先生“*”期间曾在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干校放鸭,散文集《云梦断忆》记叙的就是他在向阳湖的生活。许多年以后,二三年的四月,我去向阳湖考察,还特地去了陈白尘先生在干校的旧居。十二日上午我先到原文化部干校总部,现在的向阳湖奶牛场。这地方设有“干校”生活展室,照片、实物均有,冯雪峰和郭小川的故居都在总部。随后去《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所在连队的住址。十里长堤,在雨中一片泥泞,这就是当年的“五七”大道,到“红旗桥”时雨更大,这座桥是当年“五七战士”自己所造。上工时,战士们举着红旗从这里过去。陈白尘先生所属的十三连在一个村子里。一进村,无数的狗在叫。墙上涂有“不期回报”的歌词。我找到陈白尘、绿原、李季的故居,商务馆的集体宿舍、食堂、阅览室等,都是红砖瓦房。陈的故居已有乡亲居住,屋里一群自由自在的鸡和鸭子在走动。我站在屋檐下拍了张照片,雨水顺着屋檐直下。我后来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大雨,返回。我听到了鸭子的叫声。这不是错觉,三五成群的鸭子,在田边,在湖中。看不到放鸭的人。当年那个在这里放鸭的剧作家陈白尘已经故去,这些鸭子大概也有些是他放养的鸭子的后代。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简单地用“伤痕”来形容陈白尘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而新时期文学却是从写“伤痕”开始的。说来也是凑巧,我大学毕业留校以后见到的第一个讲演作家是刘心武先生。在钟楼的外语系阶梯教室,刘心武作了《关于我国当代小说创作及其在国际文坛的影响》的讲演。会议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卜仲康教授主持的。我印象中,刘心武先生穿的夹克衫,讲演时的风度如同我们在后来的“百家讲坛”上见到的一样。听报告的人很多,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刘心武刚从联邦德国、法国等地访问回来,他的报告自然结合了域外的见闻与观感。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自己工作的笔记本中找到了当时听报告的记录。刘心武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引以为豪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但是,就小说创作,特别是当代小说创作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一定的距离,被国外翻译介绍的作品不多,在当代国际文坛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他还说,世界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绝不能自以为是,凭主观想象来臆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必须正视世界,正视生活,正视自己,冷静观察,深入思考。我们的作家必须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作一些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来。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梗概就这些了。
这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一月一日,苏州的秋日和往年一样美丽。而这一年,中国的文坛则是天翻地覆,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中国的小说“革命”了。
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出去,是一条叫十梓街的路,顺着这条路走五、六分钟的样子就靠近了陆文夫的住所。临近马路的苏州沧浪区实验小学南面,有一处在苏州已经算是很高的楼群,那里面有一套房子,住着陆文夫一家。——这个方位是一个熟悉陆文夫的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当然不可能贸然造访,倒希望有哪一天在马路上走的时候能邂逅散步中的陆文夫。我们见过他的照片,如果遇见,一定会认出他来。但这样的想法总是落空。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4)
终于有一天,我爬上了去陆文夫家的楼梯。一九八三年暑期开学后,我送一篇习作给我的老师范培松教授,请他指正。范老师说,我们一起去看陆文夫吧。我小心翼翼地跟在范老师的后面,敲开了陆文夫家的门。我当时非常慌张,在范老师和陆文夫交谈时,我站在客厅里东张西望,有两顶书橱,但书很少。桌上放着一盒香烟,是“琥珀”牌,这是当时很普通的香烟,我们同学偷偷地抽烟,常常是到后校门的小卖部买这种“琥珀”牌香烟。我大概除了叫一声“陆老师”外,没有说第二句话。等过了几年熟悉他之后,他因为患肺气肿已戒烟,而“琥珀”这个牌子也消失多年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陆文夫作品讨论会”在苏州召开。
我以为会见到高晓声,但他没有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