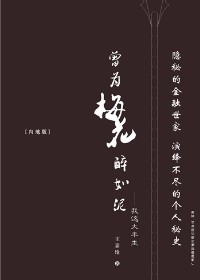曾为梅花醉如泥-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的,我同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仍不甘罢休,我会说:“你不要这么简单地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你要向我讲清楚你为什么会同意。”若是每个人都没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同意就“同意”,这样的“同意”是没有力量的;由没有力量的“同意”来决定要进行的事情,是很难成功的。
。 想看书来
飘飘然
东汉班固的《通幽赋》,有一句“北叟颇知其倚伏”的话,指的是《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的“塞翁失马”的寓言。那则寓言说,在靠近北方边塞的地方,住着一位老翁,他精通术数,善于卜算过去未来。有一次,老翁家的一匹马忽然挣脱羁绊,跑到胡人之境去了,邻居知道后都来安慰他。他平静地说:“这件事难道不是福吗?”过了几个月之后,那匹跑失了的马突然跑回了家,不仅自己回,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得知,都来向他道贺。老翁却淡然道:“这件事难道不是祸吗?”老翁的儿子生性好武,喜欢骑术,有一天他骑着那匹骏马到野外练习骑射,不小心从马上仰面摔了下来,成了残疾。邻居们听说后纷纷来慰问他。老翁不动声色地说:“这件事难道不是福吗?”又过了一年,胡人侵犯边境,四乡八邻的精壮男子都被征召入伍作战,死伤者不可胜计,唯独老翁的儿子因残疾没有被招当兵,从而得以保全性命。这则寓言,堪为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句名言当注脚。世事的确是祸福相倚、变幻无常的,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好事也可以变为坏事,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与“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我有极深的感受。
▲对“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与“塞翁得马,焉知非祸”的道理,我有极深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未到而立之年。那时的我,无论是生命还是事业,都处在蓬勃向上的阶段。在我的身体内,时常有一股激情在流淌。梁启超说:“少年人如朝阳,如乳虎,如铁路,如白兰地酒,如春前之草,如长江之初发源。”这句话在当时很能引起我的共鸣。在香港司法部,我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由于我的英文才能被发现,我由一名三级文员被提拔为暂委翻译官。这个职位,原本是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人才能担任的。当时我的同事,便都是香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我被破格提拔,不是说明了自己在上司的眼中,已具有与他们对等的实力么?更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是,我担任暂委翻译官还没有多久,又被正式提拔为翻译主任。仕履的一帆风顺,使我深信自己未来必像“朝阳”、“乳虎”、“铁路”、“白兰地酒”、“春前之草”、“长江之源”一般,充满着无尽的活力与希望。可是后来的结果与我所曾经憧憬的完全相反。
我在司法部的地位提高之后,就有了出入上流社会的资格,平时经常与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往,诸如*官、大律师什么的。加上我与瑞芬结了婚,岳父家十分有钱,这一背景对我的身份也产生了很好的烘托。我常常不无炫耀地领着司法部的同事,到内子家的别墅去开派对,对着风景旖旎的海滨逍遥自在地喝上一杯。生活似乎到处都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实在是美好极了!我沉浸在陶醉之中,感到心满意足,于是飘飘然起来。
我担任翻译主任后不久,便奉调到荃湾法院工作。离开了司法部,来到荃湾,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司法部,我虽然对自己的“翻译主任”身份洋洋得意,但其实我在部里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实际上官位并没有多大。而到了荃湾法院,情况就不同了。我作为司法部下派的“官员”,多多少少显得有点“不同凡响”。这就好比你在京城做一个七品芝麻官,与人比品秩,谁都比你高;但如果你一旦外派,比如到一个县城当县令,你就会威风八面,因为周围的人谁都没有你官大,更何况你还是从朝廷上面下来的呢!在荃湾法院工作的我,就有点像这种芝麻官。在这里,一般人等对我固然点头哈腰,那些有头有脸的探长、高级警官对我也相当客气,见了我的面,总是态度很谦恭的。他们对我的抬举,强化了我原本就很良好的自我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举一个例子,有一段时期,我学开车,一位老练的司机当我的教练。因为我的驾驶技术尚不熟练,车开得歪歪扭扭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操控者是新手。有一次,车驶在一个路口,一位交通警察把我的车拦住,示意我出示驾驶执照;我见状慌了手脚——我正在学车,哪来的执照?我打开车窗,正想向他求情,想不到那位交通警察一见是我,便“叭——”地一声对我立正敬礼,连声说:“王Sir,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说完,马上跳上电单车,一溜烟走了。这件小事情,让我发现了自己在荃湾的“影响力”,于是越发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从此之后,我做起事情来胆子更大。那个时候的我,用“年轻气盛”来形容,是一点不为过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意迷神乱(1)
我当时的岳父是客家人。到荃湾法院工作后,我才知道原来荃湾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在这个地方,经营七十二行生意的,有许多都是客家人;在各种工场食肆干活的,也多是客家人。客家人有成群结队聚居的传统,他们在香港自成群体。他们的祖宗曾留下“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遗训,因此连所操的语言都与香港主流社会通用的粤语不同。我与瑞芬结婚后,越来越多的客家人知道我是法院有地位的职员,都把我看成了一个“人物”。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从事非法活动,便希望我能当他们的保护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整日围着我的屁股转,与我套近乎。他们吹我捧我,请我喝茶、饮酒、唱歌、打牌、听歌,让陪酒女郎伴我喝酒。逢年过节,送来的不是月饼火腿,便是靓茶美酒……总而言之,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日日欢娱、夜夜笙歌,没有一天是过得清静的。而我也热衷于被人吹捧,对这种浮华的生活乐此不疲,白天在法院里向各式人等耀武扬威,晚上则在酒家茶楼里与这些狐朋狗党们坐花琼宴,飞觞醉月,日子过得好不快活!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在这种令人心性迷乱的生活气氛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跟那些客家人混熟了之后,他们觉得有我这个在法院里“当官”的人做后台,做起事情就逐渐放肆了起来。而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就通过我岳父,要我出面“摆平”。而每当我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兴奋不已,不时在我岳父跟前称赞我这位“客家女婿”如何如何“精明能干”,何等何等“神通广大”。这些客家人,有一部分以开饭馆为业。其实他们所开的“饭馆”与其说是用餐之地,不如说是赌场之所。这些“饭馆”通常只在楼下供人用餐,而在楼上供人玩牌。客人们常常在那里打麻将、玩十三张,以此方式赌钱,主人则从中“抽水”。在香港,聚众赌博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这些客家人很放肆,屡受警告依旧我行我素。有一天,管理荃湾地方的片警将一个这样的“饭馆”端了窝,当场没收了场中的赌具与赌资。这些客家人便跑来找我帮忙。来人投诉说,他们一帮乡亲父老,其实只是在一块玩玩麻将、纸牌什么的,可是那些警察冲上来,不分青红皂白,便硬说他们是在“赌博”,竟然把他们的东西全收走了。听完他们投诉之后,我便考虑到底要不要出手帮他们。平心而论,若是不认识这些人,我一定会觉得他们被警察干涉是活该,可是人偏偏就是这么怪,只因与他们有了某种关系,我的判断便出现了偏差,觉得他们只是不走运。我当时想:他们不过就是玩玩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难道香港玩牌的人还少么?为何这些警察不去管别人,偏偏与他们较真。于是答应替他们去找警察局的人理论。
到了警察局,主管长官一见到我,便十分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说:“哎呀,王Sir,今天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啦?您怎会有空来找我们呀?”
我硬梆梆地说:“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谦卑地说:“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到你吗?”
我怒气冲冲地说:“你们也太不友善了,怎么把我的朋友的娱乐家当都没收走了呢?”
那位长官不无疑惑地说:“哪里哪里,王Sir您这话从何说起呢?请讲清楚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意迷神乱(2)
我说:“怎么不是呢,昨晚你的部下不是到街捉赌,把人家的窝都端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那位长官说,“那些人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我的朋友,可是他们比我的朋友还重要。他们是我岳父的朋友,也是老乡。你看你们这么做,让我多没面子呀。”
长官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他沉吟了一会,走进警察局的内屋。过了一会儿,就出来对我说:“不好意思,王Sir,东西您叫他们来拿走吧。不过回去您可得告诉您岳父的那些老乡们,以后不要再搞这些名堂了!”
我听后,向那位长官道了谢,便离开了警察局。回去以后,我告诉他们这件事已经摆平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并没有拿他们的任何报酬,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是通过什么方式途径把这些东西搞回来的。我当时只是觉得他们发生了问题,我作为“客家女婿”,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们一把,并没有想过要从中捞一把。当然,对他们违法聚赌之事,我也进行了不咸不淡的劝告,至于他们听还是不听,我就管不着了。
我能把已经被没收的钱物弄回,让那些客家人感到十分兴奋。在他们眼中,我太了不起了,简直就是他们的“保护神”。由于觉得有我做后台,那些客家人更加胆大妄为。没多久,他们又因抽鸦片烟而惹来了麻烦。这回不仅烟枪被没收,人也被带走了。按照香港的法律,如果你在同一地方放置有两杆烟枪,就相当于是开烟馆,会遭到法律的严厉追究;如果你在同一个地方只放置有一杆烟枪,那就属于私吸烟土,罪名并不大。这一回,他们被收走的烟枪虽然只有一杆,可是被带走的人有好几个,因此事情可大可小。听了他们讲述相关情况后,我决定去找荃湾区的扫毒组探长,我估计他会知道此事。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警察系统,说难听一点,差不多就是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华探长、黑道与洋警司互相勾结,警队的*超过任何一个机构。直至港督麦里浩于1974年设置廉政公署之后,香港的警务系统才逐步变得有个样子。客家人的上述案件发生时,廉政风暴已悄然兴起,那些探长们虽然还很有势力,但是他们已听到了某些风声。因为担心将来遭到追究,他们做起事情来已不像从前那么肆无忌惮。找到探长之后,我径直对他说:“我有个亲戚,并不是开烟馆的,只是在家中藏了一杆烟枪,你们怎么就把人家的东西没收了呢?而且还拉了好几个人。”
探长向我解释说:“王Sir,这件事嘛,真没您讲的那么简单。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确是只藏了一杆烟枪,可他们不是一个人抽,而是一个人抽完了,另外一个人又接着抽。他们这是在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