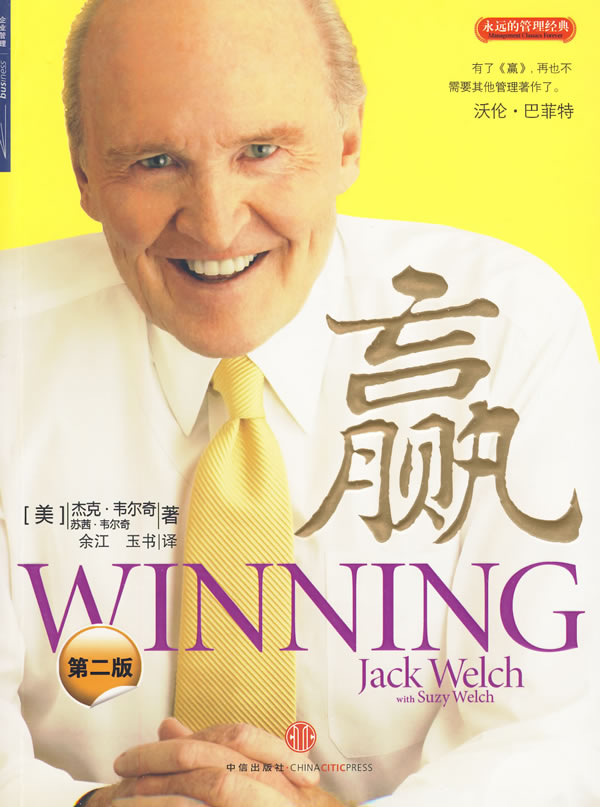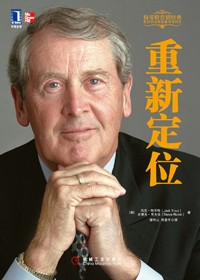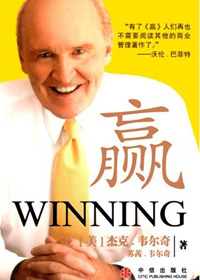弗兰克·迈考特-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听见了,迈考弗雷先生。
奥康纳太太紧抿着嘴,不看我一眼。她对巴里小姐说:我听说某个从巷子里出来的家伙自以为是,竟然躲开了邮局的考试。参加这个考试太委屈他了,我猜是。
你说得对,巴里小姐说。
与我们为伍也太委屈他了,我猜是。
你说得对。
你猜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参加考试吗?
啊,他可能会的,巴里小姐说,只要我们给他下跪。
我对她说:我想去美国,奥康纳太太。
你听见了吗,巴里小姐?
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奥康纳太太。
他开口了。
他开口了,的的确确。
他有一天会后悔的,巴里小姐。
他肯定会后悔的,奥康纳太太。
奥康纳太太说着话,从我面前走过去,走向那些坐在长凳上等电报的男孩子。这就是弗兰基。迈考特,认为自己在这个邮局干,太委屈了。
我没有这样认为,奥康纳太太。
谁叫你张嘴了,“自高自大”先生?他在我们当中也太出类拔萃了,不是吗,男孩们?
是,奥康纳太太。
我们好歹为他做了那么多。给他小费高的电报,天气好的时候派他去乡村;他对那个英国人哈灵顿先生干下那么不要脸的事情,我们还是让他回来了;他对不幸的哈灵顿太太的遗
体不敬,还自己塞饱火腿三明治,又喝了那么多雪利酒,东倒西歪的,最后从窗户跳出去,把玫瑰丛都毁了,回来的时候醉得一塌糊涂。谁还知道他送电报这两年都干了什么丑事?谁最清楚?尽管我们还知道一个大秘密,不是吗?巴里小姐?
是的,奥康纳太太,尽管它不适合公开讨论。
她对巴里小姐耳语着,她们都看着我,不停地摇头。
他是爱尔兰人和他那可怜母亲的耻辱,我希望她永远不要知道才好。但这家伙出生在美国,父亲又是北佬,你能对他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容忍了这一切,还是让他回来了。
她又从我面前走过,继续说着话,走向坐在长凳上的那帮男孩子。
他要为伊森斯工作,为都柏林那帮共济会成员和新教徒工作。邮局太委屈他了,但他却情愿满利默里克城去送各种淫秽的英国杂志。他每碰一次那种杂志,就是一次道德犯罪。但他现在要离开,他是要离开了,对她那可怜的母亲来说,这是个遗憾的日子,她祈祷儿子能有养老金,能照顾她以后的日子呢。好吧,来吧,拿走你的工资,从我们眼前消失。
巴里小姐说:他是个坏孩子,不是吗?男孩们?
是的,巴里小姐。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应该说对不起吗?应该说再见吗?
我把自己的皮绳和邮袋放到奥康纳太太的桌上,她瞪着我,说:走吧,去伊森斯那儿干你的工作吧,离开我们。下一个,来领你的电报。
他们都回去工作了,我走到楼下,走向我人生的下一站。
十六岁
我不明白奥康纳太太为什么要公开羞辱我,我并不认为自己在邮局干有多委屈或是别的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头发支棱,脓包满脸,红眼睛直冒黄水,烂牙东倒西歪,没有肩膀,骑了一万三千英里,在利默里克内外送了两万封电报,累得屁股上都不长肉,又会有什么能耐呢?
很久以前,奥康纳太太就说过,她清楚每一个电报童的所作所为。想必她也清楚我在卡
瑞戈古诺城堡顶上,当着目瞪口呆的挤奶女工和抬头张望的小男孩,跟自己干的那些事吧。
她一定清楚特丽莎。卡莫迪和绿沙发的事情,清楚我是怎样让她陷入罪恶深渊、把她送进地狱的。那是最严重的罪过,比卡瑞戈古诺城堡顶上的罪过严重一千倍。她也一定清楚特丽莎死后,我就没去忏悔,我是注定要下地狱的。
一个犯下如此罪过的人,是不会觉得在邮局干有多委屈,或别的什么的。
自从那次我同汉农、比尔。盖文和帕。基廷姨父坐在一起后,南方酒吧的伙计就记住我了———黑、白、黑。他还记得我父亲,记得他把薪水和失业救济金喝个精光,还高唱爱国歌曲,在码头上像个该死的叛徒似的演讲。
你想要什么?酒吧伙计问我。
我是来找帕。基廷姨父,来喝我第一杯啤酒的。
啊,天啊,是真的吗?他马上就来,当然,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给他倒酒呢?或许也该给你倒第一杯酒,这就倒吧?
不,先生。
帕姨父走进来,叫我挨着他坐在靠墙的地方。伙计拿来啤酒,帕姨父付了钱,举起酒杯,对酒吧里的人说:这是我外甥弗兰基。迈考特,我小姨子安琪拉。西恩的儿子,开始喝他人生的第一杯啤酒了,在这儿祝你健康长寿,弗兰基,愿你活到老喝到老,但是不要喝多了。
人们纷纷举起各自的酒杯,点头,畅饮,喝得嘴唇和胡须上都是泡沫。我吞下一大口啤酒,帕姨父告诉我,看在耶稣的分上,慢点喝,不要一口干,只要吉尼斯家族的人都安在,酒有的是。
我说想用我在邮局的最后一次工资请他喝一杯,但他说:别啦,把钱带回家给你妈妈吧,等你胳膊上挎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春风得意地从美国回来时,再请我也不晚。
酒吧里的人正议论着险恶的世界局势,还议论着纳粹战犯赫尔曼。戈林是怎么在临刑前服毒自尽,免受绞刑之苦的。美国佬在纽伦堡宣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狗杂种把药藏在哪里了,他的耳朵里?鼻孔里?屁眼里?美国佬每抓获一个纳粹,肯定都检查他们的每一个洞眼儿和隐秘的地方,但赫尔曼照样蒙过了美国佬的眼睛。你瞧瞧,他们可以横渡大西洋,登陆诺曼底,把德国鬼子炸个一干二净,但等一切都搞定了,他们却发现不了戈林肥屁股里的那粒小药丸。
帕姨父又给我买了一杯啤酒,但喝下去有些困难了,肚子已经涨满,鼓得老大。人们又在谈论着集中营和可怜的犹太人,他们从未伤害过无辜,却男女老少一齐被塞进炉子。孩子啊,你想想,他们能干什么坏事?小孩也被塞了进去,小鞋子扔得到处都是。酒吧里烟雾缭绕,声音此起彼伏。帕姨父说:你没事吧?你的脸跟纸一样白。他领我上厕所,我们两个冲着墙痛痛快快地尿了很长时间。我不能再回酒吧了,那烟雾、变味的吉尼斯啤酒、戈林的肥屁股、乱扔的小鞋子,让我不想再进去了。晚安,帕姨父,谢谢。他让我直接回家,回到妈妈身边。直接回家,哈,他还不知道阁楼顶上兴奋的事呢,也不知道绿沙发上兴奋的事,我如此罪恶滔天,要是现在死了,立刻就会下地狱的。
帕姨父回去继续喝酒,我走在奥康纳街上,心想何不趁十五岁的最后一夜,去耶稣教堂坦白自己的罪过呢?我按响牧师家的门铃,一个大个子男人问我:有事吗?我告诉他,我想忏悔,神父。他说:我不是牧师,别叫我神父,我是教友兄弟。
好吧,兄弟,我明天就满十六岁了,想在今晚忏悔一次,好在我生日的这一天得到神恩的宽恕。
他说:走开,你这个醉鬼,你这种醉得一塌糊涂的臭小子,这个时候还来找什么牧师。走开,要不我就叫警卫了。
啊,不要,啊,不要,我只是想忏悔。我厄运临头了。
你喝醉了,这种状态不适合忏悔。
他当着我的面关上门,又一次被当面摔上门!可我明天就满十六岁了,我又按响门铃。那位兄弟开门,一巴掌打得我转了个圈儿,又在我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把我踹倒在台阶上。
他说:再按门铃,我就打烂你的手。
耶稣会教友是不该这样说话的,他们应该跟我主一样仁慈,而不该到处威胁要打烂人家的手。
我头晕眼花,想回家睡觉。我扶着栏杆走过巴灵顿街,再扶着墙走进巷子。妈妈正在炉子边抽“忍冬”,弟弟们在楼上睡下了。她说:这个样子回来,真不错啊。
尽管舌头都大了,我还是告诉她,我跟帕姨父一起喝了人生的第一杯啤酒。父亲没有领我去喝这第一杯啤酒。
你帕姨父应该更在行。
我磕磕绊绊地向椅子走去,她说:跟你父亲一个德性。
我努力控制着舌头,说:我宁愿、我宁愿跟……我宁愿……宁愿跟我父亲一个德性,那也比拉曼。格里芬强。
她扭过脸,盯着灶台里的灰烬,可我不想放过她,因为我已经正式喝过人生的第一杯啤酒,喝了两杯,而且我明天就满十六岁了,是个大老爷们了。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我宁愿跟我父亲一个德性,那也比拉曼。格里芬强。
她站起来,看着我,你说什么!
你***又说什么!
不要这样跟我讲话,我是你母亲。
我***想怎么跟你讲话,就怎么跟你讲话。
你现在一副电报童的嘴脸。
是吗?是吗?那好吧,我宁愿当个电报童,那也比拉曼。格里芬这号人强,一个鼻涕邋遢、住在小阁楼里的老醉鬼,竟然还有人爬上去找他。
她走开了,我跟着她来到楼上的小房间。她转过身,说:别烦我,别烦我。我继续朝她吼:拉曼。格里芬、拉曼。格里芬……她开始推我,说:滚出去。我一巴掌打在她脸上,泪水涌出她的双眼。她发出一声微弱的悲咽:你再也不会有机会这样干了。我从她房里退出来,我那长长的罪名上又加了一条,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我倒在床上,衣服也没脱,半夜醒来吐了一枕头。弟弟们埋怨味道难闻,叫我去洗干净。我觉得真丢人。我听见妈妈在哭泣,我真想对她说对不起,可是她跟拉曼。格里芬做了那样的事,我又凭什么对她道歉呢?
早上,小弟弟们都上学去了,小马拉奇出去找工作了,妈妈坐在炉边喝茶。我把工资放到她肘边的桌上,扭头便走。她问:你想喝杯茶吗?
不。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无所谓。
她在巷子里冲我喊:你应该吃些东西。可我头也没回,一声不吭地转过墙角,走了。我还是想对她说对不起,但要是这样做的话,我就得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那天夜里,她真不该爬到小阁楼上去。我压根不在乎,我还在为菲奴肯太太写恐吓信,攒钱准备去美国呢。
在去为菲奴肯太太写恐吓信前,我还有整个白天的时间。我在亨利街上闲逛,后来,雨把我赶进圣芳济会教堂,圣弗兰西斯在那里跟他的小鸟和羔羊站在一起。我看着他,奇怪我为什么会向他祷告,不,不是祷告,是乞求。
我乞求他为特丽莎。卡莫迪说情,他什么也没做。他带着浅浅的微笑,和小鸟、羔羊一起站在基座上,对特丽莎和我,他一个臭屁也不放。
我要跟你绝交,圣弗兰西斯,一边去吧,弗兰西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你的名字。要是他们叫我马拉奇多好,那是个国王,还是个大圣人呢。你为什么不治好特丽莎?你为什么让她进地狱?你还让我母亲爬到小阁楼上去,让我自己厄运缠身,让小孩的鞋子在集中营里扔得到处都是。我又长出了脓疮,长在我的胸口上,我感到饥饿。
圣弗兰西斯不肯帮忙,他毫不制止我夺眶而出的泪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