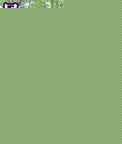悬灯录·下-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来谁都是被摆错了位置,不愿被某种权力或信仰所束缚。
转过头去还是圣女故作天真的一张脸,苏提灯笑的慈祥,「你问沉瑟那意思,就跟问他『你信苏提灯是善良的吗?』」
「然后他回答,『我想信。但我不信。』是一样的道理。」
接过辰皓恭敬递过来祈福的禅杖亦换做一张无悲无喜的脸,怜悯的慈悲惊人的冷清,他缓缓收了笑,眼看着匍匐于祭坛之下铺陈开万里山河的子民,恭恭敬敬的低首连多往祭坛上沾一眼不小心窥见了大祭司的真容都是罪过。
他内心忽然就生出万千感慨,看着那长长铺开的人群,越过流光溢彩的祭坛,越过黑压压的人头,越过五彩斑斓的花草,放空至长长远远的地方,那里或许遥指中原,也或许遥指神话里的忘川,却也亦如内心盘桓不去的那声哀叹——
他说他想信,但他不信。
苏提灯忽然又勾起了嘴角,黎明第一缕晨光洒在南疆这片纯净的沃土上,洒在他们大祭司那美好到如同九天神佛般清秀出尘的面容上,眉宇间是从未有过的清澈,眼瞳里又是欺尽世人的风彩,他含着笑,慢慢阖上了眼,将禅杖立于祭坛中央,缓缓伸开了手臂,同他那永世不变的冷清,慢慢颂起了最美好最祝福的一段咒文。
匍匐于脚下的子民都诚惶诚恐,他们都知道,现在立于祭祀台上的这位祭祀,是他们天大的福气,是这百年以来,最诡异强大的一位蛊师,同时,也是最心怀善念的一位慈悲为怀的行者。
耳朵里未曾听闻南疆的子民那沸腾一般感激的言论,苏提灯心底平静无澜的颂着祈福之歌,脑海里却死死停留在那夜幽蓝灯盏旁的宣纸。
蘸饱了朱砂的笔落纸苍茫,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亦都暗藏了锋芒,一遍遍一划划一横横入了魔一般的不肯放手去反复勾勒,及至停下时只有差不多晕开了一整张纸的诡红,本以为晕染开好像就能把心头痛、心头悔、心头恨全都化开一样,却反而发现那最初的字迹越发清晰,就像是蘸着自己的鲜血燃就——
『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
……
苏提灯眨了眨眼,又眨了眨眼。
他此刻也不想跟沉瑟提若是叫裘风去成功性更大一些,毕竟这时候说了这事也不大好,有些话就是得找个合适的时机开口,总不能在彼此稍微好了点的时候,忽然说,其实我一去中原就在你的人身上下了蛊吧。
而且纵使计谋再天衣无缝亦有老天爷的变数在其中,苏提灯也不指望一次性能把武器捞齐,只要能多坑一些人葬在里面就成了。天然的尸坑啊……
「那好,等着要行动了之前,我去送月娘到八角小楼。」
沉瑟点头,随即离开了房间。
苏提灯埋头案前,看看有没有这几天漏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一瞥眼却发现桌上码了几本,该是沉瑟挑拣过的。
看了会儿,苏提灯像是有些体力不支,窝回椅子里,淡淡向在一旁候着的绿奴道,「那碗羹……你加的甚么糖?」
「就是先生你原先常吃的那种冰糖啊。怎么了吗……出甚么问题了,是不是不合口啊先生?」
「……没事。」
「是太甜了还是太淡了,你跟我说呀先生,我下次好改……」
看着小孩又慌张起来,苏提灯轻轻摇了摇头,悲悯的笑了笑,「不是你的问题,这几天我大概是药喝多了,嘴里一直发苦。羹很好喝,合我的意。你做的没甚么不对,放心吧。」
小孩这才放心的再度落座,但内心寻思着,这几天再熬粥的时候多加些糖,先生说他嘴里苦呢!
作者有话要说:
☆、第142章 卷十,旧人序(七)
及至沉瑟带着十七同苏提灯先行上了路,他还是在内心重新把这个少年人的眼界定义了一下。
未免太过长远,本以为他是想自己去同正渊盟请这个缨,顺带能给自己洗白一些,好歹将来更好和他那大哥薛黎陷相处,却不料他自从那日同自己讲了这件事,便一直没有多少动静,直到看到了正渊盟的请帖,这才『勉为其难』又『义不容辞』的应下了。
彼时趴在桌上修着阵法图的少年有些不解沉瑟的怀疑,「卫家那趟他们都怕中了蛊,还拖重伤的我走一遭,此刻我身形健全又未带病,焉有不叫我同行的道理?」
沉瑟负手在车辕上立了会儿,寻思完事又进来,语气并拿不准,有些许怅然,「我还是不放心,你纵然暗地里起阵,最好也等我卷完武器回来的……」
「沉公子,别傻了。你卷完武器还回来么?那群正道人士都死在了阵里头还好说,可以死无对证,那万一有没死的,事情再怀疑到我身上来,那才是百口莫辩。」
沉瑟眉头未展平,继续坚定摇头道,「两仪阵法相生相克,你那是一时兴起弹了琴有了兴头才造了个杀伐阵出来,万一不小心把你自己也赔进去呢?」
少年人一双风情瞳未曾离开过手里阵图,闻言眼皮子也未多抬一下,「我死里头不是更好,了了你的心思了。」
「我没在与你说笑。」
「我亦没有。相信我,沉瑟,生死二阵我不会同时开的,心下有数。再说了,生门阵是你设计的,简直是处处有逃路,万不得已的时候大不了开了它,将所有人放出来便是了。」
「那这不也相当于都开启了么?那谁站在阵眼处,甘愿牺牲?」
「天呐,」苏提灯叹了口气,难得从阵法图上收拾起心思正眼瞧了沉瑟,「你这次怎么这么婆妈起来了。在地城炼狱里暗造阵法之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我二人不说,谁会知道?那其他随行人群总有四五个缺心眼的会逃不出来罢,难不成还一个个的都武功高至你同薛黎陷那般程度,我随便一个诱导阵还引过不去了?」
沉瑟蹙眉,总觉得苏提灯今次这事未免做的太胆大,有点赌的性质。
沉瑟向来是不怕赌的,他这个人,去赌场十中有九是能赢的,可是他对赌并不感兴趣,就跟了解『不归』一样,深知后果,所以不会触碰。
「我们虽然是提前小半月早走的,但是想必地城那边已是聚集了一些正渊盟和江湖上的高手,加之南宫家表面被毁,实际上一些很厉害的前辈也应该都躲入地城之中。不乏会蛊术者,亦不乏最终之时的漏网之鱼。」
苏提灯又展开那阵法图,特意指了几处位置给沉瑟看,「按照正渊盟说的,我们一开始进去后分三路包抄,好在地城是个大椭圆形的,我们最终怎样都是能遇见的。我一开始进去走最中间那条算是给他们躺雷了,这样的话我才能把四周都感应到,万一感受到控蛊人也可以随时让左右两边相互支援。」
「那这么说薛黎陷岂不是也不能护在你身边?」
苏提灯万分糟心的看了看完全不在状态的沉瑟,今次他又在闹甚么妖,自己难道就是个得靠人护着才能活下来的人吗?
「在有蛊术的地方,你们这群武功盖世的高手反而比我更容易遭殃好吗?我算是入如鱼得水之境了,我还怕区区一二蛊术?倒是你要小心点,还有……沉瑟,我调整过来了。」
沉瑟的眸光又复杂了一些。
「没事的,你不必担心我。这么多年了,有些东西就是不可得,从未要过一二丝家人默默温情,此刻若是真得了,大抵也是不会习惯的,反而暗生不同情愫更易做了拦路虎绊我前行。」
随手拿了朱砂又在几处圈了圈,苏提灯微微笑了起来,「我很好,沉瑟。这么多年,我早就彻底死心了。把自己活成了一条无人敢亲近的毒蛇,何曾不是怕被同类的毒牙先行咬住七寸。如今我没了这个七寸,不是更妙吗?」
马车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打在檐上七零八落响的有些凄凉,驾车的红衣女子平常心的撑起了身边小伞继续稳妥妥的架着马车,正费事的想要歪脖子同肩膀夹住之时,一只毫无温度的手伸了过来,替她拿过了伞。
人间三月末的清风细雨微香混着自家主子那一身出尘的檀香,好似莫名便在前路看到了泥塑金身佛像面前那三缕袅袅之烟,十七刚想抬头告诉她家主子她自己能应付得了,便只见眼前晃了一身白,衣摆微微飘起的幅度还未得缓下,她家主子那张同样出尘的脸便出现在了身旁。
十七侧仰着头望了望,不确定道,「主上?」你不开心么……
「走吧。」
语气永远是如故的寒冷,三月暖风未曾灼过心田一寸温。
於是她便收了心下那声叹,继续稳稳当当架着马车向前行进了。
沉瑟离去时搅动的马车帘似乎摆幅也未曾缓下,人走茶凉好似说的也就是那么回事,微风细雨下的也未免太过刁钻,趁着帘子晃荡的缝隙便可劲的往里钻,一不留神便扫了一脸细密的雨珠。
苏提灯有些着迷的盯着那偶尔晃荡起又闭合上的车帘所露出来的那一方靛青苍白天空望得起劲,心说,还好自己从小就被废了经脉,就跟那从小被夺去七寸的蛇一样,活下来是侥幸,可同样,这样的蛇还能活下来了,就是苍生的不幸了。
他忽又无声笑,正好没了软肋,正好……还有毒牙。
君山白毫仍旧能闻得出曾经那股子沁心的熟悉味道,只是,入了口便是麻木。
五感已失一感,一感已失,其余四感便是打蛇随棍上,不会晚到哪里去,或许片刻或许今朝亦或许他日,祈祷了许久愿苍天失手,多拖延的恶梦还是如期而至。既然做不到缅怀那何必不将它举办成一场欢庆。
『若我还能为人……』
这句话,今后也只是想想罢了,既然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妄谈甚么合家亲情欢乐团圆,妄谈甚么温香软玉素手在怀。
『你哪怕还是个人的时候,不照样是个废人么?』
他忽又在内心自嘲,重重将茶盏弃于桌上——这一局,他跟老天爷赌定了。
万千人命我不惜,白骨累累我不怕,纵使赔上生生世世,那个曾真心实意待过我的姑娘,我也一定要将她夺回来这人世间来!
『公孙月,你醒之后,恨不恨我,爱不爱我,都没关系。』
『说到底我不过也是一个自私的人,不甘心这么多年都是孤苦一人,不甘心从小到大未曾得过苍天一顾,我想要的,无非是让自己不那么后悔便是了。』
『恨我吧。』
『没关系的。』
『我还能爱着你,于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
*******
青天白日之下,宜进攻,宜收妖,宜惩恶扬善。
只是,关于摧毁地城炼狱这里,大家却是不用言明的晦暗默契——低调,再低调。
这个地方的存在一旦流传出去,于人心又是一场极大的惶恐,这也是冯老当初担心的一个缘由,如何天衣无缝的连锅端掉,还要必须做到悄无声息,万一留存一个余孽活下,便是往前往后中不敢深思的念想里一道时时刻刻得揣着的暗刺。
其实,冯老曾因这件事,在行动之前,特特找了一趟苏提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渊盟同鬼市一样按兵不动,不在第一时间去摧毁地城,其实都是含了这份心思在其中的——向来最恶不过人心,向来最诛心不过人言。
正渊盟虽还有十几位高手前辈,但是基本是各有各的职责,除了本身就常年在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