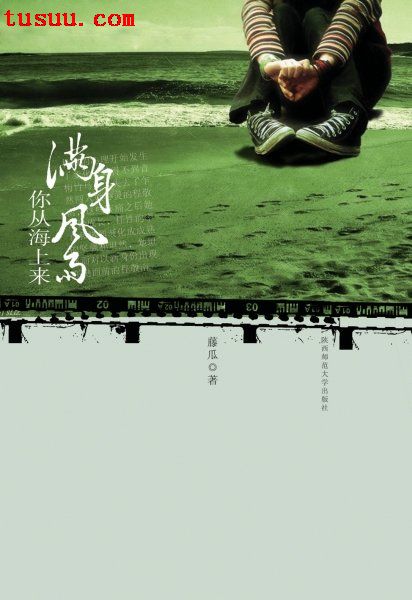海上劳工-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鹗橇降狼降敝械囊欢谓值馈4蠹野颜舛运难沂凶隽阶喾鸲福捍蠖喾鸲托《喾鸲4蟮挠辛吒撸〉挠兴氖吒摺:@死蠢慈トィ沼谠谡饬阶サ牡撞磕コ鲆坏谰庀撷佟R话宋寰拍晔露眨徽笄锓质钡目穹绱档沽似渲幸蛔JO碌囊蛔切《喾鸲惨丫俚袅艘欢危瓢懿豢傲恕�
在多佛尔的一群最奇形怪状的岩石里,有一座叫人岩。它直到今天还在那儿。在上个世纪,一些在这些岩礁间迷失方向的渔夫,在这座岩石的顶上发现一具尸体。在尸体旁边有许多空贝壳。有一个人的船在这座岩石旁沉没了,他逃到岩石上,依靠贝壳活了一些时候,后来死去了。从此岩石就叫做人岩。
寂寞的海水显得凄凉。这儿既喧闹又静寂。这儿发生的事和人类毫无关系,有什么效用不得而知。这便是多佛尔岩礁的孤立状态。四周一望无际,只有不断折磨人的海浪。
① 迷宫原指古代结构复杂、走进后很难找到出路的巨大建筑。
① 锯线是锯割时作依据用的。
二 出乎意料的白兰地
星期五早上,就是“塔莫利帕号”起航的第二天,“杜兰德号”起碇回格恩西岛。
它在九点钟离开圣马洛。
天气晴朗,没有雾。老船长热尔特雷—加布勒好像说的都是些颠三倒四的话。
西尔克吕班心事重重,结果自然使“杜兰德号”几乎没有装多少货。他只给圣彼得港的时髦服饰衣料商店装了几件巴黎来的货物包裹,给格恩西岛的医院装了三只箱子,一只装的黄肥皂,另一只装的长蜡烛,第三只装的是法国做鞋底的皮和上等的科尔多瓦皮革①。它带回前一次运来的一箱碎糖和三箱低级红茶,都是法国海关不同意进口的。西尔克吕班装下很少的牲口,只有几条牛。这几条牛给随便地装在底舱。
船上有六个乘客:一个格恩西岛人,两个圣马洛的牲口商人,一个“旅游者”②,当时已经有这样的叫法了,一个半中产阶级的巴黎人,也许是旅行推销商,还有一个是四处旅行分发《圣经》的美国人。
“杜兰德号”除了船长克吕班,一共有七个船员:一个舵手,一个烧炭的水手,一个做木工的水手,一个必要时也能驾驶船只的厨师,两个火夫,和一个见习小水手。火夫中的一个同时是机械师。这个兼任机械师的火夫是一个十分勇敢和十分聪明的荷兰黑人③,他是从苏里南④的制糖厂逃出来的,名叫安布朗康。黑人安布朗康懂得机器,而且能非常好地照管机器。在“杜兰德号”航行的初期,他全身漆黑出现在锅炉旁,给这只船没有少增添魔鬼的气氛。
那个舵手,在泽西岛出生,原籍是科唐坦①,叫做唐格鲁伊。唐格鲁伊出身于一个高级贵族人家。
这件事是完全真实的。拉芒什海峡的群岛,像英国一样,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地方。这儿还有社会等级存在。各个等级有它们自己的观念,那些观念是它们的保障。等级具有的观念处处都是相同的,在印度和在德国完全一样。贵族身分靠剑取得,由于干活而丧失,无所事事却保留了下来。什么事也不做,这便是贵族式的生活,谁不干活就受到尊敬。有一个职业会使人地位下降。从前在法国,只有制玻璃工人这一行是例外。把酒瓶喝光多少是贵族的光荣,因此制做酒瓶对于他们来说便不是丢脸的事。在拉芒什群岛和在英国一样,谁想当贵族,就应该有钱。一个工人②不可能又是一个绅士③。即便以前他是绅士,现在也不再是绅士了。
① 是一种在科尔多瓦加工的羊皮。科尔多瓦是西班牙一城市。
② 原文为英语,此词19 世纪初传入法国。
③ 指荷属殖民地的黑人。
④ 苏里南,现南美洲北部国家,旧称荷属圭亚那。
① 科唐坦,又译科坦登,法国西北部伸入拉芒什海峡的半岛名。
② 原为英语。
③ 原为英语。
祖先是方旗骑士④的水手,如今只不过是一名水手。三十年以前,在奥里尼有一个真正的乔治,他本来应该有权利得到乔治家族的领主权,可是那早被腓力·奥古斯都⑤剥夺了,他现在赤着脚在海水里捞海藻。一个姓卡特里特的现在是塞尔克的大车夫。在泽西岛有一个呢绒商,在格恩西岛有一个鞋匠,都姓格吕希,他们自称姓格鲁希,是滑铁卢的元帅⑥的堂兄弟。库唐斯①的主教府的收益表册上提到唐格罗维尔家的一项领主权,他们明显地是塞纳河下游地区的唐卡尔维尔家的亲属,就是现在的蒙莫朗西家族②。在十五世纪,唐格罗维尔的老爷的弓箭手和服装总管,约翰·德·海罗德维尔,在主人的身后,拿着主人的“胸衣和其它的服装”。一三七一年五月,在蓬托尔松③,当贝特朗·德·盖克兰④检阅的时候,“唐格罗维尔先生像青年骑士那样执行他的职责”。在诺曼底群岛,一个贵族如果突然变得贫穷,他就会很快地被取消贵族的身分。只要改变一下姓氏的发音就行,唐格罗维尔变成唐格鲁伊,于是便解决了。这就是“杜兰德号”的舵手的遭遇。
在圣彼得港的博达热,有一个买卖废铁的商人,叫安格鲁伊尔,可能是某一个安格罗伊尔。在胖子路易⑤时代,安格罗伊尔家族在瓦洛涅⑥财政区拥有三个堂区的土地。有一位特里甘神父写了一本《诺曼底教会史》。这位编年史作者特里甘是迪戈维尔家的领地的本堂神父。迪戈维尔老爷假使降为平民,那就会叫做迪古伊。
唐格鲁伊,这个人也许叫唐卡尔维尔,也可能叫蒙莫朗西,具有那种贵族的古老品质,而对一个舵手来说却是严重的缺点,他总是喝醉酒。西尔克吕班坚持要看管好他。他对梅斯莱希埃里保证过会这样做。
舵手唐格鲁伊从来不离开船,就睡在船上。
起航前夕,西尔克吕班在夜很深的时候上船来查看。唐格鲁伊已经在他的吊床上睡着了。
半夜里唐格鲁伊醒了过来。这是他夜间的习惯。所有不能自我克制的酗酒的人都有他们藏酒的地方。唐格鲁伊也有这样一处,他管它叫做贮藏室。唐格鲁伊的秘密贮藏室在底舱里。他在那儿藏酒,为的让别人难以相信能有这种事。他完全有把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克吕班船长不喝酒,为人严厉。可是这个舵手能够避开船长严密的监视,藏起一点点朗姆酒和杜松子酒,把它们放在底舱那个秘密角落里的一只探测水深用的小木桶里,几乎每个夜晚他都来和这个贮藏室幽会。监视很严,痛饮受到限制,通常唐格鲁伊的这种夜间放纵行为只限于喝上两三口,是偷偷吞下去的。有时候这个贮藏室甚至什么酒也没有。那天晚上唐格鲁伊在那儿找到一瓶烧酒,真是出乎意料。他万分高兴,但是更是感到惊慌。是从天上哪个地方落下这瓶酒给他的?他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它带上船的。他立刻把酒喝光了。也许是为了慎重起见,因为他害怕这瓶烧酒会给人发现和没收。他把酒瓶扔到海里。第二天,唐格鲁伊掌舵的时候,他身子有点儿摇晃。
不过他几乎像平时一样驾驶着船。
至于克吕班,大家都知道,他回到约翰客店去睡觉了。
克吕班在他的衬衫里面,总是系着一条旅行用的皮腰带,他在那里面放了二十个备用的畿尼,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把它解下。在这条皮腰带的反面,有他的名字:西尔克吕班,是他亲手用很浓的石印墨水写在粗皮上的,永远也擦不掉。
起航以前,在起床的时候,他把装着七万五千法郎钞票的铁盒放到这条腰带上,然后他和通常那样,把腰带扣在腰上。
④ 方旗骑士,欧洲中世纪的一种骑士,有权率领扈从在自己的方旗下上阵作战,其权位在只可使用三角旗的最低级骑士之上。
⑤ 腓力·奥古斯都,即腓力二世(1165—1223),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204 年起先后收复英王在法国境内占据的领地诺曼底、安茹等。
⑥ 指格鲁希(1766—1847),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将领,百日王朝中晋升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因未能阻挡住驰援英军的普军,以致造成拿破仑大败。
① 库唐斯,法国芒什省一城市。
② 蒙莫朗西家族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家族,出了几个重要人物。
③ 蓬托尔松,法国芒什省一城市。
④ 贝特朗·德·盖克兰(约1320—1380),法国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曾几次大败英军。
⑤ 胖子路易,是法国国王路易六世(1081—1137)的绰号。
⑥ 瓦洛涅,法国芒什省一城市。
三 中断的谈话
船轻快地开航了。乘客们把手提箱和旅行箱在长凳上面或下面放好以后,马上就去参观这条船,乘客们是从来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而且仿佛坐上船的人都一定要这样做,成为惯例了。旅游者和那个巴黎人这两位乘客从来没有看见过汽船,明轮刚开始转几下,他们就赞美起海水的飞沫。接着他们又对冒出的烟大为欣赏。他们在甲板上和二层舱里,一样一样地,几乎是一点一滴地仔细观看着所有那些航海用具,像铁环,铁钩,吊钩,螺栓,它们制作得精密,相互配合准确,仿佛是一套巨大的首饰,只是这套金色的铁制首饰上全是暴风雨带来的铁锈。他们绕着放在甲板上的小报警炮走了一圈。旅游者说:“系着链子,活像一只看家狗。”那个巴黎人接着说:“穿着一件涂柏油的粗布罩衣,好不让它得感冒。”当船离开陆地的时候,人们交换对圣马洛的景色的合乎惯例的评论。有一个乘客发表一种理论,认为从海上看附近的地方,常会上当,在离海岸一海里远的地方看,奥斯坦德①和敦刻尔克再相像也没有了。别人对他说到的敦刻尔克做了补充,说那儿有两个漆成红色的警戒浮标,一个叫吕丹让,一个叫马尔迪克。
圣马洛在远处越来越小,接着看不见了。
大海从表面看是无边的静寂,船后面的海面上出现的航迹形成一条镶着泡沫边的长长的街道,它几乎毫无弯曲地伸长,直到看不到尽头的地方。
从法国的圣马洛到英国的埃克塞特①划一条直线,格恩西岛就在这条直线的中心。海上的直线并不总是合理的直线。但是汽船在一定的程度上,有能力沿直线航行,帆船却无法做到。
大海因为起风,变得复杂了,它成了各种力量的结合体。一只船是一些机器的结合体。力量是无限的机器,机器是有限的力量。这两种组合体,一种是用之不竭的,一种是机智灵巧的,在它们之间进行的斗争就是人称的航行。
一种在机械中的意志是和无限相抗衡的。无限本身也包括一种机械。大自然的力量知道它们在做什么,要去哪儿。没有任何力量是盲目的。人应该密切观察种种力量,设法发现它们进展的规律。
在规律没有发现以前,斗争会继续下去。在这样的斗争中,用蒸汽航行,是人类任何时刻在海洋上任何地方获得的持久的胜利。用蒸汽航行最妙的特点便是能控制船只,减少对风的服从,增加对人的服从。“杜兰德号”从来没有像这一天这样在海上航行得如此顺利。它行驶得简直完美极了。
在十一点左右,吹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