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ص�Ԥ��-��1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ʶ�Ǹ������������ˣ���
�������ĸ�����
�����������ڿ��ȵ�ǰ���Ǹ����Ա����ҵ����њG��������Ǹ�������Σ�Ʒ���Ƿ�������ã��������ģ���
��������Զ��Ȼ�������ң�������һ�������˵�������á���
��������Ҳ������ֻ����ʶ��������Ϥ��Ҳ��û�����ʡ�
�������ͽӽ�β�������㷹����ʮ�����⣬Ц���ж���˵�����δ������ȥ��Ϣ�ɣ�����ϴ�롣��
�����������ң�ֻ��Ц��ͷ����ˮ����������Ӣ����������Ͷ��һƬ���裬��DZ�������ӡ�
������ϴ������so�ġ�����������ȥ��
��������Ʋ���������������ϴ�롣
���������˵��ֽ�����ĭ���棬��֪���Ϻ�������ˮ���µģ��������������̵ģ���֮������ů�ġ�
��������Զ
����û�뵽���ǹ��ᄍ�Ǿ��ε����ѡ�
��������������ôС��
�������ң�������γ���ˮ���������ָ���λش�
�����ǹ��������Ȧ�ӳ��ֹ�����֪���Լ���ʲô��ɫ�����Դ���С��������
�������ǣ�����ʲô����֪����
������Ϊ��ĸ�ķֿ������ǣ�����������������������硣
����Ȼ������������Զ�ľ��Σ���һ����֮���ף��ҵ��߾����ܵر�ȫ��
�������壩
��������
�����Ϸ���ʮ�»���Щ�������ζ����
�������Ϻ�������죬����Զ�ܻ�ѹ����Ƶ����ϣ�����������˯������Ȼ��䶼�ᡣ��Ӧ���Ǹм������ҵġ�
�������ڣ����������ľ��Ϻ���ò�Ѿ���Ѱ�٣������¼�����Ƭ��Ҫ�����ſ�����������������Ϻ����ķ绪��ï��
�����⼸�죬ż����������ĸ�������顣���������ǹʵ������飬��֪���ŵ������ܲ��ܳŵ�ס��Ӧ�ø����Ų��绰�ģ�ȴ��֪����˵Щʲô��
���������Ѿ�������ʮ�����е���ʯ��ë����ҽ����Ϊ������״�������̫���Ե�ʽ��黹�Dz�Ҫ�����ĺã����Խ�����Ϊ�缲��������е�ʱ���������Ǻܼ�ǿ��ÿ�»���Ϊ����ʯʹһ�Σ�ʹ������ƽƽ���ڴ��ϣ�����ҩ�㲻��������һ����ǿ����ʹ�ࡣ�Ҽ������Σ���ʱ����Ϊ����ֻ������˯���������µ�����Ƥ��ſ�������ؿں��֣������˲ŷ������Ŷ��ϸϸ�ĺ���Ϳ��ݱ�������ָ����ɫ���ǻҰס������ҵ�һ���������ϵĸо������»֣̿�����Ѱ�绰����ͨ120���ȣ����Ż���һ˿���ѣ������ҵ��֣�������������˵��û�£�����һ����ͺá�һ�����������������������dz�������Ϊ��ʧȥ�����·�һ�������������ⱻ��������ȥ��
����˼���ص����ڡ�
���������ź���Զ�ļ����Ŀ��Ϣ�������Ĵ��ָ����ҵ����ϣ���ů�������İ���
���������������ô���������ҡ�
������û�а������ҷ����Լ��Ĵ�������ĸ�����飬�������ɱ�������һ�����š��Ҳ������ᣬ������Щ���ŵ��������¿�ˮ���������ջῪʼ�����ҵġ��ҵ�Ϊ���������֡�
����������һ��һ�죬��Ӧ������һ��ġ�
�����л�Ҫ˵������
�������ʮ����
������ʮ����
��������
������һ��
�����Ϻ�����·���Ĺ��������ص�������ػ�����Υ�ĸо���
������˵�������������հɡ���
������ѽ������ȥ����ױ�����Ҽ��ٻ�ױ��ֻ��Ϊ�˶�����������Ҫ�ٰ�һ�㣬Ȼ����ɫ�Ŀں죬�Ҷ�û�Թ��߸�Ь�������ȥ��һ˫����
�����������뻳�������Ҷ�����
����ǡ��һ����������������������ǰ�æ���գ����Ӻ��������У��ɷ�Ҳ�������������ź���Զ���ֻ�����ص����Ƕȡ�
��������˵����������䡣��
��������ԶЦ��л��
�������������Ҹ����˵�ף��������һ��Ҳ����Ҹ��ġ�
�������죬�Ϻ�������磬�����˿˿��������磬ȴ�����䣬����Զ�����ҵ��֣�������ש�̾͵�С·���ţ��·����������ӻ�һֱһֱ����������ȥ��
���������������¹仴��··β�Ĺ���Ʒ�ꡣ�Ϻ��Ǹ��ڻ��ͨ�ij��У�����ÿ��·ÿ���ֶ�����������صĵ�������������ͼ�����������Կ���Y�ǵ�����Ҳ���������Ϲ�֮����ʮ�ֵ����С�
���������ڲ���һ�Һ�С��С�ĵ��̣��������Ƿ�����ȵ�������ӡ�Ŵ�䰵��ɫ�Ļ��Լ��Źֵġ�Roma�����������������֣�С���������ÿ���������ı�ɴ���ӣ����������м���һ��խ������ľ��¥�ݡ�
����������λ���������صij���Ů�ɣ�С��ɫ��Ƥ��ȴ�����������Ƶľ�����٣�Ѫ��Ĵ�ɫ����ë���ܵ���������ɫ����Ӱ��ͻأȴ���ˡ��ɰ��Ķ���������ɫ��ë�صĶ���������������ij�ȹ���������ľ�ʵĵذ��ϡ������ڽ�������Ż��ʣ�רע�ؿ�����ǰ�Ļ�����һ�Է����ͻ������ϣ�����û�з������ǵij��֡�
����С��ش�����������ȴ���ż�С�Ҹ��ӵ����棬ͨ���¥�������ѣ��ɼ�ӯ�������������������ˡ�����ĵ�������Ӧ����λ���������ң�����Ȧ���ֻ�Ľ��������ʶ����ʿ����Ϊ�˵ص�������ʮ�ֵİ���
��������������һ�Ժ���ɫ��ָ��ָ���������СС�ּ��������㡱�������Զ�����ӣ���ʮ�ֿɰ���
���������������¾�Ӧ��ϧ����������һ���������
����˵��ʱ����ȴ��û�п����ҡ�
�����Ҵ�δ��ʶ���������Ե�Ů������Щ������˼�ط����ǶԽ�ָ����Ȼϲ�����ǵ����֣�ȴ���������ǡ����㡱�����֡�
��������Զ�������Ҷ�������˵����ϲ��ô����Ц��ҡҡͷ���������¡�
��������ɫ����ɣ����ɫ�����¼Ŀ�ʽ�����dz������д�Լ������úÿ���Ҳ������Ϊ��ʰ�����������ʡ�
������Խ�ָ��Ȼ����������Զ�Ĺ��£�һ�ι��ڡ����㡱�Ĺ��¡�
�����������뿪��ת��֮�ʣ��Ҵ���������������������Ŀ�⣬ֱ���Ҽ�������ء�
�����ҿ��ٱܿ���Ҳ������Ϊ���ʱ��̫�������ұȴ�ǰ��������ֱ�������������δ����
����������
��������
�����й䣬�����������ˣ��ҳ����������ɿ�ǣ�ź���Զ���֡�
�������Ǻ���Զ��ͬ�£���ͦ����װ��������ƤЬ���������ɵĵ���������һ��ģ����̳���ʯ�ˣ��������ģ�Ŀ��ȴ��Į���ɼ�����ҵ��Ӣ��
�������������ܡ����Ϻ����˵������dz�֮������
����������������ôû���ڽ�ï��������������ԶΪ������ǰ�볡��
��������λ�ǣ���
�������Dz��Ҷ�Ȼ���ȣ���Ȼʮ�ִ�����
�������Ⱥ���֮���������Լ�û��Ӧ���μ�������ï�Ĵ��;ۻᣬ�ҵ��д��ǣ����ۡ�
����������ֻ��һ����ȥ��Ȼ�������������֪�����ǣ��ۼ��ڽ�ï�Ľ���һ���Ŷ�ͬ��ǰ�������ƣ�������ɫ���������衣
�����������Ǻ��Ƹ���룬��֪������𣬻����������ͣ�����ͬ���ԣ�ֻ��ϧ�Լ���Ȼ�����Ϳѡ�����������רҵ��
��������Զ
����ͣ�����Ϻ������һ�����ϣ��ҽ���ȥ������Щʳ��Ľ����ң�������·��ȥ��ϣ���Ǽҵ껹δ���ȡ����³������ɿ����������š�
�������������ҷ��������پ���֣�Ȼ���ֽ����Ц���ʵ��������ǶԽ�ָ����
�����Ҵ��ǡ�
����������ô���ģ������ѵã�ֻ�ǣ��ǹ���֪��ô���������ţ�ȴ�ִ��ţ��Ӵ��ع���ȡ���ǶԽ�ָ�����͵����㣬��ȥ�ɡ���
�����ҿ������ƣ�����һ����������л����ȥ��������������Ű��飬Ŀ�����������ɣ���������˿˿���ij�Ц�벻м��
�������ƺ����ε�ҡ��ҡͷ���ſ��Ѿ�������һ�����ɫ��ʱ�ݣ�������λ��̬ͺ�������ˣ�����ѩ���̣���ͷ���ڴ�������������
������������darling��
���������س������ȴ�ǰ�����һЩ���·��������������Ӿ��������ʱ��һ������ʧ������
�����ҵľ��Σ��������Ů�ӡ�
�������Ǽ���ѩ��Ů�ӣ��۾���δ���������������������ȴԲԲ�ÿɰ�����ë���Ƶ���ɫ��������������ᷢ����Ȼ������Բ�ཱུķ����촽��������Ȼ��Ȼ������¶�����õ�Ц���飬ССԲ�����ż����°͡������Ķ�����Ϊ���ְ���ܳ��ַۺ�ɫ���������Կ���ϸ���ʻ��Ѫ�ܣ��������ۡ����������У�û�����ิ�ӵ��뷨����δ��˭��ʾ����������ξ�������һ���������֡�
����Ȼ�����������������࣬��������ص����£���������װ������
����������һ�ഩ��ְҵװ����Ⱥ���ܻ���Ȼ�ɿ��ҵ��֡�
�������ڵ���ʲô���Dz��Ǻ�������֪��������֮��Ĺ�ϵ���Dz�����Ϊ�Ҳ�Ը�����������ҵİ��ˡ���
����������
��������
�������Ϻ��ر����ĺ��ൽ��ʱ�����������㡣
�������·ɻ���ĸ��һ���������ſ������˳��������ȼ����֣�ȴ������һ������������ĸ��д����С�Σ��������������������Ͱְֶ���Զ���㡣
������֪���������վ����Ƿֿ��ˡ�
������һ�̣���ͻȻ��һ�������Ƶij嶯����Ҫ�Ͽ�ص�Y�ǣ��ص����������ļң�Ҳ�����ܸ��ϣ�Ҳ��һ�ж�ֻ�Ǹ���Ц��
������ʵ������Ӵ�֮����Щ���ڹ��������˵���Ƭ���ᱻʱ������������ڱ��˽�β�ļ���������²����������˹��е���Ӱ����ʱ���������ʼֵ�û����ô�ɱ��������ȥ���Ҹ�ͬ˭һ�𣬰ְ֣��������衣
��������Զ���ң���ô�ˣ�
��������ǿЦ��ûʲô������Сʱ���˵����û��Ҫ������ƿ�����������������ڽ�ʲô���Ҵ�ûʲô��
�����Ҳ�֪������α����ˮ�������̡�
������ûʲô���⻰˵���ˣ�Ҳ���Լ��������š�
�������м䣬���ӵ�һͨ�绰����û�й���͵����ë����ֻ�ǻ�Ͳ��һ�ߵ������ƺ����ٻ��ţ�Ů�ӵ���������ֻ����һ�����������ۡ�ʹ����
������һֱ�ڰ���������ˣ�˵������Ҫ�ţ������Ͼ͵���
�����ɼ���ʮ������顣
������������Ǹ�أ������£��������ѧУ���ǵ�Ҫ�Է�����
�����ҵ��ͷ��
���������ɲ����ģ���Ҫ�չ˺��Լ����Ҳ��ܷ��İ����͵�ѧУ����
�������š����ٴε��ͷ��
�������Ҹ����绰����
���������
�������ɣ���Ҳ��һ���˾��������롣
��������Զ
�����·ɻ������ο�һ���ֻ����۾���ʱ��졣����⼸�죬�����ƺܲ���Ը�����ֻ���������ú�Զ��
����һ·�ϣ����Ļ�Խ��Խ�٣������кܶ���ص�����ѹ����ͷ���������ɡ�����Ը˵���Ҳ�֪�Ӻ��������˾�ɥ��
�������������������⣬ֻ�д�Ƭ��Ƭ�İ��ơ��������������壬�������������ϣ���ĬĬ�����۾�����ֻ���˵�С�������ҵ����ˡ�
�����ҵ����࣬���������������ִ���һ��������ãã��ʹ�š�
�������������ʣ����յĵ绰����������յ������ڵ绰���Ե�ʮ�ֻ��ţ���Ϊ��ʹ��������ϸ��
�����������������������Դ���������ȴ�Ǵ˴�����ä��ֻ�ܾ���ϵ������������͵�ҽԺ��
�������ģ�
��������Զ
����ҽԺ�ļ��������ս��������ҵ��֣��·��þ�ȫ������߬��һ�����ݡ�������ɲ�������ɫ�Ұ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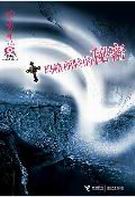


![[HP]�������ʽ���˷���](http://www.sntxt2.com/cover/47/4741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