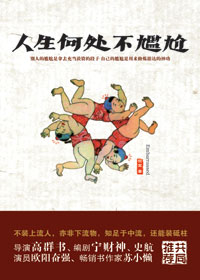玉人何处-归墟-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姑娘。”对方再次开口,声音淡淡的,也好听。
“嗯?”
“敢问姑娘,你手里拿的可是雪缨子?”
“雪缨子”三个字适时点醒了痴愣的女子,泠然下意识抱紧怀里的东西,脱口而出,“不卖。”
男子看着这个额头粘了泥巴的小姑娘,牵起嘴角,“姑娘真是冰雪聪明。”
“奉承也没用,雪缨子我是不会卖的。”泠然绕过对方,石耒也忘了拿,慌慌张张地往山下走。
男子不紧不慢地转身,看着女子跌跌撞撞的背影。“人可以走,东西要留下。”
“切……”泠然撇了撇嘴,别以为长得好看就了不起。“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想明抢不成?”
“姑娘言重了。在下不过提醒姑娘物归原主罢了。”
“呵……”泠然睁大眼睛回头看了他,“物归原主,你确定?”这雪缨子是她在祁瀮山脉转悠整整了大半个月才找到的,这个人居然说东西是他的!
“确定。”对方面不改色,含笑点头。
泠然飞起一个白眼,“这山难道是你家的?”
对方轻摇折扇,郑重其事点了点头,“这山的确是我家的。”
“你。。。。。。”泠然一个踉跄。山势陡峭,眼看着就要摔下去。只觉有手在她肩膀上一按,身形便稳住了。
再看眼前的男子,依旧摇着扇子似笑非笑看着她。怎么看都不像是他救了她。
一定是先生冥冥中相助。一想到落声,泠然便不争气地红了眼眶,抱紧雪缨子转身就走。
嗯?雪缨子呢?
泠然一个箭步冲到男子面前,“喂!你把东西还我!”
男子无奈笑笑,从背后拿出那个金色的胖娃娃,仔细打量一番,“长了一百多年,不过这般大。”
“还我!”泠然懒得跟他废话,伸手去夺。
对方轻巧躲过,“给个理由。”
“我家先生。。。。。。”泠然想起落声的嘱咐,“要你管。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快还我!”
“我出一千两黄金,姑娘可否相让?”
“不让不让不让!多少钱都不让!”泠然喘了口气,“你有那么多钱,尽可以雇人来挖。为什么非要跟我抢?”
“嗯,姑娘所言有理。”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可我只想要姑娘手里这一株。”
“你这人。。。。。。喂,你怎么走了?把东西还给我!喂!把东西还给我!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明抢呢?喂。。。。。。”
泠然一路追下山,见那人上了山道旁的一辆马车,眼疾手快也跟着爬了上去。“你。。。。。。快把东西还我!”
那人放下胖娃娃,倒了杯茶递过来,“喝茶么?”
泠然跑得气喘吁吁,接过茶盏一饮而尽。
在她开口之前,男子已将雪缨子递给她。淡淡吩咐道,“启程吧。”
泠然抱着胖娃娃仔细察看了一番,还好还好没有磕着碰着。“嗯?马车怎么动了?等等,我还没下车呢。”
男子在小几上摆开了棋具,“长路漫漫。泠然姑娘,可否陪在下下盘棋?”*
作者有话要说:
☆、八、梦复一梦
这一夜,薛清夜做了一个梦。
时间是十一年前。
感官在慢慢恢复,痛楚一点一点清晰起来。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她比谁都明白。药石只能强迫他昏睡,徒劳地为他保存最后的元气。活一天就少一天,这是他从二十岁那场大病后就再清楚不过的了。
她红肿着眼,沉默不语地为他换着冷水浸过的毛巾,长时间的高烧令他全身无力。
“哭什么,我不是还没死吗?”他勉力挤出一丝微笑。
她强忍着一言不发,趁转身拧毛巾的时刻,拼命咬住自己颤抖的唇。
“还愿意嫁给我吗?”嗓子像着了火一样,他却还是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你……”一开口,就再也控制不住,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少女用手背抵住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是啊,嫁给我这样的人,可随时都会当寡妇的……”他自嘲地一笑。
“我……我不当寡妇。”她哽咽着,不管不顾地回过头来,狼狈不堪,“你……你快点好起来,我才嫁给你。”
他终究没有好起来,只是独自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她也始终没有嫁给他。明明只是那样一个柔柔弱弱爱掉眼泪的小女孩,却为什么就是那么那么地难以把握?难道真的是因为怕变成寡妇吗?
那个冷漠淡然的白衣医者,那个沉默寡言的诡异杀手,都不是他的小姑娘。
温暖的午后,暖而旧的光线里,白衣女子抱膝坐在廊下,单薄地像一枚小小的纸人。她定定看了他许久,才缓缓攒了个惨淡的笑容,“清夜,你抱抱我。”
那才是他的苏叶。
天地间蓦然空无一物,巨大的空旷转瞬淹没那个单薄的身影,墨一般的浓云从天边滚滚而来,一寸一寸染过灰白雾霭。
待雾霭再次散开,枯死多时的枝桠挂着凌晨时分最后一抹月色,高树落尽了叶子,灰暗的天空云气隐约。
在杂草深处,他看到了那座隐匿多年的荒芜坟墓。无名的藤蔓爬满了墓碑,墓碑看不出材质,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褪了色,黯淡地无法分辨。无论曾经多么触目惊心的殷红,最后,都会在岁月面前褪淡成无力的苍白。
在这个世界上,也唯有他,还记得在某座深山里孤零零的这块墓碑。几个黯淡字体的轮廓,真真切切是他的笔迹。
他一直都忘记了。原来八年前,当他写下最后一笔起身离开的时候,苏叶于他而言,就永远地烟消云散了。
·
(锦行)
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
锦行将泡好的一盏茶,放在窗边的案几上。茶烟袅袅里,墨衣女子放下手中的书卷,对她微微笑了笑。
“先生。”
每次她一开口,那个单薄的剪影便像雾一般悄然散开。一夜复一夜,一次又一次。
落声一直很嗜睡。遇上糟糕的天气,她醒着的时候会更少。但她唯独喜欢江南的雨天。下着雨的时候,她常常会无声地靠在窗台上,望着薄薄的雨幕。
锦行从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直到在壁城的那一次。先生在痴愣中,恍惚念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清夜。”
第二天,她便伤在那个人的剑下。
为了交换归墟咒印,她以身犯险,被关在紫云湖底整整两个月。事后,不过只是悠悠叹息了一句,“错过了紫薇的花期,真是可惜。”
那个人一句话,她便摘下面具,换回女装。笑得眉眼弯弯,“嗯,我要成亲了。”
那个人消失无踪,她站在蔷薇花下苍白着脸安慰自己,“延后十日吧。他有要紧的事。”
那个人一声不吭便弃了婚约,她在屋里坐了一天一夜。
重新戴上面具,成为落声。为的,是苏薛两家的颜面。
强弩之末,不惜金针封脉强行出手。为的,是她和泠然。
落荒而逃,埋骨幽谷。为的,是那些在乎她的人。
她对每一个人都温柔,唯独忘了自己。
她唯一为自己争的,是一份遗忘。
她说,“我现在很累。你们安静些,让我好好睡一觉罢。”
先生,我知道,也只有我知道,你有多想忘了那个人。
*
(苏叶)
愿意醒来么?
我不知道,大概,不愿意吧。
我的这一生很短,短的只容得下四个人,苏芷,清夜,蓝翎和小白。
当看清九风手里的丝绢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苏叶,你终于该忘记他了。我坐在窗边想了一整夜,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占据了我四分之一的人生,如果想要忘记他,我必然要先忘记自己。
十三岁,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在海边跳房子玩,跳完一栋之后,转身看见有陌生的少年站在不远处,笑容戏谑,“你一个男孩子,怎么玩女孩子家的游戏?”嗯,这就是他对我说得第一句话。我摸着因为长头虱而剪短的头发,翻了个白眼回答他。
当天晚饭前,苏芷唤我去大厅见客。那个白瞎的少年就坐在次席,正端起茶盏埋头喝茶。苏芷向他介绍,“这是舍妹,苏叶。”他抬眼看过来,随即“噗……”地一声,茶水喷了自己一身。
薛清夜让我刻骨铭心地领悟了一个词——尴尬。我相信,我于他也是一样。
十四岁,我第一次来葵水。
大半夜爬起来,翻遍了医书也找不到对应的症状。因此吓哭,抱着来拖我起床的少年不松手,眼泪鼻涕各种往他身上蹭。最后,他忍无可忍,红着脸咬牙切齿地告诉了我关于葵水的全部知识。事后,我赏了他一句:“登徒子。”
十五岁,我第一次目睹死亡。
他挡在我身前,用手捂住我的眼睛,“别看。”因为我的无能,数百名感染瘟疫的病人被赶入一个洼地,而我只能透过他的指缝模糊感觉到漫天的火光。那一场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也烧尽了我年少时所有的恐惧。
我第一次为人所伤,对方是个孩子,凶器是一柄锈钝匕首。我扶着墙去汤婆婆的馄饨摊找清夜,吓坏一干路人。清夜一边骂我,一边撕了衣角替我包扎,然后背我回府。我因为伤口太疼,在他背上哭得稀里哗啦。第二天,全城的人都在传,少城主光天化日之下强抢良家妇女。
十六岁,我第一次杀人。
鲜血溅在脸上,尚有余温。我来不及害怕,转身扔了剑跟着东霓沿河一路找寻清夜。仲冬之月的冰河,彻底伤及清夜的心脉。
十七岁,我第一次受人跪拜。
一大把年纪的二爷,跪在那里要我这条命。对于这点我心里一直很不舒服,搞得好像我跳崖自尽纯粹是因为他那一跪,我的命还不至于那么不值钱吧?
二十四岁,我重回江南。
遇见的第一个人,依旧是薛清夜。可谓阴魂不散。
二十六岁,差三个月,我第一次被弃婚。
“回去告诉薛清夜。苏叶自当,如他所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抬头望见,一双云雁飞过高远天空。
从此山水不相逢。于他于我,都是最好的。高傲如他,由他的属下转达我的建议,他必不会说一个“不”字。或者,他根本求之不得。
十三岁到十七岁,四年时间。我看着他从薛少城主一步一步成为织月楼主,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织月楼主薛清夜,对任何人都一样绝情,包括他自己。
和我这个苏家二小姐在一起,有很多好处。落谷落声,有令枯木逢春之术;苏家虽然只剩个空壳,但百年声望依旧;上通朝廷下达武林的萧家大当家萧雨凡会成为他的连襟。最后一点是,他恰好爱我。
他爱我,我从未怀疑过。但是,又如何呢?江山永远比美人重要,更何况我还算不上美人。他弃婚,不过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仅此而已。我将婚期延后十日,已是死皮赖脸。而他的回答,不过一块丝绢。简洁明了,是织月楼主一贯的风格。
原本我该像十三岁时那样,翻个白眼回答他。可事实证明,我远没有少年时那般潇洒。苏芷说得对,我是苏家的女儿,生来就注定不能嫁给他。这是命,怎么争都没有用。结局不过一个。
死了也好,死了干净,死了我和薛家就两清了。老城主的惨死,薛清夜的旧疾,那些薛家死士的性命,我用我的两条命以及苏家二小姐的声名来偿还,够吗?
不够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