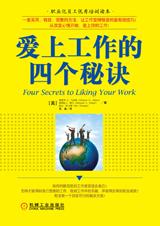耶路撒冷的四季(完结)-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似乎淡定自若,并没有第一次出席大场合的局促紧张。不时拿起桌边的杯子喝一两口水,随意翻阅着手边的资料。越来越怀疑他的身份,为什么会在此时出现在Nahum的位子上?
迎视投来的目光,很友善,又似乎夹杂着戏谑的笑意,很快转开了。大使正在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早日打破军用合作的僵局,他听到,盖上了手中的文件,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什么。
以方首脑接过大使的话,做最后陈辞。让的视线,却一直跟着少年。他写好纸条递给了身后的司仪人员,又埋头不语。嘴角,收敛了情绪一本正经起来。
他是谁!要干什么!
会议结束,双方会谈人员起立,大使与外长握手的瞬间,本该礼貌性告别,却见微微低头,交流了什么。动作太快太隐秘谁也没听见。面上一切如常,宾主各自带队离席!
会后转到休息厅,晚上的酒会和签约会场已经布置完毕,特别供休息的区域放着酒水饮料和速食餐点。
顾不得和熟识的官员打招呼,回到会议厅。工作人员正在收拾整理,Nahum座位的名牌已经被收走,留在位子上的只是几张白纸。到司仪处拿下午的会议列席名单,Nahum在名单的后面,和前几天的记录一样。
再回休息厅,穿梭在人群里寻找那个身影,抓住身边的使馆一秘带话给大使。
一定有什么不对,那少年已经不见了,搜索着银色镶钻的领饰,只在休息厅角落看到拿着酒杯的同声翻译。
“大使和公使呢?”
“散会后跟以方几个代表进了小会议室。喏,就是那间。”
“谁跟着!”
“武官和以方的翻译,不用担心。休会了放松一下,喝一杯,晚上签完协议今年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推开酒杯,顺着隐秘的侧廊走到小会议室,门口有几名持枪的军人把守,只好退回外面。
谈判桌边的少年,老城里的水果商贩,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打电话给饭店,天放和大家都在等消息,不好直接问她,只是嘱咐最后的关头更要格外注意。
大家已经听说了一些消息,口气都很放松,说是等着他回去庆祝。也许只是自己想太多,甚至认错人,毕竟老城的那次短暂相遇没来及端详清楚。
走回空空的会议室坐在窗边,拿出西装口袋里的小盒子捧到手里轻轻打开。应该安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事。低头看着掌心,那对特意为她订做的戒指躺在丝绒盒子中央。明天这个时候,就套住她一辈子了。
打量盒子里的两枚戒指,希望她会喜欢。比起腕上的小瓷猫,少了些可爱,可又多了一份厚重。大卫星中镶嵌一圈碎钻的是订婚戒指,纪念从这个国家开始的感情。而一枚新月托起晨星的,是结婚戒指。璀璨的钻石替代了原来星星的位置,在清真寺的那晚,他们一起经历过生死,交换了承诺。
把两个民族最吉祥的符号带在她身上,守护来之不易的婚姻,以后的路还很长。
求婚时太匆忙没来及送,今晚一切结束以后,要带她去老城的中央,在第一次一起走过的哭墙广场重新求一次,求她给他作一辈子太太。这一刻真的到来,并没有想象中紧张,只是迫不及待,如果不是少年出现,现在已经抛开酒会回饭店了。
只要合约一切顺利,明天一早就去市政厅办手续……
“让,想什么呢?不喝两杯?”一时出神,没察觉背后有人,盖上盒子收回口袋里,看到以色列外办工作的熟人。
“刚好找你,今天下午的会Nahum怎么没来?”
“是吗?没注意,刚刚还看见他。”
“在哪儿?”
“大堂,和家人一起走的。”
是那个短发的少年吗?
“是他儿子吗?长什么样子!”
“干吗这么激动,会谈已经结束了。”对方笑了,举着杯子啄了一口,打趣。“不是儿子,Nahum的大女儿,也许你们没什么机会见,这两年合作又没谈成。儿子去世以后,Nahum做事特别低调小心,很宝贝大女儿。”
Bluma也来了?
“今天他小儿子来了吗?下午会谈时看见座位上坐着个十几岁的孩子。”
对方皱眉,摇摇头。“Nahum只有一个儿子,可惜去年出事没了。现在就剩下两个女儿了,小女儿还小,以后生意可能都要大女儿接管,今天就是带大女儿过来的。”
“可座位上的男孩……”
联系到一起,心里一惊。
“哦,也许是Bluma吧,大女儿叫Bluma。听说儿子死后他没再按老教义带女儿,毕竟以后要继承事业。你一说,远处看Bluma确实有点像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短短的头发……”
想不明白,巨大的恐惧瞬间笼罩在心里,好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顾不得眼前的熟人,也来不及等大使出来商量,冲出宴会厅。
难道这么久一直认错了人,下午会议室里的男孩是Bluma?那哭墙广场见到那个长发女人是谁?和庄非一起在老城受袭的女人又是谁?
周密计划了那么久,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接近,难道,是一个圈套?
她在旧城的犹太区被一群蒙着头巾的阿拉伯男人打断了肋骨,他们有枪,那水果少年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带他们去了窝藏的旅馆。每周有几次,她会和一个自称Bluma的女人在学校的三明治吧见面,那女人自称也喜欢Ofra Haza。哭墙广场上,长发女人背后跟了很多侍女,Nahum没有出现,只在地下教堂回廊祈祷,照片的背影一片模糊……
闪现在脑子里很多错乱拼接的画面,庄非说过的,朝纲和牧说过的,照片,音乐,谈话,静默……
哪里错了?
一年前大儿子死在旧城,遇刺之前,他约见了使馆的工作人员。
四年前,方舟代替自己去加沙的军工厂押运物资,和那批武器都消失了……
国会附近的街道在戒严,街上巡逻的军人很多,夜空里回荡着某种余响,像是警报。在车场把使馆的司机抓出来,跨进车里急速驶离。
拿手机的手有点发抖,但是必须打过去。
“天放,大家都在吗?”
“哦,除了顾洪波和庄非,其他人都在呢,他们应该也快回来了。”
“去哪了!”额角炸开,震怒。
“带她回希伯来大学了吧,说是很快就回来。好……好,我这就让牧去追回来,走了……呃,大概半小时……”
“追回来,无论如何,马上追回来。” 用嚷的,声嘶力竭。
调转车头,冲着学校的方向开。打她的手机,光线太暗找不到号码,特别联系的键按下去,没有回应,顾着方向盘又试了一次。
迎面闪过车灯,打轮,手机没握紧掉到座位下面。Shit,够不到,只能把油门踩到底。
终于到了,市区内的校区,最安全的校区。停稳车子摔门下去。
校园里正在做住棚节义演的准备活动,从校门到广场密密匝匝的学生。草坪中央的屏幕上转播着本赛季的足球决赛。找到她提过的服务楼,直接上二层。
并不显眼的三明治吧,几个客人在散座上看书。收银台边的收音机里是电台音乐,配合着操场上的节日气氛。
转了一圈,她不在。踱到阳台上,面对着夜色中的草坪。再打过去,电话通了。
上帝安拉保佑,通了!
广播里的音乐节目突然中断,插播的新闻传来。
“二十分钟前,希伯来大学山顶校区的多功能楼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警方已经封锁了整个山顶校区。在此次爆炸中,至少有三十名外国留学生遇难,已核实有五人来自美国,两人来自英国,一人来自日本,两人来自中国,两人……由于遇难学生身份现在还无法确认,警方正在……”
屏幕上的球赛切换了,记者拿着话筒站在一片燃烧倒塌的废墟前。
握紧手机,这次不能掉了,车钥匙上拴的小铃铛丁丁响,那是她的小母猫。
快接,快接!
熟悉的,反复的,噬人的铃声……
101
顾洪波是第二天下午找到的。电话从使馆转到代办处,天放接起来,一声不吭。在以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亲耳听到这样的消息。
“让,洪波……找到了。”
颤抖的声音意味什么再清楚不过,扶着椅背站起来准备去接电话,迈开步子又退回来,让自己冷静。
坐在角落里太久了,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也是麻的,从半夜回来浑浑噩噩到现在。
好在不是她,虽然很痛心,又庆幸不是她。
电话依然能打过去,但是没人接,不知拨了多少次,希望是海法那样的状况,可找到顾洪波的消息,又破灭了某种坚守的希望。
伤亡的名单不断增加,昨晚赶到封锁的主校区,拿着使馆的外交照会好不容易进去,面对一片废墟,头一次不知所措。
还没扑灭的大火卷着热浪,秋夜里弥散着焦煳味。很多学生围在警戒线周围,有人哭,几种语言交汇,叫着陌生的名字。
废墟周边布满挂荧光带的救援人员,担架上抬着伤员,看仔细,是巨大的黑色裹尸袋。死亡太近了,恐惧到心里破了一个洞,怕她掉进去。
试图闯,护照抓得变了形,嚷,推搡拥过来的人,终于闯到倒塌的房屋近前。手上抓着腥潮的泥土,残砖断腕,仅凭两只手挖不过来。
不是第一次见到血腥,只是这次彻彻底底被击倒了。被警察推出警戒线,站在警戒线外注视着抬出的担架,那条黄色的带子,几乎搅断了。
那时候不希望见她,即使平安无事也不想她看那些黑色的袋子。更不可能……那些负担不了她的生命,绝对不可能!
天亮时回到饭店,走到角落,在椅子上坐下再没起来。
心里怀着期望,不会扑灭,反复播她的电话,宁可听到无休止的响铃,好像她在忙碌中,几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以后会打回来,也或者像海法时的情形,去医院帮助受伤的人,一场误会。
放下电话走回角落里,伸进西装外套,摸到坚硬的棱角。戒指盒子,装着好几天准备要在关键时刻送她的,演练着该说的话。心想着总要亲手给她套上,只是时间问题。
指尖被什么扎到,摸出来,是支干枯的木本植茎,没有叶,只剩下粗糙的刺。什么时候刮到衣服里的,刺在肉里,疼得踏实一些。
“让,洪波的遗体已经送到医院,警局让我们派人去一趟。大使他们都回特拉维夫了,公使交待善后的事情要及时处理,使馆会尽快派人过来。”
没有抬头,把掌心的干支折断,应该果断处理事情,把一切安排好,可脑子里太乱,只能放弃。摆摆手,想安静的一个人待着。
牧没有马上退开,迟疑一下,又问了一次。
看得出他心情极差,庄非还没有找到,但是顾的后事不能不开始料理,很多事情都要人做。谁也没想到谈判刚结束会出这样的事,昨晚被派去追,还没开上山,车被突来的震动冲得歪到路边。
现场惨不忍睹,几乎找不到完整的遇难者,袭击者引燃了楼里的燃气管道,几层的大理石老楼整个坍塌,周围院系的门窗玻璃一概震碎了。
庄非,也许……
抓着发根,够使劲了,还是不疼。听到牧又在催促,愤然起身抓着他的领口逼退到门边。
“你去,现在就去!”
颓然放开,知道自己失控了,又回到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