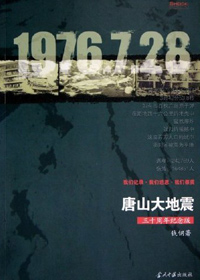大地雅歌-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树,从南面的雪山垭口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像峡谷底的几把绿伞,因此来往的马帮都叫这个地方核桃树。
我是这里最老的原住民,我并不只是几棵古树,也不是在这附近山上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傈僳人,更不是擅长在雪山下放牧、在河谷地带种地的藏族人,或者某个赶马为生的过客,或者某个在山洞里闭关修行的喇嘛上师。哦,不,不,那个年代,做一个人太难,需要承受太多的苦难。我情愿只做一个风霜雪雨、沧桑演变以及人间悲欢离合的见证者。路过这里的马帮都知道我,他们对我深怀敬畏,给我烧香,念经,甚至磕头。尽管他们谁也没有见过我。
那么,我是一个本地神灵吗?或者,我是洋人传教士所说的天主大神吗?
不会告诉你的。这是我们的事情,你们不可随意问。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个村庄的历史,比后来你们听人们说的,听人们唱的,包括看别人写的等等,更生动,更真实。
过去,马帮到了这里一般都要宿营,因为第二天,他们就要从前面约三里地的渡口过澜沧江。这个渡口叫“鹰渡”,人、马、货物都像老鹰一样从澜沧江上飞过去,靠的就是横跨在江两岸的那根藤篾溜索。人、货物挂在溜索上,利用溜索一高一低的落差,夹风带云,“哧溜——”一下就过去了。麻烦的是骡马,得用绳索绑住它们的身子,一匹一匹地吊过去。当它们被挂在溜索上时,四蹄乱蹬,目光惊恐,伸长脖子绝望地望着湍急的江水——当你们看到这一幕,你也会觉得,即便是做一匹牲口,也不比做人好多少。光是过一次溜索,一支一百来匹骡马的马帮队也得过上一天。
我总是在暗中祝福那些过溜索的人,必要时也会给予一点帮助。比如,有的家伙,喝得醉醺醺的也要过溜索,都滑到对岸了还不知道减速,眼看着就要一头撞在岩石上,这时我会一把将溜索上的人拽下来,扔到江边松软的沙滩上。
就像雪域高原的其他地方一样,这是一片宁静祥和的土地。天地间除了人的歌唱,鸟的鸣啼,牲畜和野兽的私语外,还可以听到煨桑的青烟的祈诵,经幡飞舞的祈诵,喇嘛们发自丹田深处的祈诵……啊,这是一片充满祈祷的土地。雪山、峡谷、森林、江河、湖泊以及它们的子民――人和百兽、牲畜,都在向主宰一切、并恩赐一切的神灵们祈诵吉祥平安。藏族人和他们的神灵在大地上和睦相处已经上千年了,没有谁比雪山上的神灵更高大,没有谁比佛陀的慈悲更宽广。直到有一天,洋人从喜马拉雅山那边打了过来,许多本地的康巴好男儿都被征调到后藏打洋人,但是他们都被洋人魔鬼才拥有的法器打败了,那是洋人的大炮,黑烟升起,红光一闪,冲锋陷阵的康巴马队便被炸得人仰马翻了。那场战争后幸存回到澜沧江峡谷的康巴武士说,洋人是“骑着炮弹进来的,”当他们肮脏的战靴玷污了圣城拉萨洁净的土地时,洋人就成了魔鬼的化身。。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教堂村志(2)
澜沧江峡谷的洋人也是“骑着炮弹进来的,”不是指他们在进来之时,而是在他们来到藏区之后。开初,他们是一些谦逊而又有礼貌的人,和喇嘛们的关系也不错。可是当喇嘛们发现这些洋人是一些“无耻的小偷”时,喇嘛们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们不偷别的,专门“偷窃藏族人的灵魂。”而喇嘛们一向认为,藏族人的灵魂是由他们来照料的。清朝末年,澜沧江上游地区燃起反抗洋教的烈火,许多教堂被焚毁,洋人都像驱赶魔鬼一样被赶走了。喇嘛们在每个雪山垭口插上了众神胜利的旗帜――五色风马旗,“神胜利了”的呼喊声响彻雪域大地。
但在一个云雾笼罩一切的黑色日子里,洋人骑着炮弹回到峡谷里来了。人们传说一个洋人像驾驭一只鹰那样,骑在夺人魂魄的炮弹上,把死亡的阴影随处播撒。他的身后跟随着朝廷的军队,他说“这里那里”,“这个人那个人”,军队的炮弹就雷霆般倾泻下去,不论是牧歌悠扬的牧场,炊烟袅袅的村庄,还是金碧辉煌的寺庙,洋人骑着炮弹所过之处,仅留下一片废墟和哀号。
这时喇嘛们才明白:洋人不仅带来了偷窃藏族人灵魂的宗教和十字架,还有骑在他们胯下的炮弹。
炮弹是那个时代最有力的法器,不是用来对付魔鬼,而是成了宗教纷争的裁决手段。洋人的教堂被捣毁了,他们就骑着炮弹到处巡游,寻找新的地盘。让雪山上的神灵也感到费解的是,朝廷的军队帮洋人打了胜仗,却还要赔洋人大笔的银子,让他们在藏区重新选地方建盖自己的教堂。而那些被打死的喇嘛和被炸毁的寺庙,朝廷却不管不问。
在峡谷里人神共怒的时候,洋人来到了核桃树,发现从这里沿马帮驿道南下十天的马程,就到了大理。那里虽然是白族地区,但由汉人统治,洋人传教士时刻需要汉人军队的炮弹保护。而前面过了“鹰渡”,经阿墩子往北翻过卡瓦格博雪山垭口,就进到了西藏地界;往西南方向翻过斯纳雪山,马帮们告诉他们,穿过怒江峡谷可以走到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
于是,一个叫古纯仁的法国传教士,他的胡子已经飘到肚皮上了;更早以前他从我身边的这条驿道走过时,还是一个年轻人,现在他老得连上一个坎都要喘气。喇嘛们私下里说,当年就是他骑着炮弹召来了朝廷的军队,要不是他早年间对那些麻风病人有慈悲心,这个让人不知道到底是魔鬼还是人的家伙早就被喇嘛们的毒箭射杀了。我不明白这样的老人为什么不想回家。那天他用手中的拄杖一点说:“我要让这里成为教会的一个连结印度、缅甸、西藏传教线路的宗教庇护所。”
什么叫庇护所?是马帮们歇脚打尖、遮风挡雨的驿站吗?他说的印度和缅甸,连我都没有去过。他们是做什么买卖的呢?竟然要跑那么远。
洋人传教士跟我看见过的那些在马帮驿道上一晃而过的陌生人不同,他们喜欢上一个地方,就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不会在感叹一句“这段峡谷的路真像魔鬼的肠子!”或者说“看啊,那开到天边的花儿!”然后就继续赶路。洋人传教士们刚来时,也被我的雄浑艰险所震慑,但他们感叹完后,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园了。不仅如此,还要把他们故乡的一切,从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到他们的神灵,都要照搬过来。
从那个古神父来到这里住下后,我这里就开始慢慢热闹起来了。每隔几年都有一些高鼻子、蓝色眼睛、浑身长毛的外国神父到来,法兰西国的,意大利国的,瑞士国的。我从他们的交谈中慢慢知道了他们都是从大海那边,乘坐一种可以漂在海上的房子过来的。他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好像我们这里有什么宝贝令他们着迷一般。只有古神父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现在是两个瑞士国的年轻神父罗维和杜伯尔陪着他。
教堂村志(3)
这是两个充满活力的家伙,他们总有一些让我不明白的东西。罗维神父是一个滑雪高手,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滑雪板在雪坡上飞翔,就像在雪地上长了翅膀的人,只是那翅膀不是长在肩上,而是脚下。一天他们拿一个可以蹦蹦跳跳的圆圆的东西,在刚收获过的青稞地里踢来踢去,不知是谁惹他们不高兴了,还是又在玩什么阴谋。我总是对这些和我们不一样的洋人心怀戒备。
不过,应该承认,他们是一些不计酬劳而又相当有耐性的人——一定程度上说,可以称得上是勇敢的人。我们的神灵起初并不欢迎他们,给他们制造种种麻烦,用雷霆击中他们的房屋,下泥石流冲毁他们的道路,甚至还放出魔鬼的瘟疫,让他们患上疟疾、伤寒。藏族人碰上这样的灾难,一般只有转求下一世往生一个好去处了,但外国神父总有神奇的药物驱赶我们放出的瘟疫,还搭救那些也染上瘟疫的人们。就在去年,魔鬼的口袋里放出像乌云一样宽广浓厚的蝗虫,吞吃了峡谷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后,这些洋人喇嘛就从外面用马帮运进来大量的粮食,拯救那些快要饿死的藏族人。他们的慈悲心有时让我们的魔鬼也下不了狠手了。
澜沧江冲刷出这段峡谷以来,我都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在洋人传教士手里变戏法似的冒出来了。那天我从古神父的茶杯里闻到一股怪异焦煳的味道,我听见他对自己的仆人说:“啊,今天的咖啡煮得不错。”于是我明白他们的茶叫咖啡。他的房间里有一种会唱歌的盘子,他们叫留声机,唱出的歌声谁也听不懂。有一种曲子,古神父特别喜欢听,叮叮咚咚的像雪山下的幽泉发出的声音。后来我从他们的谈论中知道了,这是一个叫肖邦的人写的曲子,用一种叫钢琴的东西弹奏出来的。说实话,尽管我听不懂,但我很喜欢。
无论是咖啡、帆布浴缸、折叠椅子、牙刷、爽身粉、奎宁,还是留声机、钢琴、望远镜、指北针,这些东西都不足以改变核桃树这个地方缓慢、悠闲、宁静的岁月。核桃树还是核桃树,仅仅是个马帮歇尖的小驿站。当古神父说他要在这里建教堂时,我就像一个大姑娘,一夜之间变成别人家的媳妇了。
仅仅两三年的工夫,一座我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大房子就矗立在峡谷里了,它有一个高大巍峨的钟楼,后面是矩形的经堂,里面有彩色壁画的穹顶,彩绘玻璃——一种像薄薄的冰的东西——的窗户,明亮辉煌的神龛,以及上面供奉的我不知道的神灵——一个近乎*的男人,挂在十字架上,他们天天都膜拜他,每七天还做专门的法事;还有一个怀抱孩子的妇女,长得很美很温柔,像一个家有大群牛羊的藏族妇人。这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看上去跟普通人一样。这个大房子既不像寺庙,也不像藏族人的土掌房。在峡谷里,它像一个孤独沉默但又很野蛮的巨汉。
核桃树开始被改变,一些信仰洋人宗教的人们开始陆续来这里定居——他们是藏族人、汉族人、傈僳族人、纳西人、彝族人。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你信奉洋人的那一套,神父们都把他们接来这里,分给他们地开垦,送给他们一本叫《圣经》的经书,就在这个地方天天念叨;还有一种这里从来就没有生长过的植物——葡萄,也被神父们从他们的国家引种过来,还在教堂后面开辟出一块地专门种植,然后,一种藏族人从来没有喝过的酒——葡萄酒,取代了人们天天都要喝的青稞酒。它是红色的酒,红得像人的血,神父们说这是耶稣为他们流的血;还有一种小小的面饼,神父们每次做法事时都要庄重地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分给众人吃。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人们,去吃代表别人身体的祭品?平心而论,他们是一些和喇嘛上师们一样具备慈悲心的人。
但我看出来了,洋人神父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相信他们的神灵可以救人上天堂,而喇嘛上师们说的那些道理,都是错的。可麻烦的是,喇嘛上师们也认为:洋人神父是魔鬼的化身,藏族人的苦难,离不开他们的慈悲,洋人神父的说教,只能把藏族人引向地狱。
由于洋人的教堂像一根钉子一样地扎在我的身上,很多藏族人把我看成了他们眼中的钉子,他们连去拉萨朝圣都不走这里的驿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