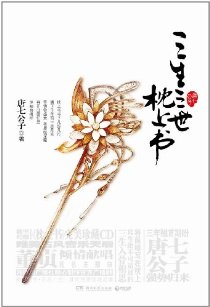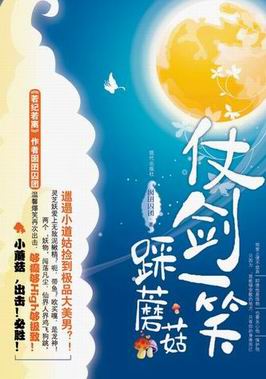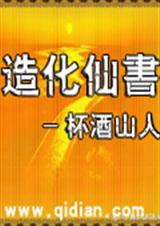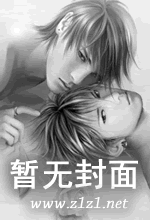私语书-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序
细节处,方能勇敢
黎戈
我有很多银饰,但还是在继续收集,口袋里一有余钱,就去那家尼泊尔专卖店转悠——泰银雕琢过度,有点闺阁的脂粉气;藏银样式张扬,气势逼人,表演味太浓,和东方人平淡的五官也不和谐;尼泊尔银比较中庸,为我所爱,相熟的店主看见我,就把银器端出来给我看。
宽幅的银镯,形制接近于古代的“钏”,上面有大朵大朵丰肥、绵延的莲花,又蔓又枝,抵死缠绵。也有线条素丽的虾须镯,一大串带在手上,配上莲步摇、罗裙摆、红袖招,颇能造点声势,可是我又嫌它啰嗦,最后看中一只镶银的木镯,木质的部分嵌了两颗绿松石。心中忐忑着:价格不便宜,和全银的一样,而且尼泊尔银成色虽好于藏银,至多也不过是七五银,木头又易腐,一边犹疑一边继续试戴,手腕太细,最小号的勉强挂住了,店主说“嗯,这个,可以便宜点给你”,嘴巴向我努动一下,这才看见上面有个小小的、微微起伏的结疤。
之前还在犹疑呢,一下子就决定买下它了。我爱不完美的事物,不完美就是识别度,之前它只是木头镯子而已,结疤之后它就是我的了,它们的杂质让我觉得亲,生命之大美就是杂质之美。“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从来也不能爱上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我觉得他们真是乏味啊。本雅明说:“一个男人会爱上一个女人的软弱、怪念头、她脸上的斑点、皱纹、寒酸的衣着、崴着的步子……”我是个女人,可是我的想法与他雷同,我总是爱上男人的卑琐、畏怯、孩子气、矮小、疲劳感、疲塌、粘滞、没翻好的一个衣领、丑丑的步态、难听的口音,像花鸟市场里被挤到角落里的、最丑的那只小小狗,让人心生怜爱。栖息在他们的缺陷处,我才觉得安全。那是我们的暗号,帮我找到“我的”他们。
又试了好几条裹裙,浓,热,满,我是说上面的花饰,修身又冶艳,大家都说好看,可是我想不出用什么样的碎步来配它,它们真是美啊,如果穿在一百年前的印度女孩身上,她们长着蜜色的皮肤,浓重的眉睫,住在和男人隔绝的内院里,在出嫁之前,连视线都没有被污染过,每天早晨她们起床汲水,从延至水面的石阶上走下去,洗个凉水澡,顺便摘几朵莲花插瓶,开始身心俱净的一天。她们的自矜和从容,才配得上这样盛大的狂欢气息的裙子。
或者买一条回去,用图钉钉在竹帘上,聊作装饰,好歹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卑琐可以,生活态度不能卑琐。可是我最大的享受也不过是:点一炷伽南香,拖干净地板,穿一条洗旧的睡裙,在清风徐来的阳台上看《诗经》,想象自己在河边走,空中像云库一样在飘絮状物,那是某种植物的种子,菖蒲的清香从水面上飘过来。还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少女,她们的歌声从上游传过来。
我吃的不多,睡的很少,几件棉布衣服就可以过一个夏天,精神食粮还有一部分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过去我会很想念那些我在市面上买不到的书,还完以后,还会把它们再借出来看看,现在好像也比较平和地看待离合了。我很耻于我是个物欲淡薄的人,泰戈尔说他小时候过的是微贱的生活,顶多是粗布口袋里能摸到一两个糖果,所以长大后,每个梨子他都能吃到核子还觉得甜,我没有经历困窘的日子,对物质亦有温热的爱,可是要我踮起脚跟、奋力地争取它们,我很怕累着自己,肚子很饿的时候,两块五一碗的凉皮,或是一顿大餐,它们给我的满足度好像也差不多。我再也不能像二十岁那样,对每个牌子都能倒背如流,为一件买不起的衣服失眠到天亮。现在我还是会奢侈,在某些细节处,比如一个镯子,比如为一个人,恍惚片刻,那是波上千层浪中的一点白、长夏草木深中的一丝碧,在日常生活的洪流中,它很快就会被裹挟而去,转身不见。
微物(1)
枕头
最著名的枕头,当然是《枕中记》里那个。赶路的书生,蒙老道热情招待,俯就枕头时,发现枕头上的孔越来越大,渐渐恍惚,身入其中,做了一枕黄粱好梦。像我这样专好留连细节的人,就一直在琢磨那枕上的洞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因为书生用的是瓷枕,为了防止箱体在烧制过程中受热变形,一般会预留两个小孔在枕侧。后来读笔记小说读多了,发现五代和唐宋之人,多用硬枕,瓷质居多,所谓“残梦不成离玉枕”、“玉枕钗声碎”,指的都是瓷枕。因为古代女人就寝时,会松松地挽个睡髻,上插金钗,金钗和玉枕皆硬物,相撞时才会“钗声碎”、“敲着枕函声”什么的。当然,枕头上的动作,直接造就了这些活跃的声效,所以,它也是有性暗示的。而且,比什么“尽君一夕欢”、“时闻款款娇声”要含蓄隐晦得多。
一直在想,古代人好像都不怎么畏寒似的,你想想杜甫白居易他们,结庐造屋,都是木头墙体,茅草顶。顶多拦一道屏风,挂一个竹帘。后来看资料说,唐代时,全球气候是偏暖的。气温远高于今时。啊,这才明白,老杜老白他们为什么好瓷枕、竹枕、石枕——有种石枕是桃花石做的,上有天然石纹,隐约如花瓣坠于春风,这个意象真是太诗情了。到了明清,士大夫阶层的享乐要精致得多,你看史湘云醉卧花荫的芍药枕,还有宝玉用的那个,填塞了各类干花瓣,枕上无甚奇特,内里落英缤纷。芳气满闲轩,枕上好梦成。呵呵。至于用干茶叶填制的枕头是自古就有,其功效雷同于李时珍所倡导的决明子枕头,就是至老明目什么的。其他植物参与的枕头还有:清热凉血的鸡冠花、补肝肾的女贞、舒缓神经的薰衣草,毋论其药效大小,它们都好算是一种积极养生、向光的生活态度。
还有一种枕头取向,类似于精神养生,比如文震亨的“书枕”,用纸三大卷,状如碗,品字相叠,束缚成枕。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此人,士子味道太浓稠了,文章架子也大。这种“书枕”固然风雅,但是,能舒服么?我自己用过一个硬枕是荞麦芯的,触感生硬咯人。不管它宣称有什么明目助眠之功效,我也把它直接改制成靠枕了,这下化劣势为优势,它的生硬,摇身一变成硬朗,躺着歪着靠着,皆有所恃。呵呵。还给爸爸买过磁石枕,后来,他老人家的肩周炎确实治愈了,可是又得了眩晕症。因为睡硬枕老空悬着头的缘故。再后来,这个功过皆半的家伙,被我们塞进衣橱里,永不见天日了。
这些也罢了,居然还有一种枕头,是专为与肉体的软弱求安对抗的,比如北宋的司马光同志,用一个小圆木作枕头,睡觉时,只要稍动一下,头从枕上滑落,便立即惊醒,醒来之后继续发奋读书,他把这个枕头取名为“警枕”,这种行为艺术,与头悬梁,锥刺股,是一个系列的,即以身体自虐的方式,来谋得学习的积极性。个人觉得还是李渔的态度比较切实,且顾及身体舒适度。“爱精美者,一物不使稍污。夏凉冬暖即可。”是是,我不停地点头。洁净,素朴,简静,耐用,纯棉质地,触感柔软,带着亲切的体味。我对枕头的要求,和对男人差不多。想起来有个希腊女人,思路估计和我是重叠的,把枕头设计成了一个男人的臂弯。想想看,孤身返家的冬夜,如果有此物为伴,其滋味如何?
微物(2)
从细枝末节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性。周作人偏好日式居室,四壁萧然,几个坐褥,即可安住。只一小几在窗下,置一壶清茶,自斟自饮便好。卧具是收在橱里的,不占地方,颇有萧索之意趣。这个我也喜欢。没有物欲拖累的心,才是轻盈的。还有的枕头,情意浓浓,梁实秋的太太,啊,彼时还是他未婚妻,在他留美前,特地绣了一对枕头给他,上结了好多同心结,暗喻其情坚贞不移,其爱蜜意和美,有一次,梁伏枕一梦香甜,感而作诗一首,就是那首《梦后》,哈哈,怎么能想象,这就是和鲁迅对骂笔战、热血勃发的那个桀骜男人。“寤寐难眠,辗转伏枕”,可是这个伏枕多甜蜜。后来枕套的丝线褪色,图案模糊了,他还留着……这才是真正的爱人枕。
要考究这类物质细节,最好在有恋物癖的作家文字里找线索。张小娴写过一篇小说,里面有个家居店小职员,暗恋一个男医生,卖给他的枕头里,她偷偷缝进了一封情书。“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把枕头用烂,看到我对他说的话。”自然这是不可能的。希冀再华美,也只是一枕绮梦。但是正如我的朋友P同学所说,暗恋就是这样,“一辈子不出手,是最高贵的姿态”。至于张本人的枕头态度,哈哈,有阵子我看她给AMY写的专栏,里面详尽介绍了她的物质生活,包括杯子、台灯、内衣裤等等,都是附着实物图解的。她用的枕头是一款意大利丝绸枕头,专程去买的,旅途中都带在身边。“女人一定要备这种枕头啊,它能让你永远都不长皱纹!”哎呀呀,实在是聪明女人。文字里,浪漫得好像逛玫瑰花园长大似的,在生活中,却尽可能善待自己。小说里高蹈得出尘,现实中低调得务实。
张爱玲当然是要写实得多,她笔下的枕头,是香港沦陷时,女学生用来偷运大米的,结果学校里的老修女们,想象力太活跃,以为是“战争孤儿”,大大地惊恐了一场。这个情节应该是复制现实。三毛那个就难说了,她的枕头是装了钞票,抱在手上,去沙漠,千里迢迢投亲,哦,不对,应该说是投奔爱情用的。哈哈,后来她写《滚滚红尘》,里面那个沈韶华,也是从枕头里,摸了金戒指出来,给来人做小费。这个小说,据说取材于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它更像三毛本人的超现实风格。亦舒么,人家是物质女郎,做她笔下的女人,真是三生有幸,穿戴行头一一细描。她们用的都是什么英国牌子(确实记不清了)的卧具。白色细纹布枕头,光面,无花边,无绣饰。哈哈,质地精良,无款式,不是内行都看不出好处的通常才是最贵的。这种奢侈物的把玩,也只有师太的文里才有。但是,真正把物质细节手到擒来的,都是大家出身的,比如内米洛夫斯基那样,本身就是大资产阶级家里的独养小姐,看她写妈妈从箱笼里拿出祖传的枕套什么,不屑一顾的,几笔闲文,水波不兴地就带过去了。
扇子
《东周列国志》里,看到过这样的插图:两个梳双髻的宫女,手执长柄大扇,立在对坐畅谈国事的公侯身后,这样的扇子多半是由奴仆执掌,象征性大于使用目的,它是表白强权的道具。准确地说,它是礼仪扇。汉代的扇子,则是用竹篾编成,其形制类似于现在的大号菜刀,扇柄附于一侧而不是居中,且开始落入平常百姓家。在古画中,常见一奴仆蹲踞扇火,大力使着一把扇子,扇子地位大跌。汉末有一些原理简单的机械扇,诸葛亮同学发明过诸葛扇,悬挂屋内,手拉使之转动生风,穿过千年时光隧道,哈哈,在关于老上海的电影里,仍然可以看见理发店里有这种手拉的风扇。小伙计拉着一根绳,扇子左右缓移,那时间的纤维,也被拉长了,太太小姐们一边做头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拉呱家常。春日迟迟,欲睡昏昏。反正闲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