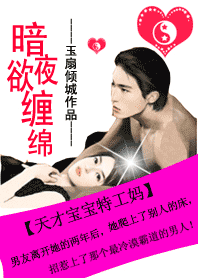超能特工-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我就想,正射手虽然是执行正义,但毕竟他没杀过人。或许,他看过电影上的杀人,一枪过去,人便不动了。却不知道,鸡尝能临死挣脚,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弄不好,他一生都会为此作恶梦。
但那是近距离。
我想。
我将要做的,是远距离射击。一百米上下距离的射击,和在部队一百米射击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这样安慰自己。
却听到了灵魂在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十五章 痛下杀手(三)
我这样安慰自己。
却听到了灵魂在哭……呜呜地哭。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得很凄凉。边哭,眼睛还偷偷挤出一条线瞧瞧我,看我有什么反应。
我没有反应。我心硬起来的时候,我是可以做到毫无表情的。就像当初我拍照敬良的尸体,我是没有什么情感可言的。那是工作。一个人被枪毙之后,还得验明正身。就是说,除了上面来督杀的人,需要对敬良的尸体进行现场检查,看看到底是不是敬良本人,看看到底是不是死了之外,就轮到我和法医上场了。法医会翻翻敬良的眼皮,看瞳孔扩散了没有,扩散了多少等等,然后记录在案。再检查枪口。射入口很小,比烟头还小,只渗出几滴血,但周围的皮肤有些焦了,还有些火药味。毕竟是近距离射击。法医检查过之后,认定是步枪射出的子弹形成的枪口,记录在案了,就轮到我了。其实,之前我就开始工作的了。当刺刀顶住敬良的脊梁骨,还没有开枪的时候,我就得拍下全景。刺刀顶着的整个敬良,射手是不能拍进去的,这是规矩。开枪将敬良射倒了,我又得拍个他倒在地上的全景。原始的,翻过身来的,得从好几个角度拍。拍完了,督杀的人检查,法医检查。法医检查枪口之前,要解去敬良身上五花大捆的绳,剪掉衣服,令其赤裸上身……
法医检查完射入口,我就将比例尺(纸做的)贴在枪口旁边,然后进行拍照。
法医将敬良翻转身,(我说过,我从来不碰尸体。当然,我老爸死了的时候是例外,我不但碰了,还为他擦洗了一遍身子,让他干干净净地上天堂,在月亮上面等我妈。)敬良的双眼突然又睁开了。不得好死的人,眼睛不会好看。眼瞪瞪着一股怨怨的死气,挺吓人的。法医连忙用手去合他的眼皮。合一次,睁开。再合一次,仍然睁开。法医就唠叨了,“合上嘛,你这是自己找死的,又没人冤枉你。合上、合上、快合上。别影响我工作。”
好像听得明似的,法医再用手合一次,敬良的双眼才合上了。嘿,怪。
射出口也很小,也只渗出几滴血。血在敬良白晰的皮肤上,显得十分显眼。从两只枪口都没大出血的情形看,正射手其实是射得很准的,子弹从背脊钻入去,穿过心脏,从胸口这边出来。心脏一穿,不难想象,那就像大坝决堤,血液喷射而出。我想心脏肯定也会被逼爆,所有的血齐齐涌在腔腹内。这也就是枪口只渗出几滴血的缘故。
子弹穿过心脏的时候,灵魂是否升天了?我想没这么快。
心脏爆裂的时候,大脑的神经是否即刻死亡了?显然不会。
以灵魂的速度,大脑神经的敏感,只要有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足以感觉到死亡前的痛苦、恐惧、绝望、身陷地狱那种难以言说的煎熬……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现在许多地级市枪毙人犯的时候,都不再用枪射杀,而是改用打毒针。先将被枪毙的人犯麻醉,等其进入麻醉状态之后,再打入毒针。想这种方法,也许会让人犯好死一些。
“那都是死。”灵魂撒泼道。
我装聋作哑,不理。
它哗声大哭,倒在我胸口上打滚,手脚并用,拼命击打,打得我的胸膛“嗵嗵”的响。
我生气了,将它翻转身,抽了两下它的小屁股。
不得了了,它哭得更凶。连波姬丝的灵魂也跑了出来,站在一边,陪着它呜呜地哭。
这不反天啦?
我真生气了,冲它吼道,“哭、哭、哭,哭我死啊?再哭我不要你了。”
呆了,我的灵魂呆了,它的眼睛对我射出陌生的目光,针刺一样,刺得我的心痛得滴血。
我无言。但心感惭愧。
它背转身,抱着波姬丝的灵魂,放声痛哭。
这样下去,真没完没了了。但用硬的方法显然不成了。过了片刻,我轻轻抚摸着它的背脊,柔声道,“我知道你难过,但你不要哭了,好吗?你知道,我们不是老子的时候,可以骑一匹青牛跑到关外去,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去。也不是陶渊明的时代,受不了,就可以跑,可以避,可以找一个桃花源,与世隔绝。每天花,每天蝶,过的都是如诗的日子。连火星都准备打仗了,你叫我怎么办?”
“那你说实话,你写诗是真心的?”它哭泣着问。
“绝对是真心的。”我坚定地答。
“那你杀人呢,也是真心的?”
“不,怎么可能是真心的?那不过是职责所在。”我道。它好像断定我会杀人的了。
望着我,以春天的美丽春天的柔情,它望着我,“我求你不要去杀人。以后遇到对手,我跑快一点。即使被打,我也不过是痛一下,为你,我受得了。真的,我受得了。”
我心一酸,真想抱着它哭。为它这么爱我。
可我不能。
因为我已经听到华莱尔和泰森回来的脚步声……感到了枪枝生冷的寒意。 。。
第五十六章 痛下杀手(四)
因为我已经听到华莱尔和泰森回来的脚步声……感到了枪枝生冷的寒意。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我想拉开波姬丝搂着我的手,让她多睡一会,可手刚碰到她,她就更是紧紧地搂着我,嘴里朦朦胧胧地说着,“亲爱的,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不走不行了。我想。对方的杀手正向我们赶来。
只好对着她的耳根轻声道,“亲爱的,我没走,我要上卫生间。”
“嗯,真的?”
“真的。”
她松开了手。
呵呵,美丽的谎言,有时还挺顶用的。
连忙跳下床,穿上衣服。开门,泰森已站在门口,悄声对我道,“头在房里等你。”
走入花莱尔的房间,珍娜已经在里面,可见她的动作比我更快。望着华莱尔,我关切地问,“你们没事吧?”
“没事。一切顺利。”华莱尔显得很轻松地道,然后望着我,“下一步怎么做?”
我感受到了他的疲惫,便道,“你和泰森先休息。到五点钟叫你们。”
“行。”华莱尔答。
我和珍娜走出房间,敲开罗伯纳的门。罗伯纳仍睡眼腥松,嘟哝道,“是不是又出发了?”
我和珍娜相视一笑。珍娜戏谑道,“是啊,要赶到月亮上去。”
“真的?是不是我们的航天飞机被劫持了?”罗伯纳就像被一盆冷水淋了头,马上醒了。
第一次见珍娜戏谑人。无疑,她冷冷的表情下面,还深藏着些天真和调皮。冷美人不冷。冰山下面也许就藏着火山。
拍拍罗伯纳的肩膀,我对他笑道,“暂时还没有。你先去洗个脸。”
罗伯纳朝珍娜扮了个鬼脸,然后入了卫生间。
凌晨四点。四周静悄悄的。
“李先生没睡好?”珍娜望着我,突然问。
“睡了,睡了一会。”我不敢说睡好。因为我根本就没睡,灵魂此刻还跟在我屁股后面擦眼泪。这家伙,仿佛在监视着我,只要一有点不对劲,它肯定就要跟我闹别扭。
罗伯纳出来了。不用我说,他马上打开电脑,望着我问,“查什么?”
“机场附近的建筑物。”我道。
很快,机场显示出来了。附近的建筑物也显示出来了。
“看有没有一幢靠近机场正门出口、又没人住的楼房。”我对罗伯纳说。珍娜的目光闪了一下。她一听就明白,我在寻找最佳的射击位置。所谓最佳,也就是不惊动别人,又能达到射中目标的地方。
“有一幢旧楼房,与机场出口斜对面,座东朝西,相距出口一百五十米。”罗伯纳干脆利落地将我所要的资料报了出来。
“行,就它。”我道。
五点十分,我们离开了旅馆,朝机场开去。
没有人问我所要射杀的目标是谁,怎么知道杀手会来。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好像已经是料事如神的了。
其实,并非我料事如神,而是,一连串的事情,使我深感对手非常厉害。我的灵魂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就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他也像我一样,只是个梦想家,而不是一个行动者。实则不然。他早将我们的古训“欲肩天下之大任,先劳其筋骨”付之实践,练就一付好身手,且出手狠。再就是湖边神秘的白影。我的灵魂说他是他的探子。我原来推测会不会是汉德姆斯,因为我们追他追得紧。但细一想,第一、第二回合,不但让我们避过,而且令他损失不少,已经知道,我也不是一个笨蛋。汉德姆斯绝不会是我的对手。既不是我的对手,他自然就不会再用他。那么,神秘的白影,就是另有其人。
这人是谁?
当我追他的时候,他闪避得很快,显然很熟悉苏必利尔湖这个地方。两种可能,一是他为当地出生的人,二是当地周围的人。
探子离我们很近。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
原打算在桑德镇多住几天的,我的灵魂便去设了迷魂阵,令我的对手一时半载找不到。可没想到汉德姆斯暴露得这么快,一下子就被我揪住了,便来个将计就计,叫罗伯纳向总部发信息,又闯入国防部的资料中心,自我暴露。
当我们撤离小镇,不用说,我们的行踪已经传到了我对手那里。对他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渥太华有他的人,但这些都是浮在表面的人,早在各国的特工监视之下,是不能动的。唯独的一个办法,就是派人前来渥太华。
我推测,从他知道我们撤离桑德镇,到确定我们确实是前往渥太华,他大概需要七八个小时。当然,这都是我的灵魂去骚扰他的结果。确定之后,再发出指令,派杀手前来,又得要一段时间。我估算了一下,杀手乘搭的飞机,在早上六点半到达渥太华机场。
车上没人吭声。
他们都在等着我发话。我便对罗伯纳道,“查一查昨晚九点从X国飞来渥太华的航机上,是不是有三个法裔墨西哥人。”
罗伯纳最开心的是要他摆弄电脑。我的话音刚落,他的键盘就“嗒嗒嗒”地响起来了。不一会便报告——
“没错。机上就三个法裔墨西哥人。一个是哥斯特,身高一米九二,是个胖子,曾是特种部队的队员;一个是莫尼克,身高一米八三,身材健壮,前身是特警;一个是尼高,身高一米八五,是个拳击手。”
跟我灵魂回报的资料一样。我想。才知道我的灵魂哭归哭,该干的事仍然是干得头头是道。
我扭回头,对华莱尔道,“到了目的地,你和波姬丝、罗伯纳留在车上。我和泰森、珍娜实施狙击。”
“不,你留车上,我去。”华莱尔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