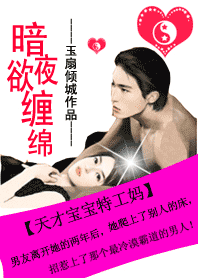超能特工-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已露出鱼肚白。
未近灌木林,我已看到蝶影翩翩。心已稍安。
近了灌木林,几只蝴蝶绕着我起舞。一只落在我的肩上,又一只落在我的肩上。
哦,真是蝴蝶的家园。
白光一闪,灵魂站在我的头上,不满了,“主人,你分明是不相信我。”
“没有,我哪会不相信你?”
“相信我的话,你会这么早起来,不陪陪波姬丝?”灵魂不放过我了。我只能辩解,“就是为了想一生好好陪她,我才出来看一看。毕竟,我是肉体,是现实主义嘛,眼睛不看到真实的蝴蝶,怎么能踏实,你说是不是?”
“嗯,看你那么爱波姬丝,这回原谅你。”说罢,灵魂飘回别墅,飘到波姬丝的眼睫毛上,向波姬丝贩卖它的蝴蝶梦了。
我和珍娜往回走。珍娜身上的肤息很淡很淡。显然,在特工职业训练的时候,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如何使自己变得理智,肯定是重要和一课。特工是项危险的职业,容不得有半点情感的渗入,该果断就绝对要果断,绝对不能手软。像那位直升飞机的机师,就因为犹豫了一秒钟,也许是想到对方该不该杀吧,自己反倒被杀了。
“李先生,你每天都爱早起的吗?”珍娜突然问道。
“是的。”
“因为写诗还是习惯?”珍娜似乎对我的生活有点兴趣。在她眼里,我或许是个怪人。我望着天边升起的半轮太阳,说道,“两样都不是,而是观念。我是这样想的,要睡觉的话,死了之后大把时间去睡。”
珍娜瞪大眼睛,显然感到不可思议。
我笑笑,又道,“人生百年,本来就像弹指一挥间,再不珍惜的话,岂不浪费?事实上,我每天睡五个小时,还有三个小时是和灵魂一起去周游的。真正睡着的,恐怕就两个小时。”
“灵魂真听你的话。”珍娜欣羡地道。
“不。它有时也调皮,也爱自由活动,不听我的。”我实话实说。珍娜“哦”了一声,再不说话。或许她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真能控制。
太阳鲜艳,湖面铺满红光。多美的景象啊。
便沿着湖边,我和珍娜走了好一段路,才回到别墅。
华莱尔他们都起来了。
见到我,波姬丝眼里却噙着泪,一把抱着我,怪道,“亲爱的,你一大早跑哪去了?醒来不见你,真急死我了。”
“亲爱的,我心里不踏实,所以才一早出去查看了一番。没事了。”我亲了一下她的脸蛋。
吃过早餐,我对华莱尔道,“今天就弄那个乳房迷案吧。”
“好!我叫罗伯纳准备。”华莱尔显然感受到了我的好心情。
罗伯纳毕竟是专家,很快,他就拉上客厅的窗帘,在客厅的墙壁上挂好了银幕。打开电脑,接上微型投影机,将乳房迷案的资料投射到银幕上。
“用人才外面守吗?”华莱尔轻声问我。
“不用。那样显得更显眼。”我道,华莱尔点了点头。
银幕上打出的先是乳房迷案的简介——
2047年2月23日凌晨五点,巡警在纽约东区伍德黑义街,发现一具裸身女尸,双乳被割,腹部被剖开,年龄在二十至二十五之间……
二十多宗乳房被割案的简介都差不多。只是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而已。根本看不出什么眉目。
“放照片吧。”我对罗伯纳道。
“是,李先生。”罗伯纳答。
仍从第2月23日这第一宗案放起。
罗伯纳很有经验,他先放整个现场的环境。
大方位:伍德黑义街。
具体地点:伍德黑义街海兰公园门口左侧。
“伍德黑义街主要住的是什么人?”我问。
“白人。”罗伯纳答。他也是个活资料库。
“海兰公园是情侣爱到的地方么?”我又问。
“是的。”罗伯纳答。接着放了几张女尸现场照,几张创口的特写。那都是惨不忍睹的。不详述了。
“放一张女孩脸部的特写。”我道。
罗伯纳放出女孩的脸部特写。
我细细地瞧了一会,大脑转了一下,即道,“这被杀的女孩不是海兰公园里的情侣。”
“你怎么知道?”波姬丝禁不住问。我望了她一眼,“很简单,她的脸上根本就没有一丝恋爱的神色。”
“恐惧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有留下恋爱的神色?”波姬丝显然不支持我的观点。因为她不知道,我就是透过恐惧的表面,深入去看,才看出这点来的。雁过留声。一个恋爱的人,不管她碰到什么恐惧的事情,仍然会在身上留下迹象的。当然啦,这已不是肉眼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我说是看,其实是灵魂带着我去嗅去品去搜索。这好比一个人身上带着毒品,然后再在身上洒些异味。一般的警犬会被异味骗过,而出色的警犬,则可透过表象,搜索出毒品来。只要存在过的,就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何况,一个人身上发出来的恋爱味道和恐惧味道,是截然不同的味道。反差极大,所显示出来的神色也就不那么容易被掩盖。
我简单地向他们解说了一下,他们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二十九章 纽约迷案(二)
不知为什么,当我望着银幕上的照片,我的灵魂居然显得很兴奋。一时跳入我的眼睛,一时跳到银幕上,放大镜一样瞧着尸体的每一个部位。老实说,要不是因为美方的盛情,半请半骗地让我加入反恐行列,看这些死人照片已经成了我的职责,不得不看的话,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想看。照平常人的想象,以为看女尸是会很过瘾的,什么都可以看到,而且是近距离地看。那真是不懂什么叫死人了。再美的女子,只要是死了,变成了尸体,就跟死狗死猪没什么两样。
当年就有人问过我。“你拍女尸的时候,有没有点那个?”
那个,当然就是指有没有性趣了。
我觉得这是废话,便反问道,“你望着猪肉台上的一块块猪肉,有没有性趣?”对方被我问得面红耳赤。
而且,因为是同类,望着心里就更难受。那种难受,不是一般的难受,是一
种难以言说的难受。每回,法医要翻动尸体,我绝对不动手,让别人去帮手。不是因为我要拍照,即使我不拍照,我也不会帮。乃是我曾搬过一次,死尸那种沉重,不但像大石那种沉,而且是沉到心里发寒的那种沉。所以,有时为了形容某件物品的沉重,有人就会说“那东西死沉”。因此,搬过一次,我便发誓不搬。
人死,灵魂就飞走了。至于灵魂是不是投胎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或者是转世为猪狗,这已不是我所要说的。我也不想说。因为那实在太唯心了。我只想说,没了灵魂的死尸,肤色是寡青、寡白,寡得令人心里发毛的。那种无形的死气,兼上尸体的死寂,就像将你罩入一种无比压抑的氛围。
如果你问我什么最难看,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死人。
我的灵魂为啥会兴奋?
不用说,这坏家伙是想趁此机会卖弄自己的才学。
它看得很细致。连阴部都翻开来看看,闻闻。
真是恶心。
“主人,你别忘了,这是工作。别将我想得那么下作。”灵魂批评我道,然后又说,“我为什么要翻开阴部来看?法医一般只凭阴道有没有遗留精子,有没有损伤来判断其有没有做过爱,这都是很表面的。戴套,就不会留下精子,是不是?将女方刺激得很亢奋,如果不是故意用手去抓去爪的话,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是不是?”
它言之有理,我只能点头称是。
“我要去看,要去闻,其实就是要更深一层去检查,这女的死前有没有做过爱。这对你们破案很作用,是不是?”
“当然。”我心道。
“阴阳相交相合,不管情愿不情愿,都会本能地发出味道来的。浓淡不同,也就说明双方的感情深浅不同。而且,即使同是浓浓的味道,也浓中有异。比如是因为恐怖、狂乱、受到外在刺激而发出来的味道,就会浓得不那么纯。懂了吧?”
灵魂在教训我。
“懂了。”我心答,却想,好像它是外宇宙来的,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一样。
灵魂去细看尸体,我却没看得那么细。我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发案现场的图片上。
发案的地点,不,只能说是发现尸体的地方。据我粗略分析,尸体倒卧的地方,并不是第一现场。若莫综合了一下,抛尸点都集中在公园、商场、十字路口等人多、热闹、显眼的场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倾左的方向。如门口的左边,十字路口的左边。凶手似乎对左很有兴趣。
那么,凶手是习惯用左手的?我还不能断定。这只能是一个推理的方向。真正要认定,仍须看凶手割乳房的刀法,破肚的刀法。
但只看了乳房迷案的现场图片,及简单的尸体图片,就已经到了中午。
这时我才发现,别墅外面很热闹,显然有不少的游客。
“李先生,中午是吃唐餐,还是吃什么?”华莱尔征求我的意见。我扫了一眼大家显得有点憔悴的神色,便道,“去吃顿湖鲜吧。”
苏必利尔湖还没受到什么污染,湖里的鱼自然是挺鲜美的。
出门之前,大家都换上休闲装,实足游客一样。当然,我和华莱尔戴上眼镜之后,就像了教授。波姬丝、珍娜、泰森形同我们带的博士。罗伯纳则像是我们的助教。
我知道,对这样的身份安排,罗伯纳心里是不舒服的。他老想着自己是电脑专家。但有的东西是没办法的,他跟我和华莱尔站在一起,就显出了层次的不同,他就是助教的料。
“罗伯纳,委屈你了。但这是工作需要,跟你真正的才学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我安慰他道。罗伯纳连声称是,还自嘲道,“谁叫我的长相显得那么不成熟呢?”
我们都笑了。
本想可以大吃一顿湖鲜的。谁知到了一家叫利尔的餐馆,坐定之后,欲大点这鱼那鱼的时候,侍应生礼貌地告知我们,“为了环保,为了保证苏必利尔湖鱼儿们的的正常生长,不至于做成滥捕滥杀,每人只能点半斤的鱼来吃。”
捏指一算,我们六人,只能吃三斤鱼。
想想我爱鱼的肚子,恐怕三斤还不够满足它的要求。
鱼不够,肉也可了。牛排、猪排,吃。
“那凶手也爱吃鱼。”灵魂对我道。
“你怎么知道?”我兴奋地问,以为立马就有了追寻的线索。
却无回声。只见我的灵魂苦着脸,很不开心的样子。
“干嘛了你?”我关切地问。
“我突然闻到禾花雀的香味。”它道。
“嘘,想都别家。人家这里的人从不吃鸟。”
“还有狗肉香。”它这明明是要我的命。我爱养狗,偏又爱吃狗肉。一到冬天,每星期肯定会打一次狗肉煲。这家伙,真是坏透了。明知当年全世界就有五百万人联名签字,反对亚洲人打狗吃狗的。叫我在爱狗的国家叫吃狗,不将自己当成狗被人打了?
可我不能硬来,我只能耐心地跟它说,“这里的湖鲜挺不错的,肯定又鲜又嫩的。”
“那等会你多吃点。”它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