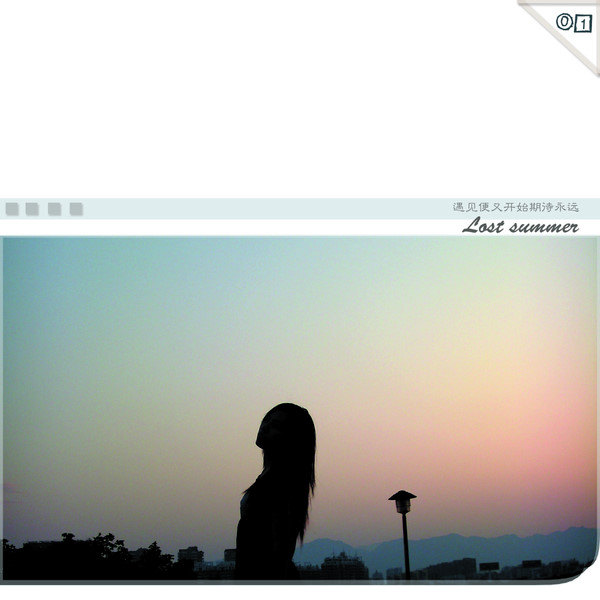黄昏以后,黎明以前-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活下去,不需要别人对他赞美。想回到小时候放松的日子。他睁开沉重的眼皮,僧侣在他身这闭眼沉思。从那张凝神的脸上,看到了冰霜了的眉目,还有努力抗拒颤抖的牙齿。雪地阳光,正从万千穿阻的雪中中飞舞,利剑般斩入眼睛,他像从一个坑里爬出来筋疲力尽,也不畏惧。
在沼泽,你见到了所有可能的腐烂,在飞虫的叮咛声中找到所有的路,与腐水腐根缠在一起成为一体。一丝不苟地耐心把他们驱赶开自己,像蚁群一样支出团团包围。噬咬着无法动弹,起码到它空了,呼气挣扎成了最后的祷告。他的心里也有万千的蚁群。扑向硕大的的虫子,咬住它,没有放松,不管甘甜与求饶怒吼,弱小的你还是不能放过示弱的它们,坚持远远不够。你看看强大的怪物奄奄一息,在以前某一刻,它盘踞在你的内心处,令你的智慧与情感都听令于这纵然可以把它踢走,到了死亡的尽头,除非你没有意志。就像一片柳叶甘愿随风走,随雨落,随蜂虫戏耍,你的热情都被它当作是廉价的崇拜而挥霍个没完,它成了你的主人,而你从来没想过辛苦的自己却成了奴隶,听话的奴隶。与繁杂的气味相吸,与无数的蚊虫相识,你任由它们在身上流淌,但你没有下沉。像一只落水的兽又回到了天堂的领空。抖去了所有的弱水与凝滞泥块。你是只在风雨中搏斗的鹰,争取的是把自己从破碎组成完整,拼成自己的世界地图。天地万物,宽容大度,任由生物生长而肥沃自己。阳光生育万物流转于万千生命之内,无数的丛林在水边繁衍,水善万物而不争,不管它被如何地捣碎,被如休地肮脏,仍然是它自己在颤动着,生活该如休走,仍然该怎么走不要吝啬,只要付出别管后果对你是对是坏,未来才知,别管别人能给你什么,别满足到自己的*,陷自己于虚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某一则新闻
阿容的想法里可能永远不会出现阿标的负面形象,正应了情人眼里出西施。她的心底世界中剔除了外界的种种,如家庭规则,法律,只留下舞台中两个人,或者说只有一个阿标时,他的一切像暗室里的一粒烛光,慢布了全部,即使微弱即使与她丝毫无关,她能将之串联成一段与她有关的台词表演。意识里的拥抱能让她在无聊中突然激动起来,她喃喃道,唉,标哥一定不希望她这样子,她该怎么办才好呢,她开始陷入不安,望向天空或者窗外,一直看着仿佛自己就能飞去了那里自由了。她肯定他票意要求这么的,于是她暗暗下了决定,慢慢放松呼吸,笑意已在嘴角边了,她的丈夫常常看到她时缓时促的表情,的确的赐开始时,他觉得她神秘的表情一定藏了梦幻的心思,她逃避似地缓过神来,回到现实里,继续看着她的丈夫儿子房子。久而久之,他习惯了她宋发呆,频繁,也习惯了发呆之后之中的不可捉摸和正常化。在多年之后的离婚时,她焦急稚气的笑却让他开始懂了:这种女人还是别懂了为好。带着孩子从那一元所知的生活里走开了。
邻里人都习惯了粗糙的生活了,买菜煮饭,大大咧咧地骂,阿容从小都只是和邻居一起的,当着别人的配角,走在别人的身后,她极力隐瞒自己的主张,想法和不满。其实她不必这么做的,就是并排站着,别人也看不出变化,不会留心一个十岁女孩心里那种关于自尊自插萌芽在那样的情境下。况且她沉默着更在乎他们的评说了。有一次在夜里她与表姐行路,她隐隐看到路旁的红色烟火,显然是痞子在聚谈。她蹑着脚越走越轻,快路过时,什么都与无人一样。她心里陡增失落感,让她想得恨了。鞋擦着地面,有了响声。他们听到了,口哨,一声两声,她得意了,头也没偏继续,越走越轻。这是她想要的,又是不想要的,
阿容的父母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与众不同,不理解她一直没追求没情绪没感受,并不与一般小孩儿合群。正像在田地里忙活,她也是做完了自己部份,让别人管理接下来的事,小一点的时候如此,大到十四五岁仍然如此。她觉得别人不懂她,阿容疯狂地贪恋着橱窗里的商品上架下架。喜欢是罪恶,罪恶在于满足感得不到偿补。令她每每产生时都会增添一点负气。她每天买菜时经过的街已经看透看旧,她与她妈提菜篮子过去,从这菜到那菜摊,拣拣拣,她母亲一直教导,人要安于现状,有什么就做什么,努力尽力。但她只是一边听一边出,和妈作恩爱母女。
她只念到初中,*中*得很,但家中却平安,参与*。一窝峰跟到那混到那,觉得没意思。
阿容没追求过什么,没有什么爱憎,需要特别选择干什么呢?那么多人没有找到自己的有宄,她凭什么会过得更好,阿容想过了,不挑剔就容易快乐。二十时候结婚,介绍的对象是个技工,感觉生活和别人一样了,阿容以几年后发现这样的生活枯燥,她还没懂得收获到了,慢慢像饥渴一样折磨心肠,令她的目光也变得凶狠,有摄取的样子。她感觉别人看出她时,她却像被烫着一样,让这些目光里的东西收回在心里,怎么可以这样呢,已经结婚了,阿容随太夫出外打工,阿容若有所思地安定,在原状里继续工作。
一介女人在婚姻里会磨灭会积淀,对于她这样匆忙完成结婚任务的人,却有时突然开窍。一些灵光在脑子里闪动,萌发些念头。在适合的条件下长叶,幽然地就散发了整个空间,有风有水有盐分,阿容感到世界的目光都不重要了。她想要的是别人想不到的。她二十多岁身材仍然是美好的。时常感到完全展现是一种太虚荣的表现。于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她是忠心不二的,甚至于丈夫也有所保留。她有什么爱好呢,就是往低标准看齐,怜悯且同情,恨不能替代痛苦,把自己痛苦代价而得的欢乐却用受难的心态去接受去排斥去抗拒。她唯唯诺诺过度视劳动为欢乐的心情,让她的丈夫的母亲很欣慰,却让丈夫觉得糟透了。吃过期的饭,买仿冒衣,去批发市场淘货,特价商品,这些让她心满意足,很无聊。
阿容四十二岁了今年,离婚,孩子很长大了。她仍然记得阿标对她说,你怎么这么早就结婚,那句话有她18岁着念的归属地,阿标37岁才结婚,她听到时毅然离婚,想必他也等了太久了吧。
她在横岗在龙岗,在坪山,她陷入情绪里宛然对表兄说,我真傻,真的,真不该。表兄时常听到前半句,想问她后半句,她已经回神过来,我刚才没讲什么吧。该过去的事都去了。她想起了什么,在龙岗她23岁时,正对生活不变的格调感到抑郁,她决会这样这么一种生活了,阿标是那个思想的产物,他好群还读了高中,文化气质都与众不同。阿标很觉得事业是男人的根本,在人群谈论自己将来什么。她听到了很惊讶,有见地有主张的一个人,而自己却没想到自己会遇到与想象中一样的人。这引起了她频频的伤心,她为什么结婚还找了这样的丈夫,她本来有选择的,只是自我意识没有苏醒,她上商场去,挑衣服,店员颇意外地接触不时敷衍地赞美几句,她想,不就是花钱么,值得。谁都会。阿容绽放的时候的确让周围的人兴奋了一阵。也成为男人的饭后谈资。阿容小资地偷闲时,碰到了阿标。她说,你是那谁媳妇吧,怎么那早就结婚了啊。她沉默,他觉得自己问得唐突便告辞了。她想,我不该啊,如果早遇到他就好了,你难道在怨我没等你就嫁了吗,还是在问我是否有意跟你呢。阿容调怅了一阵,回到丈夫身边去。她正打牌,阿标也刚去,已经凑成一桌了。见阿容回来,丈夫瞄见,阿标笑说,来看牌啊。她心里一酸,我都后悔了,你问我想好没有是不是。可惜我不能啊。她就到丈夫背后看牌了。丈夫说,你煮饭去吧,今天晚上招待。好好玩个通宵。被视为煮饭婆的她生怨气,走开了。阿标在后面说,记得打酒啊。她想,阿标在羞辱我吗。想想我的苦吧。她心灰了。
阿容总觉得被阿标看着。她感到身后有目光在考量着,转过身时,目光又收走了。身后还是那群打牌的,阿标却笑着摊牌说赢了。阿容心想原来是你,别逼我,别逼我,让我考虑想想。阿标若无其事,看到阿容,有些心不在焉,所以多看了几眼,那背影是少妇们丰满的身形。阿标问阿容男人,容姐是不是不爽哦,看那样,择菜都没安心呢。丈夫答道,习惯了决那样,轮你出牌了,快点。
她听到了半句,觉得心凉。对得起我吗,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怎么认为我贱人似的,不当理会是回事。她骂在心里。她去买酒了。冰在心里。吃饭喝酒是男人的事,女人就躺在床上不安了一夜。心里恨得睡不着。突然直起身,靠抱着胸,斜眼看着那间亮灯的屋子,叹气,好不甘心啊。
接到群众报料去现场,拍了照片,又陪同去了医院。幸好只是轻伤。包扎休养一阵也就痊愈了。她此时很安静,眼神定定地看着被褥,哭腔已浆化成了嗫嚅,医生在一旁抚慰了几句后离开了。我问医生究竟她感受的是真是假。她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更年期的女人与年轻时相对变化了很多,浮肿,臃肿,皱纹像毒蛇一样缠着她的眉头。我并不知道要问些什么,从报料人口中说,关于她等阿标十八年的暗恋变得很难相信,又不容置疑。她却说什么,眯着眼睛猛地会睁开,然后竖起身子,双手托着自己的双颊。那红润的脸像少年的羞。她叹了口气说,都是她的错。
我说不容易啊。她搔着头发越来越乱,为什么他不肯见我,他不肯原谅我对不对。你说你犯什么错了,要求他原谅,要和他见面。你说了,他转告她说,说不定会来的。她的脸舒展开,怎么说呢,好多年前了。
饭局后,她看着阿标揽着年轻女孩打闹,她经过了,没打招呼,空气里有些怪异。她经过了,却又回头看,这里阿标打招呼了,与年轻女子松了距离。她没答,仿佛气极了,没有任何迟疑便回去了。她心里是矛盾的,既然自己结婚了又怎么能出墙,自己又在年轻时看着母亲主宰自己的命运,又怪得了谁。
平淡的日子在阿容宽容的心态里有了阳光,因为阿标谈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听丈夫谈起仿佛羡慕的样子,阿容说阿标怎么不好好谈个对象。丈夫说,不愁啊。年轻还是先自由自在些年吧。说不定最好的还在后头呢。她愣,自己这么早结婚,也是为了来这里与他见面的,过多少年后自己也许离婚了,就有可能了吧。自己还有孩子在家里呢。自己要当好母亲,怎么能开玩笑呢。
她说,我那里结婚了。因此有苦说不出,也不能拦着他,帮助他。她的嘴唇干裂皱了,她恨地咬住了唇。别人知道吗。我老乡表弟都知道,不小心让人问出来的。我结婚时这些话怎么能说呢,要做有妇道的人,现在离婚了,孩子大了,我也要有自己的幸福了。最后悔的是十年前我受伤了离开了工队,也是因为听了他要我回家的话,所以赌气走了。前两年离婚,就回来找他。这话没敢说。可在坪山打工时竟然碰到他了,没结婚,还是那么一副好看潇洒。我不是因为这个爱他的,那庸俗,我懂他,他辛苦又勤奋,是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