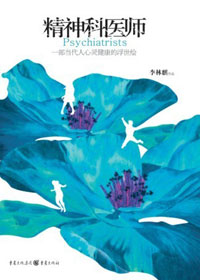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装在花瓮里埋在地下五年,才取出来冲茶喝。妙玉的”‘茶道’简直使我们望尘莫及了。“
王一民一听也笑着说:“那是只有妙玉那样脱离红尘的散淡闲人才能办到。我读到那里真有点替她担心,我怕那埋了五年的梅花雪水再变成陈年佳酿,岂不坏了茶的味道。”
王一民说得两个人都笑了。这时下女又用托盘端上来三个盘子:一盘水果,一盘糖果,一盘点心。
玉旨一郎一边让王一民吃一边说:“日本和中国有许多相同的东西,又有许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有趣的是不同当中又有相同。”他一指三个盘子说,“例如敬客摆盘子,中国必须是双数,一般是摆四盘。而日本却最忌讳这‘四’字,所以只摆三盘。因为‘四’和‘死’都是发西的音。人们怕死,也就怕‘四’。死和四,中国发音很相近,日本就完全相同。而迷信,怕死,图吉利,这些就都和中国一样了。中国每逢吉庆日子,例如过年过节,不是都不许说死吗?”
王一民点点头:“平常也忌讳说死,骂人话上面常常加个死宇。”
“日本也这样。所以我说不同当中也有相同。譬如我们的语言是不同的,但是写到纸上的文宇却又相同了,‘真名’和‘假名’,一是完全从中国拿来的,一是拿了一半——单‘立人、宝字盖、草字头、三点水等等中国字的偏旁,就成了我们的字母。再譬如现代穿的衣服,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妇女。但是在中国戏台上演的历史剧中,却可以看到现代日本服装的原型,这又是不同中的相同。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和日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真是到处可见,俯拾皆是了。”
王一民注意地听着,品味着,思索着他谈这些话的真正意图。同样的内容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它可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也可以成为真正亲善的思想基础。那么玉旨一郎想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到这里,他就接着玉旨一郎的话音,试探着说道:“您讲得很精辟,很有见地。可是是不是有些抬高中国了?”
“不,不。”玉旨一郎紧摇着头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教育史也是历史的一个分类——我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日本有好多东西来源于中国,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样敬重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根本原因。”说到这里,他打开书橱,从里面捧出一个用黄缎子带系着的,一尺见方的木板夹子,轻轻地放到王一民面前,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解开缎带,打开木板,里面展现出一张很粗糙的黄纸——是由于年深日久而变黄的纸。纸上用木版印着一位盘腿打坐的中国老和尚的肖像,肖像的两只眼睛闭着,周围是白色的灵光。肖像下面写着“初祖传灯大法师”,肖像周围印着象征着祥云的“云卷”图案。在黄纸的最下边,有一行小字,上写:江户福康药店制。
王一民一边看着,玉旨一郎一边指着说:“这是我国江户幕府初年的一张包药纸,距离现在有三百多年了。‘江户’就是东京,‘初祖’是日本医药界对鉴真和尚的尊称,‘传灯大法师’是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法号。看了这张粗糙的包药纸,您就会知道日本朝野上下对他是如何敬重和爱戴了。这是历史的见证啊!”
王一民深深地点着头说:“好!您收藏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这是家父留给我的,在日本大概也找不到几张了。”玉旨一郎一边说着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把木板盖好,系上缎带,送进书橱。
王一民略微思忖了一下说:“这样珍贵的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一看,我建议您制成锌版,在画报或报纸上发表一下……”
还没等王一民说完,玉旨一郎就摇着头说:“不行,至少现在不行。”稍停了一下,他叹了口气说,“不是时候啊!”他又直盯着王一民看了看说,“连您不都说我在‘抬高中国’吗?您看现在有哪一个日本人能站出来说一句‘抬高中国’的话呢?把中国抬高了日本怎么办呢?还能在这里当‘太君’,当‘太上皇’,像我叔叔那样……”说到这里他把话咽回去了,低下头,看着脚上穿的木头拖板,沉默着……
王一民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
半天,玉旨一郎忽然抬起头来,他眼睛里闪着亮光,直看着王一民说:“王老师,我今天请您来,是要把心里话向您讲讲。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研究和分析,我认为您是一位正派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得更进一步的话,您可能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下了,直着眼睛看王一民,目光那样深沉,是观察?是审视?还是要看到王一民内心深处的什么?使人不解。
王一民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连眼睛都不眨,庄严地和玉旨一郎对视着。他脸上既没有惊讶的表情,更没有恐慌的流露,简直平静得像方才看过的鉴真和尚的坐像一样。
从墙上传来的嘀嗒嘀嗒的钟声判断,时间大概过去了有一分钟,玉旨一郎才点点头说:“您真镇静!我敬服的也正是您这种大无畏的镇静态度。我第一次发现您这惊人的镇静是在课堂上,您正在给学生讲反抗异族侵略的中国皇帝朱元璋,这时您发现我了,竟能那样不慌不忙地把问题一转,转得又轻松又自然,让人简直无懈可击。接着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您竟能在爱国真情已经完全流露的情况下,辩解得既不露痕迹又头头是道。我相信,如果那是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您一定会获得无罪释放的。”
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道:“后来我们的接触就多了一些,当您的学生罗世城被捕以后,您那镇静的态度被感情的波涛冲破了,您焦急了。接着,我特地请您和我一同去检查他的遗物,我知道您是如何急于要拿到他那些不宜公开、更不宜落人我手中的遗物。但是不幸得很,那本记着他和另外几个学生活动的重要记事本偏偏让我发现了。我看了,并且记住了那几个学生的名宇。后来我把本子交给您了,我在等待着,看您怎么办?开始我以为您会胆怯,会不敢拿走。因为只要我一伸手,您就会立即陷入罗网。这一切,您当然会看得清清楚楚,您会感到那罗网就张在您的面前,您会把手缩回去。可是,您没有顾到个人的危险,您不但拿走了本子,还把那封写有罗世诚家庭地址的信也拿走了。您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样干了。而更使我惊奇的是,干完这样的冒险事情以后,您不但不藏不躲,还照常上班,见了我的面也一如既往,好像您根本没有干过任何伯人的事情一样。您的镇静使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是不是我看错了,那本子和信您根本没有拿走?我又第二次去重新检查罗世诚的遗物,不但本子和信确实没了,竟连任何可疑的东西和线索都没有留下,您干得于净利落!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卫着别人——也可能还要加上保卫您的信仰。您的行动不但使我佩服,使我同情,也使我非常感动。紧接着,我们又都到罗世诚家去了——可惜的是我去晚了一步,没能在那特定的环境里遇上您。如果那时遇上,可能今天我要说的话在那时就说了。当然,罗家的人——主要是当时自称为小学教师、实际是名演员柳絮影小姐,隐瞒了您去过的真实情况,这我从她家的种种迹象和哭红了的眼睛上都可以断定。所有这一切,都向我说明:您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爱国者,您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玉旨一郎讲完,就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王一民,等待着他的回答。
王一民这回没有再沉默,他异常冷静地说道:“对您的推理和判断,我先不进行辩解和说明,我将保留这个权利。我想先大胆地问您一下:您讲这些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我要进一步了解您。”
“了解并不是目的。”
“我的目的很简单,”玉旨一郎一挥手说,“我早就当您讲过,我要有您这样一位诗书传家,深晓汉文,能够和我在事业上共同切磋琢磨的中国朋友。交朋友,就必须要有所了解。”
“可是这种了解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王一民也一挥手说,“如果您是以上司——副校长的身份来询问一个教员,那我将有问必答。如果为了达到您所说的目的,那就应该是双方面的。”
玉旨一郎点着头说:“您说的有道理。”
“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您。”
“我的心向您敞开着。”
“那您能允许我大胆地向您提问题吗?”
“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将有问必答。”
“好。”王一民点点头,郑重地说道,“我对您不了解的地方很多——不,不是不了解,是不理解。您用您的行动在我的脑子里打上了一长串问号,这一串问号汇集到一起,就成了一个谜。不必讳言,您曾间接地、直接地,给过我好多援助,这是正义的援助,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早就应该站到您的面前,在向您致谢的同时,主动伸出友谊的双手。但是严酷的现实不但限制我在行动上那样做,连感情上的流露都不可能,因为什么会这样呢?”
玉旨一郎垂下眼帘说:“因为我是侵略你们的日本人。”
“不,不单纯是为了这个。”王一民摇摇头说,“您是一个日本人,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您是哈尔滨——甚至整个北满的日本统治者玉旨雄一阁下的亲侄子,在您背后站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请允许我用一个不够恰当的比喻:犹如您在前边走,您的背后跟着一头老虎,您走到哪老虎跟到哪,这在中国叫什么呢?”
“您的意思是说‘为虎作怅’吧?”
“至少会让人往这方面想。一往这方面想,您的那些正义行动就必然被画上问号。”
“这么说,您的问号主要是集中在我和家叔的关系上?”
王一民点点头。
“好。那我就向您讲讲我的家庭情况吧。”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仰起头,眼睛望着西边墙上贴的大小两个乌龟,缓缓地说起来……
56
“我们家从我祖父开始,就是研究中国古汉文的汉学家。他老人家在这方面有一些专门著作,在日本是很有影响的。
“祖父生我父亲和叔叔兄弟二人。祖父希望他俩都能继承家学,研究古汉文。所以从他们开始读书起,就教他们学习比汉两种文字。父亲比叔叔大五岁,所以学习的时候自然就形成祖父教父亲,父亲又领着叔叔学的局面。
“父亲和叔叔这兄弟二人,不但岁数差得比较多,秉性相差就更加悬殊。父亲敦厚踏实,老成持重,读书非常用功,祖父夸他是读书种子,可以继承父业;叔叔眼尖嘴快,飞扬浮躁,读书不用心,全靠小聪明。祖父说他聪明外露,难成大器,调教不好,将要长成一棵歪材。因此对叔叔管教很严,经常考核他的功课,父亲也尽全力帮助他,所以他在日、汉两种文字上,还都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不幸的是在父亲二十六岁那一年,方满五十岁的祖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时候我已四岁了。可是刚刚二十一岁的叔叔还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汉文。祖父一去世,家里生计立时成了问题。过去是靠祖父著书卖文为生,父亲一直给老人家当助手,祖父去世,二十六岁的父亲立刻就失业了。生活的困窘逼迫叔叔中途辍学。弟兄二人为找职业而各处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