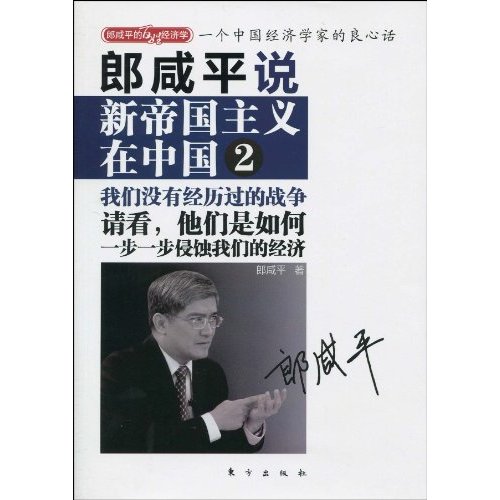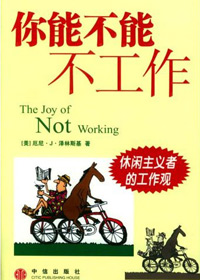专栏主义嗔-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都顶着小说的名目,却不宜拿寻常看欧美小说的眼光去看它。
我这看法,或许日本作家自己就不同意。因为日本现代文学兴起,正是受了俄罗斯和欧洲文学很大影响;而成功的作家,也往往声明自己从日本以外得到师承。不用提早期的红、露、逍、鸥了,岛崎藤村、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等,都是如此;就连川端康成,也说过“可以把表现主义称作我们之父,把达达主义称作我们之母”。但是外来影响最终不过是引发他们对本国文化传统的某一方面加以继承和发扬而已。灵魂永远是日本自己的。一千年前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随笔集《枕草子》,始终是奠定日本文学总的追求和方向的作品。而虽然前者算小说,后者算随笔,在我看来,它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相异之处。日本的小说读来有如随笔,而日本的随笔若与欧美的随笔比较,更像是胡乱写的,一般所谓章法脉络他们不大理会。总之,我们看作不得了的,日本人似乎很少顾及;我们轻易放过的,他们却细细加以体会。这里附带说一句,一般论家谈及日本文学,总喜欢贴上现成的标签,譬如说谁是浪漫主义,谁是现实主义,谁是自然主义,谁又是唯美主义,这多半因为日本作家自己也搞这一套,然而这些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借口或名义罢了,实质则根本不同。我们讲“主义”,都是以情节文本作为前提的;而日本文学是另外一种文本,这些标签之于他们,他们之于这些标签,总归不大对得上号。
一部小说的读法,可以有粗细之分。这里仍然不论高下,但是粗读读情节,细读读细节,大概是不错的。日本文学作品如若粗读,恐怕一无所获。因为它根本不重情节,也不重结构。日本现代最有名的几部长篇小说,如夏目的《明暗》,谷崎的《细雪》,严格说来都算不上长篇小说。读这样的书,不仅不能忽略,而且应该特别重视每一细部。日本小说的细节与别处内涵不同,分量不同,地位也不同。田山花袋的《棉被》,说得上是这方面极端的例子。整篇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结尾处一个细节的铺垫。主人公时雄送走为他所深深爱恋的女弟子芳子,回到她曾经寄宿的房间:
“对面叠着芳子平常用的棉被——葱绿色藤蔓花纹的褥子和棉花絮得很厚、与褥子花纹相同的盖被。时雄把它抽出来,女人身上那令人依恋的油脂味和汗味,不知怎的,竟使时雄心跳起来。尽管棉被的天鹅绒被口特别脏,他还是把脸贴在那上面,尽情地闻着那令人依恋的女人味。”
本来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却被发现具有特别意味。最普通的东西也就变成了最不普通的东西。人物之间全部情感关系,都被浓缩在这一细节之中。这里也体现了日本文学中情感交流的基本方式,即往往并不直接发生在人物之间,而要借助一个中介物,出乎某种情感,人物对它产生特殊理解,使之成为投注对象,而它本身也具有了情感意义。在日本小说中,人物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从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情感背景出发,连续不断地对现实生活中瞬间与细微之处加以感受体会。
然而《棉被》到底是极端的例子。在这种物我交融之中,情感的表达未免过于强烈。更多的时候,则要更蕴藉,更深厚,也更耐人寻味。日本文学的特点,不仅在一个“细”字,还在一个“淡”字。但是这仅仅是就表现本身而言,若论底蕴则是很浓郁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并不针对社会,而是针对人生;并不仅仅针对人生为情节所规定的那一时刻,而是针对人生的全部。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充分的直接交流根本不可能进行,所表达的只是一点意思;另一方面,对于人生沉重而悲观的感受,几乎是先验的,命定的,不曾说出大家已经心照不宣。底蕴就是这种感受,细节是底蕴的表露,而表露往往只是暗示而已。夏目的《玻璃门内》虽然是随笔,但前面讲过,日本的小说与随笔并无根本区别,所以也可以举为例子。有个女子向作者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然后问他如果写成小说,会设计她死呢,还是让她继续活下去。这问题他难以回答,直到把她送出家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本文学与我(2)
“当走到下一个拐角处时,她又说道:‘承先生相送,我感到不胜荣幸。’我很认真地问她:‘你真的感到不胜荣幸吗?’她简短清晰地答道:‘是的。’我便说:‘那你别去死,请活下去吧。’不过,我并不知道她是怎样理解我这句话的。”
这应该说是更典型的日本式的细节。心灵的极度敏感,情感的曲折变化,含蓄的表达方式,不尽的人生滋味,全都打成一片。人与人之间距离既非常远,又非常近。在夏目自己和岛崎、谷崎以及井伏鳟二等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见到类似写法。此外日本的“无赖派”,如太宰治的作品,人生体验也是特别深厚的。
这种瞬间与细微之处的感受体会,除关乎人生况味,还涉及审美体验。可以说日本文学对世界最独特的贡献就在于审美体验的全面与细致。忽略了这一方面,恐怕世界文学多少有所欠缺。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在审美方面显得特别突出的那些作品,如谷崎的《春琴抄》和《疯癫老人日记》,川端的《千只鹤》和《睡美人》,不仅是世界文学的异数,可能也是日本文学的异数,因为这一方面毕竟太突出了。谷崎、川端仿佛专门描写的东西,实际上也见于别的作家笔下,只不过糅杂于其他描写之中罢了。而日本文学的真正特点正是将人生况味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话说回来,细细品味谷崎、川端的上述作品,其实也未必那么单一,只是一方面太精彩,将另一方面掩盖住了。他们写到审美体验,也就写到了人生况味,就像夏目等写到人生况味,也就写到了审美体验一样。在日本文学中,人生况味总是诉诸于审美体验,而审美体验也总是体现了人生况味,《细雪》和《雪国》都是很好的例子。
日本文学的审美体验,所强调的是两个方面。第一,美只在瞬间与细微之处,稍纵即逝;第二,所有的美是感官之美,美是所有感官之美。这当然有赖于细节描写。如果忽略细节,日本文学就没有美可言。例如《雪国》的开头,“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就是对一瞬间视觉与心境上黑暗与光亮、狭隘与开阔之间强烈对比的细腻把握。日本文学不仅把我们通常看到的视觉与听觉之美写尽了,而且扩展为嗅觉、味觉和触觉之美,在所有感官审美方式的体验和表现上都达到极致。这是《源氏物语》以后日本文学的重要传统,而现代作家几乎无不有所继承。前引《棉被》的例子,就是写的嗅觉与触觉之美。棉被既是情感投注的中介物,也是审美体验的中介物,时雄所感受的,最终是芳子在嗅觉与触觉方面呈现的美。如果对此不能接受,对整个日本文学也就难以接受。作家永远期待着与之心灵相通的读者,期待读者能够对他的理解加以理解,对他的体会有所体会。这里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有如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
审美对象的无限性与感官的开放性是相互依存的。很少只有某一感官单独启用,美最终是对所有感受的综合,或者说是通感。在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中,这一审美过程作为复杂的系统,其间发生了多种借代、递进、转换和扩展的关系:
“忽然发现加代坐在我的旁边。我看到这个加代一面露着一种妖艳的谜一般的微笑,一面直望着前面。也许是她听到了我的自言自语。我像直接地感到了她的肉体。她胖得简直要撑破白皙的皮肤,浑身滚圆,甚至连脚趾都油光可鉴。在她身上,大概没有一块皮肤松弛的地方吧。接着,突然我就像看着樱花盛开时那样,情绪变得郁闷而厌恶起来。于是,想起了从她房间里不断冒出的煮肉的味道,它笼罩了我的心。一下子我的情绪变坏了,想吐,就悄悄地站起身来。这时,我的视线移到她的膝盖周围。那膝盖别扭地弯曲着,粗大的腿像圆木似地装在肥胖的腰上。因此,她给我的印象就像蹲着似的,她的上半身要比其他的人高出一截。
“我从令人窒息的、狭窄的房间走到走廊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想,她的肉体充满着人间的梦想。”
情绪近乎戏剧性地变化之后,感官之美充盈了整个心灵。美穿越一切,美是终极,它不受人世间逻辑的限制,或者说,美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美是字面之外所有东西的真正联系。日本文学的美呈现于所有细节,而细节总是弥散的,作为感受体会的对象,细节在作品中并不孤立存在。无论审美体验,还是人生况味,日本文学往往是从别人笔墨所止步的地方起步,最终完全另开一番天地。
巴别尔与柳托夫(1)
巴别尔的《骑兵军》里有个贯穿始终的“我”——既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又是重要角色。从书中只言片语的描述看,“我”无论职司、相貌还是经历都很像作者自己。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中,“我”被人称作“文书先生”,乃是首次表露身份;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中,师长萨维茨基提及“我”“架着副眼镜”,设营员则说:“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第九篇《拉比》中,“我”的身份进一步得到证实:“在那儿,在车站,在第一骑兵军的宣传车上,等着我的是成百簇闪烁的灯火,电台奇幻的亮光,印刷间不停飞转的机器,以及那篇未给《红色骑兵军》写完的文章。”在同一篇里,“我”还承认是犹太人,来自敖德萨;第十一篇《机枪车学》讲到“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他姓格里休克,年三十九”;第十八篇《一匹马的故事》中,“我”自诩“是个性情平和的人”;第二十五篇《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首次借助他人之口,叫出“我”的名字“柳托夫”——巴别尔当年参加布琼尼骑兵军,用的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巴别尔的照片,也是萨维茨基所形容的样子。其间惟有一点出入,即《我的第一只鹅》中,“我”自称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在后来为《骑兵军》补写的《吻》中,再次提到“我毕业于法律系”,而巴别尔并无这一背景。
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托夫这位《骑兵军》的叙述者已经预先出现在作家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里了。其中每每见到诸如此类的自我提示:“要写写集市”、“写写正午时拥堵在残破的桥头前的辎重大车”、“要写写通信员、参谋长和其他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即落实于柳托夫的叙述之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中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