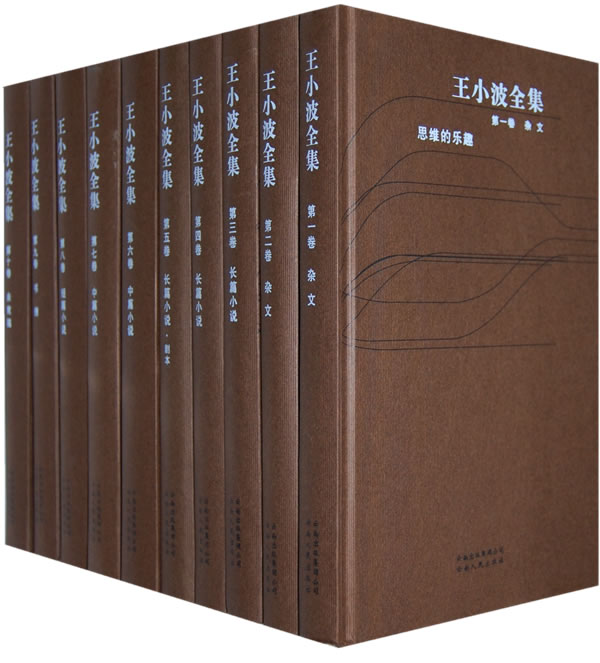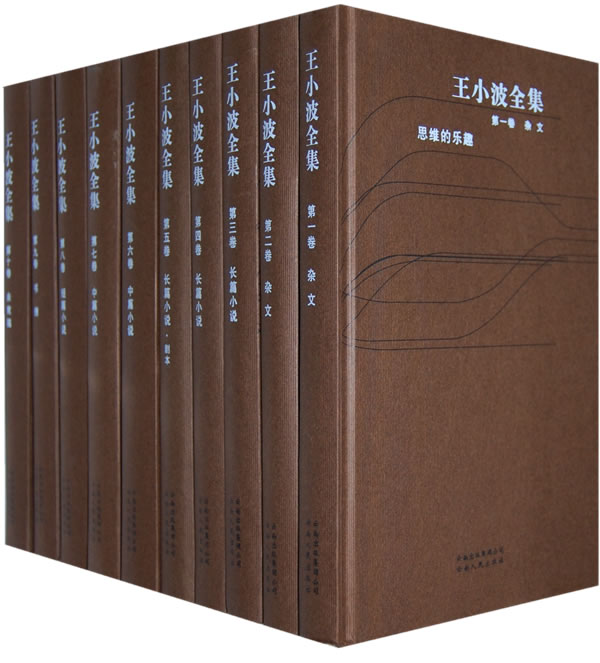王小波全集第二卷我的精神家园-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大匣子里。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宗族和孔孟哲学没有合法的权威性。真正有权威的是村落。办事都要按一定规矩办,想问题要按一定方式去想,不管你乐意不乐意。这既不是因为古板,也不是因为有族规,而是因为有一大群人盯着你。我相信,这样的解释更加合乎实情。她描述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你怎么挣钱,别人不管;但你怎么过日子,大伙就要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当然难有崭新的过法。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所依据的是在山西、浙江两地的调查。她的见解十分敏锐,遗憾的是实证功夫稍有欠缺。假设她的调查不是在这两地的两三个村子,各百十户人家里,而是在散布在全国的上百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里完成,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要求近似扳杠。因为她用的是人类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面对面交谈,通过翻译都会遭人诟病。人类学的前辈大师米德女士在萨摩亚实地调查多年,只因为听人转述,就遭人耍了。考虑到这种情况,谈了百十户,谈得扎实,也就不错了。最主要的是,她不是在文献里找出个说法,然后在调查里验证一番,而是自己来找说法,到调查里验证,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她阐述的现象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罢了。北京城里没有村落,但有过胡同、大杂院,有一些人员很少流动的单位。在这些地方,隐私也不多,办个什么私事,也难说全是个人决策。因为这类现象并不陌生,你看了这本书,不会怀疑村落文化的真实性。
罗素大师曾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方法,思辨就不重要了。实际上,要提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下一番思辨功夫。这真是至理名言。据我所知,这番功夫她是下了的。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那么是否能说,他们的幸福观就是这样,另外的快乐、幸福对他们来说就不存在了呢?在结束了在山西的调查、浙江调查未开始时,李银河给《二十一世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不能详加引述,以免文章太冗长。简单来说,结论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以此为据,村落文化的实质就容易把握了。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2)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有人重视啦,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啦,写了多少学术专著啦,但是这些在她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发现。
***
《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李银河著,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于同性恋问题(1)
从1989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几经波折,终于得到了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圆满的结果——发表了研究报告,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他们的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有一些显著的缺点,也有一些显著的优点。优点在于首次发现了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着广泛的男同性恋人群体,并且存在着一种同性恋文化——我们说的文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指一个群体内全体成员共有的信息,具体来说,指关于同性恋活动场所、相互辨认的方式、绰号、圈子内的规范等知识。我们对这种文化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描述了其内容。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发现。
这本书的缺点在于没有按统计学的要求来抽样,故而所得的结果不能做定量的推论。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性格外向的勇敢分子,他们只是全部同性恋者中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情形是他们转述的,所以由此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多少有些偏差。
一些人带有固定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知不知道有同性恋这件事,或者是否经历过同性恋行为,这种倾向始终存在。因为有了这种倾向,一旦他开始同性恋行为,就不能或者很难矫正过来。而没有这种倾向的人,可能会在青少年时期涉及同性恋活动,等到成年以后,却会发生变化,憎恶这种活动。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很可能是遗传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也有可能是在童年养成的——我们发现它和初次性经历有很大关系。一件有趣的事是,世界各地的人,不论其种族、文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带有这种倾向。我们说的同性恋者,就是指这样的人。现有的资料说明,终身的绝对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1%到10%,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仅从我们发现同性恋人群的规模来看,肯定超过了男性人口的1%,但是到底有多少,却无法确知。假如你有个孩子惯用左手,你可以禁止他用左手写字、用左手拿筷子,但是他的左手毕竟是较灵活的手。这种情形和同性恋的情形是一样的。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可能没有机会经历同性之间的性生活,但是他始终渴望这种性生活。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把这种现象当作自然现象来看,虽然它的形成过程可能与童年的生活环境这类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大中城市都有同性恋人群,他们在一些公共场所相互辨认、攀谈,找到自己中意的人后发生性关系。但是在这种场合活动的人,只是男同性恋者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在自己周围寻找Xing爱的对象。在后一种情形下,涉及到的人就不一定纯然是同性恋者。有些与常人无异的年轻人会在无意中同一位同性恋者交上朋友,加之本人尚未结婚,就很难说是完全自愿,也很难说是完全不自愿地参与了同性间的性生活。这说明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是不能仅仅从行为上区分的,真正的分界是看某人在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两种性生活方式中选择哪一种。我们说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1%到10%,是指终身的绝对同性恋者。只是偶尔(一二次或某段时间)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境遇型同性恋不计。除此之外,我们对同性恋者的生活、同性恋的原因以及同性恋者的价值观念等等做了研究和描述。这些在书里都写了,不再赘述。在此主要分析一下与同性恋有关的伦理问题,这是我们在书里没有谈到的。
一个人的成长大体受到三种力量的左右:他父母的意愿,他的际遇,他本人的意愿。而一个人成为同性恋者不是因为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一种际遇。就算这是遗传决定的,一个人带有何种遗传因子,对他自己也是一种际遇吧。既然这不由他本人决定,同性恋就不是一种道德或者思想问题。我们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性恋者像其他人群一样有些负面的现象,比如喜新厌旧、对恋爱对象不忠诚、对妻子家人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倾向等等,这些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或者道德问题,有一些具体的人应当为此负责任。但不该让全体同性恋者为此负责。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长成一个同性恋者,包括同性恋者本人在内。这是因为同性恋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遇到比常人不利的成长环境。这种愿望无可非议,但是现在举不出什么可靠的方法可以防止孩子成为同性恋者。发现孩子有同性恋倾向,也没有可靠的办法矫正。
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种说法,把同性恋称为“社会丑恶现象”,列入了应当根除之列。在惊愕之余,我们也感觉到一些人对我们的社会期望之高。假如我们这个社会是一片庄稼地的话,这些同志希望这里的苗整齐划一,不但没有杂草,而且每一棵苗都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那位以同性恋为“丑恶现象”的人心目中的“美丽现象”吧。不幸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某种意志的产物。这种现象的内容就包括: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性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有些事原本就是某个样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我们都知道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们对同性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道德上比较清白无辜,同性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少有人同情,故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我们的好几位调查对象就曾受敲诈,遭殴打,事后也不敢声张。有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现在可以给它加上一句:敲诈同性恋。打聋子缺德,是因为他不知你为何打他,也就不知该不该还手;骂哑巴缺德,是因为他还不了口;扒绝户坟缺德,是因为没有他的后人来找你算账;敲诈同性恋缺德,是因为他不敢报案。这四种行为全在同一水平线上。照我们的看法,这才是“丑恶现象”,应当加以根除。一个现象是否丑恶,应当由它的性质来决定,而不是由它是针对什么人来决定。
关于同性恋问题(2)
国外不少社会学同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娼妓、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甚至与男性相比之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全体女性,帮助他们改善生存环境,改变于人于己有害的行为方式,以便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我们研究同性恋现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但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使公众对这个社会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有所了解,并持一种更符合现代精神的科学态度。
***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第1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发表时题目为“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