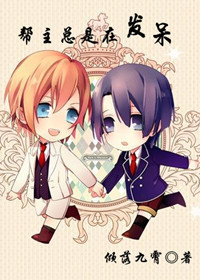梦里闲情总是君-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表姨……”陆其双终于失去平静,声音哽咽,双肩轻微颤抖。
江晚樵心里顿时揪成一团。
哀哀哭了半饷,妇人终是被手下扶着走了,陆其双恢复平静,依旧直挺挺地跪着。
从晌午到黄昏,从晴天白日到暮色四起,陆其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跪着,除了在表姨面前流露出些许脆弱外,至始至终都平静地向往来之人鞠躬,道谢,还礼,然后焚烧纸钱,江晚樵没看见他流一滴泪。
天色越来越晚,进屋的人渐渐的少了,没了,只剩跪在堂下的陆其双和几个下人,看着甚是凄凉。
“少爷,今天估计是没人来了,您去用些饭吧。”管家走到他身旁低声说。
陆其双一动不动。
“少爷,您一天没吃东西了,夜里还要守灵,您不吃点东西哪有力气熬下去。”
“为了老爷,您也吃点吧。”管家说着说着,声音也略带着颤抖。
陆其双终于开口:“先带他们去吧,我随后就到。”
管家扶起旁边几个跪着的下人,先行离去了。
出门前又看了看身在暗处的江晚樵,江晚樵朝他做了个“请放心”的手势。
灵堂里光线越来越暗,只剩牌位前抖动不停的烛火。
陆其双终于抬起头,远远看着堂前父亲的长生牌位,轻唤了声:“爹。”
江晚樵心里一紧。
听见他又唤了一声:“爹……”
眼泪随之簌簌落下。
“其双不孝,其双不孝。”陆其双喃喃地重复这句话,泪水顺着脸颊低落在衣襟上,大颗大颗的,连结成串。
江晚樵静静地看着他,只觉手脚都动弹不得。
陆其双扶着地面,艰难地起身。无奈跪了整整一天,双腿早已麻木,尤其是膝盖,针扎似的疼,身边没有可扶之物,他狼狈地站起来,一个摇晃,便要倒下去,江晚樵冲过去,一把扶住。
陆其双似被下了一跳,浑身一抖,待看清楚他的面容后,眼中露出写诧异,却一闪即逝。
“你怎么还没走。”
“我说了要陪你的。”
陆其双不再说话,从他怀里退开,堪堪稳住身子,却怎么也迈不出步。
江晚樵也不理会他的反应,将他一把拦腰抱起,放在宽敞的梨木椅子上。
将陆其双安置好,江晚樵又单膝跪在地上,双手轻轻地帮他揉捏膝盖和小腿,疏散筋骨。
“晚上睡觉前用热毛巾好好敷一敷,否则这两天都走不了路了。”
“我要守夜的。”
江晚樵双手一顿,又道:“那也不能跪着了,伤了腿,以后是个大麻烦。”
陆其双伸手拂开他,平静道:“去吃饭吧。”
弥补
花厅里,饭桌上依然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除了四周立着的下人,空空荡荡。
“大家累了一天,下去休息吧。”
下人们安静地撤出去。
陆其双在江晚樵的搀扶下坐好了,执起竹筷,却不看眼前的米饭,只端过一旁的粥,低头安静地吃。
江晚樵看看他,也不勉强,向他碗边的小碟里夹了筷菜,柔声道:“不吃饭,多吃些菜也好。”
陆其双顿了一下,头也不抬:“吃完饭,你便走吧。”
江晚樵也停下筷子,侧着连脸看他,“我留下陪你不好么?”
“晚上守灵,没什么好陪的,你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
江晚樵脸有些微热,低声道:“我,我看看你也好。”
陆其双“啪”地一声放下竹筷,冷笑道:“怎么?怕我寻死觅活?”
江晚樵一惊。
“以后整个玉茶居都是我管,这点事还怕我熬不过么?你未免也太瞧不起我了。”
那方才独自在灵堂落泪的是谁,疼得站不起身的又是谁。
江晚樵不接他的话,只问道:“你还有别的亲人么?除了下午来的表姨。”
“都在南方,应该还在来的路上。”
“那在你亲人来之前,我就在这儿陪这你。”
陆其双冷冷看他一眼,嗤笑道:“织锦堂呢?你不管了?”
江晚樵想说“有我爹在”,话刚要出口,又赶紧咽下去,装作随意的样子说:“也不是离了我就不行。”
陆其双继续低头喝粥,沉声道:“随你。”
虽然已入了夏,夜里的风还是有些凉,下人们关好门窗,又拿了薄毯给自家少爷围上,便靠在墙边一阵一阵地打瞌睡。
江晚樵坐到陆其双身旁,替他掖了掖边角,低声问:“困不困?”
陆其双摇摇头,不置一词。
江晚樵看着他在烛光下显得越发瘦削的脸庞,有些艰难地开口:“那天晚上,我……”
“江公子,热水端来了。”
管家端着水盆,胳膊上搭着毛巾,立在一旁。
江晚樵接过来,将毛巾浸湿,又蹲下,轻轻卷起陆其双的裤脚,直挽到膝盖上。
陆其双浑身一震,怒道:“江晚樵!你疯了?”
下人们一下被惊醒,都莫名地看向这边。
江晚樵也不松手,沉沉地看了他一眼,一手握住他小腿不让他动弹,一手将热毛巾敷在他膝盖上,轻柔地按压。
陆其双握紧了椅子,指节发白。
看着江晚樵从他一只腿换到另一只腿,陆其双突然轻声笑笑,了然道:“你这是为那天的事赔罪么?其实真没必要,一切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不想天公不作美,让我病了一场,不过也没死不是,你这样,倒真折煞我了。”
江晚樵心里像被人狠狠抓了一下,抬眼看他,却只看到笑得弯弯的眉眼。
管家下人们纷纷投来探究的目光,江晚樵低声说了句“以后再跟你解释”,又转身搓洗毛巾。
陆其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会儿,便歪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江晚樵果然言出必行,几日来吃住都留在陆府,前去织锦堂时从陆府出发,处理完生意再回到陆府,陆家下人知道自家少爷此次所受打击甚大,便乐得有人出面帮忙,都把江晚樵当座上宾看待,陆其双则依旧是一副不咸不淡的样子,不再赶他走,也不与他多说话,江晚樵只当他还在生自己那晚失约的气,并不放在心上。
江府派人来催了他几次,都被他压下去。
一日,奉了江老爷命的小厮又来催江晚樵回去,正巧陆其双从旁边经过,听了个正着,江晚樵背对着他,原没看见,倒是小厮瞧见了,忙打了个千儿,叫了声“陆公子”,江晚樵扭过身来,一时尴尬不已。
这边江晚樵还急的不知说什么好,那边陆其双却不瞧他,只倚着廊柱,斜挑着眼跟小厮调笑道:“回去跟你家老爷说,你家少爷不回去了,就在我府上做上门女婿。”
小厮知自家公子与陆其双交好,又听不出其中的讽意,只当个玩笑话,讷讷地赔着笑。
倒是江晚樵像生吞了头牛一样,眼瞪得老大,直直地望着陆其双离去的背影,直到拐进屋里瞧不见了,还呆愣愣地立在原地,把旁边的小厮看的莫名其妙。
这日晚上用饭时,陆其双便发现江晚樵有些异样,先是不停地给他夹菜,嘴里说着“多吃些多吃些”,眼睛却不停地盯着他瞅,瞅一会儿,又扭过头去,心不在焉地扒拉米饭,嘴角还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陆其双皱了皱眉,只当没看见,可没一会儿,一双眼睛又瞟过来,偷偷摸摸地看一会儿,又扭过去低着头笑,一两次陆其双便忍了,可一顿饭快吃完,江晚樵就跟抽了筋似的拿他瞅个没完,陆其双终于受不了了。
“我说,你今天没事吧?”
“啊?没,没事啊。”江晚樵像是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愣了一下。
“那你总瞅着我笑做什么?我脸上长花了?”
江晚樵慢慢放下筷子,脸悠悠地红了,“你,你不是让我做你家女婿么?”
这下轮到陆其双愣住了,好半天回过神,脸又“腾”地烧起来,骂了句“你脑子有病吧”便急匆匆地出了饭厅。
江晚樵忙在后面巴巴地跟着。
“喂,是你自己说的啊。”
“连我家下人都听见了,你可不能耍赖!”
陆其双终于停下来,却依然背对着他。
“江晚樵,耍人很好玩么?”
江晚樵顿时急了,“你说清楚,这到底谁耍谁?”
陆其双不再理他,直奔着自己书房走去。这几日来,他不仅要料理父亲后事,还要打起精神重整家里的生意,从早忙到晚,着实辛苦。
眼看着陆其双一脚踏入房门,江晚樵哀哀地道:“其双,你就莫生气了,我那天……”
陆其双却突然扭过身来,对门外人笑道:“所以说,你是答应了?”
江晚樵有点反应不过来:“答应什么?”
陆其双挑了挑眉:“做我家女婿啊。”
江晚樵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我,我……”
陆其双继续笑:“其实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说的可不是做我爹的女婿,而是……做我的女婿。只可惜,我现在还没有女儿,所以,你还得等上几年。”
陆其双站在屋里,笑得如沐春风:“乖乖等着吧,我的好女婿。”
说罢“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没几日,陆其双远在南方的亲人终于赶到,一大家子人在灵堂里又是一番哭天抢地,江晚樵远远地看着那人的身影,心里依旧有些苦涩,却知道自己终是没什么理由再继续呆下去了,便命人收拾收拾回府去。
回到府里,江老爷正在前厅自己跟自己下棋,江晚樵刚准备上前请安,却见父亲直起身子,瞧着自己冷言冷语道:“哟,还知道回来啊,我还当你记不得回家的路了呢!”
说罢将棋局一推,拂袖而去。
江晚樵辛苦了几天,却落得个左右挨骂,里外受气,站在前厅里委屈地摸了摸鼻子。
偶遇
从铺子里出来,正是晌午时分,江晚樵上了自家轿子,悠悠地朝家里走去。
从织锦堂到江府的路上,必经一间经营火爆的赌坊,白天夜里都热闹非凡,灯火通明。江晚樵不好这个,向来也没什么注意。
是时正值盛夏,轿子里难免憋闷,江晚樵便挑起窗帘,摇着扇子透气。
拐过这个街角,走不了几步便是那间赌坊,江晚樵远远瞧见赌坊门前几个虎背熊腰的男子正和名女子交谈着什么。
咦,这年头女人也出来赌博?当真罕见。
江晚樵颇有兴致地朝那边张望。
慢慢地走近了,江晚樵发现,他们似乎不止是在交谈,而是在争辩,或者说,是在吵架。
“二十两?那都是一个月前的老黄历了,你出去打听打听,我们聚财坊有白借人钱的吗?”其中一名男子掂了掂手里的钱袋,恶狠狠地说。
“那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从二十两涨到一百两啊,你们,你们分明就是在讹诈!”女子据理力争。
“哈哈!讹诈?我们就是讹诈又怎么样?有本事季老二别来我们这赌钱啊!愿赌服输,你个女人懂个屁!”
“就是,要不是看在妹子你有几分姿色的份上,今日要还的可不止一百两哟!”旁边一个神情猥琐的男子开始出言不逊。
“是啊是啊,要不……小娘子你陪我们兄弟几个乐乐,把大爷们伺候好了说不定我们又给你少点儿,哈哈哈!”说着一只手就要伸上去。
女子连忙扭身避开,江晚樵坐在轿子里几乎可以她微微颤动的肩膀。
“哟,不乐意啊,成,不乐意也成!一百两雪花银,现在就拿来,少一个蹦子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