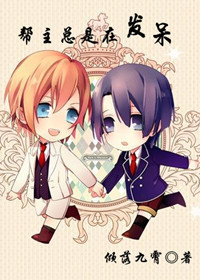梦里闲情总是君-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少爷?”范三忙扶住他,焦急地唤了一声。
江晚樵只觉脑中混沌一片,眼神都失了焦距,范三看自家少爷脸上又是震惊,又是喜悦,又是茫然,又是愤怒,不由得有些心惊。
“少爷?少爷!”
江晚樵失神良久,眼神终于渐渐清明过来,又紧盯着手里的信,仿佛能给那七个字看出个花样,半饷,才小心翼翼地将信折起收进怀里。嘴角露出了丝冷笑。
“范三,此事你功不可没,但记着,万不能与别人说起。”
“爷你放心。”范三坚定地点点头。
正在前院练太极的江老爷突然听见门外一阵马蹄声,抬头便见自家儿子驾着马一阵风驰电掣而去,好笑地摇了摇头,“去个铺子着什么急,真是。”
“来人!开门啊!快开门!”江晚樵在陆府前翻身下马,拼命地拍门。
没一会儿,一个老奴便过来开了门。
江晚樵不及老奴开口,便一把推开朝里面大步走去。
“哎,江公子,江公子!”老奴忙在后面跟着,“你可是来找我家少爷的?我家少爷不在!”
“不在?”江晚樵忙停下脚步,“那是去哪了?”
“这……”老奴露出犹豫的模样,陆府的人都知道,这些日子自家少爷很不待见这位江公子,几次上门都是闭不见客的。
“你不说,我便在府里等他!”江晚樵不耐道。
老奴忙赔着笑,低头道:“奴才哪敢,只是,公子来的不巧,我家少爷南下去了。”
“什么?!”江晚樵知道这南下必是十天半个月回不来,一把揪住他衣领,急道:“什么时候走的?”
“怕是有一个多时辰了罢。”
江晚樵问清了方向,二话不说,上马便追。
忘言
秋日的寒风夹杂着泥土扑在面上,江晚樵独自一人在驿道上策马狂奔。
他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按了按胸前,摸到怀里的信,心里隐隐有些抽痛。
误会,偏见,天意,人为,他一次一次错过他,糟蹋他的心意。
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偷吻他。
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情一次次来江府跟随他左右。
听见自己对晚樵的心意,他又是怎样不管不顾地替他解蛇毒。
他听见他说:“我亲你,是因为我……喜欢你啊。”
后来自己说了什么?
“你这种行为,真让我,真让我觉得恶心!”
让他觉得恶心……呵,自己怎么就那么蠢!
江晚樵按紧了怀里的信,将它紧紧地捂在胸口。
他说“勿负尾生之约”。
“勿负尾生之约。”
然而自己不仅负了约,还让他在城外淋了一夜的雨,生了大病。
江晚樵……你这个蠢材!!!
他用力抵住胸口,让信封硌进皮肤里,以缓解心里的痛。
一路南下,江晚樵不敢做丝毫停留,遇到驿站,也只是进去搜寻一圈,没见到人,便换匹马,继续往下一站奔驰。
约莫走了两三个时辰,江晚樵终于在驿道前方看见一队身影,当头的便是那个自己一路追寻过来的人。
“其双——”
“其双——”
江晚樵一甩马鞭,加快速度,直奔到队伍前方,然后一转马头,猛拉缰绳。
马蹄嘶声,江晚樵在队前停下。
“吁——”
“吁——”
“吁——”
陆其双一行没想到后面突然冒出来一人拦在前方,躲闪不及,纷纷拉缰停马。
“喂,小子,你疯啦!”
“妈的,不要命了你!小心老子撞死你!”
众人纷纷咒骂,江晚樵却像没听见一样,只直直望着队伍中一人,口中喃喃。
“其双。”
“其双。”
陆其双堪堪稳住马匹,皱着眉朝前方望去,双眼蓦地睁大。
“你——”
“其双,我有话跟你说。”江晚樵众目睽睽之下一步一步走到陆其双跟前,语气平静。
却掩不住抓着缰绳的手隐隐地发抖。
“什么话不能回去再说?”陆其双收起脸上错愕的表情,显得有些冷淡。
江晚樵不答话,只定定地看着他。
两人下马,直走到离队伍稍远的一处小丘后面,方才停下。
“好了,说吧。”陆其双也不问江晚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便开门见山。
江晚樵望向眼前男子的眼睛,只看到平淡中隐约有些不耐,不由得胸口一窒。
他握了握拳,从怀里取出那封信。
陆其双脸色一白。
“你什么意思?”
“其双,”江晚樵伸手拉住他,眼神坚定,却掩不住声音里的颤抖,“其双,我错了。”
陆其双笑了一下,却并没有挣脱。
“你何错之有?”
江晚樵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之前我误会你与季姑娘有私,对你,对你口出恶言,又……负你约定,害你生病。”
陆其双又笑了一下,淡淡道:“就这?”
江晚樵有些愕然,不知他言语何意,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陆其双看了看自己被握着的手,缓缓抽出来,一字一句道:“江公子当真有闲情,为了这么几句话大老远跑过来,那么其双便生受了。只是其双家中生意繁忙,实在耗不起时间,这便得走了,江公子保重。”
说着当真便要转身。
“其双!”看着他冷淡的模样,江晚樵脑中简直一片混乱,本能地拉住他,不由分说便吻过去。
“唔……”陆其双一时没反应过来,推拒不及,就这么猛然被堵住了唇。
江晚樵一手握着他胳膊,一手环过去揽住他的肩背,嘴唇相贴,一动不动。
看眼前人似没什么反抗,江晚樵制住他的力气小了些,只用嘴唇缓缓摩擦着他的,似是抚慰,过了一会儿,又伸出舌来轻舔了对方一下。
陆其双蓦地一抖,身体僵硬,江晚樵立马感觉到了,也见好就收,松开手臂。
“其双,你别急着走,听我说完好不好。”
陆其双垂着眼帘,看不清表情,却也没露出马上便要离去的样子,江晚樵便又拉了他的手,语气诚恳道:“其双,误会你是我不好,你想怎么打我骂我都行,可负约当真不是我本意,是……是有人从中作梗,故意施计让我没去成。没想到,没想到那天下那么大的雨……后来,我又有急事去了宁州一趟,谁知道一回来,就听见你爹去世的消息……”
江晚樵面色黯然,继续道:“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也一直没机会向你解释,要不是那天在街上遇见季姑娘,我,我定然还不知道实情。”
他紧紧拉住陆其双的手,柔声道:“其双,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罢。”
半饷,陆其双终于抬眼看他,却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知道错了又怎样,原谅了又怎样。”
江晚樵有些紧张地看着他。
“我,我知道你喜欢我,其实我也,我也……”
“江晚樵。”陆其双突然出声打断,语气却听不出什么波澜。
“以前,就当是我错了,以后,你也莫再错了。”
江晚樵大惊,急道:“你,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不喜欢我了?”
陆其双移开眼睛,不知望在哪里。
“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我只是,醒悟了。”
“醒悟,醒悟什么?”
陆其双淡淡地笑了笑,不动声色地拿出手,轻声问道:“你知道我和我爹最后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我都在做什么么?”
江晚樵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这样问,茫然地摇了摇头。
“那时候,我正因为你的误会和恶言相向赌气在家不吃饭,而我爹,就每日在家里劝我进食。”
江晚樵心中苦涩不堪,无法言语。
“从小,我爹就恨不能把我捧上天,当爹又当娘,还要管理府里上下事务。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很辛苦,很辛苦。”
陆其双在袖子里握紧了手,指甲深深掐进肉里。
“而我,在长这么大以后,还在他临走之前,为自己一点点不堪启齿的私情和他赌气,伤他的心。你说,去死的是不是应该是我?”
江晚樵胸口一阵钝痛,痛得他几乎快呼吸不上来。
“不是!不是这样,是我的错。其双,是我的错!”
他仅仅握住陆其双的肩膀,只想一把将他圈进怀里,融进骨血。
陆其双却轻轻拂开他的手,摇了摇头:“不是谁的错,是我自己不孝,愚蠢,怨不得别人。”
他垂了垂眼帘,继续道:“如今,即便是我跪死在我爹墓前,也无济于事了。为我挡风挡雨的人已经不在,而这个偌大的陆家,还指着我来管,你觉得,再说那些,还有什么意义?”
江晚樵死死盯着眼前神色寡淡的男子,两眼发红,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多谢你能大老远的跑来与我道歉,以前,我是怨过你,但现在,”他苦笑了下,“什么也没有了。”
陆其双转身朝队伍走去,江晚樵就这么呆呆地站在原地,双拳紧握,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灵魂。
眼见着他快要走出自己的视线,江晚樵终于哑声道:“其双,还有我,还有我在,我不会离开你的,永远不会。”
翻牌
回京城的路上,江晚樵几乎是浑浑噩噩毫无知觉了,他丢了马鞭,任凭身下骏马在官道上撒开腿地跑,天越来越黑,驿站也关了门,不知走了多远,马持续劳累又不曾进食,嘴角已开始泛起白沫。江晚樵索性放了马,继续独自往前走。又不知走了多久,天竟下起雨来。江晚樵心下茫然,对落在身上的雨滴也不管不顾。
雨越下越大,天也越变越黑,豆大的雨滴砸在身上很有些疼,乌压压的雨幕中,江晚樵朦朦胧胧地想,那个晚上,其双也是这么一个人在郊外淋雨么?不知他冷不冷,夏时的雨,必然比现在还大,倘若,那时候我去了,此时又是番什么情境?
江晚樵进城的时候,天已蒙蒙亮,雨势渐小,淅淅沥沥的雨滴落在青石地面上,溅起水花,积成一个一个的小水窝。路上行人还不多,三三两两的举着伞避着地上的积水走,深一脚浅一脚,很是艰难。江晚樵却不怎么管,走到哪是哪。
行人们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街上这个状若疯狂的人,全身上下湿到透,衣服上,鞋袜上,到处都是乌黑的泥水,面色青白,头发散乱,简直不是一个狼狈便能形容的情状。然而本人却像浑然不知,只直着眼踉踉跄跄地往前走。
能在这个时间起床的大都是些卖苦力的底层百姓,并没有人认出他,都皱着眉一脸嫌恶地避开,生怕这人突然发起疯来生了什么事。
织锦堂江府今天一天很不平静,先是自家大公子昨日一夜未归,一大清早却被小厮在自家府门前的台阶上发现,早已不知昏迷了多久。其后便高烧不退人事不省,忙乱了一屋子的大夫与下人。
喂了药,屏退了一屋子的下人,江老爷亲自在床前为儿子换毛巾敷额头。
“晚樵,晚樵。”
看着儿子烧得发红的脸,江剑川心中既是心疼又是焦急。
连睡觉都眉头紧皱,是这些日子压力太大了么?
他擦了擦江晚樵头上的虚汗,见儿子嘴巴微微动了动。
“晚樵,你说什么?”他将头低下去,耳朵贴近江晚樵的嘴巴,细细地听。
江晚樵依然在昏睡当中,一双俊眉狠狠拧在一起,嘴巴却喃喃地不知在说什么。
“是不是不舒服?要什么?爹给你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