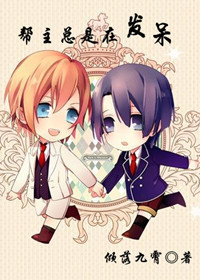梦里闲情总是君-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哟,不乐意啊,成,不乐意也成!一百两雪花银,现在就拿来,少一个蹦子儿也不行!”男子马上目露凶光。
“麻烦,麻烦几位大哥再通融几日,我……”
“通融?我们跟你通融,老板可不跟我们通融!今日就是约定的最后期限,要么拿钱,要么,就拿他季老二两根手指头!”
女子身体猛地一抖,几乎快要跪下,喏喏地说:“求你们,求你们……”
小轿渐渐的快要行过赌坊,江晚樵继续打着扇,并没有什么要下轿的意思。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又有空同情谁呢。
“哼,你不是有个有钱的相好吗?叫他拿张银票过来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什么相好?你胡说些什么?”女子有些羞恼。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如今玉茶居的大当家陆其双,不是你姘头嘛,难道说,你在他眼里,连一百两银子都比不上?”几个男人猥琐地笑起来。
其双?!江晚樵手下一顿,扇子“吧嗒”一声掉在地上。
“你们,你们莫要胡说!我和陆少爷清清白白,我们,我们……”
“哎哟,瞧这小脸儿白的,当真是护主心切。我可不管你们清不清白,倘若你今日拿不出这钱,别说是玉茶居大当家,就是你说出天王老子来,也不管用!”
“是么?那不知这印着天王老子的银票管不管用?”江晚樵慢悠悠地从后面踱过来,接过小厮手里的银票,笑着递到那几个男人面前。
“一百两,一个蹦子儿不少,闭上你们的臭嘴,别让我听了恶心。”
“你!”男人作势要冲上来,江晚樵却捏着银票,冷笑地看着他,没有丝毫露怯的样子。
打手们看看江晚樵,又看看他身后的一干下人,知道这是个不好相与的主儿,一把拿过银票,又瞪了一眼旁边的女子,愤愤地进了赌坊。
江晚樵冷眼瞧了瞧那几人的背影,却不看那女子,转身便走。
“多谢公子出手相救,敢问公子贵姓,来日民女也好将银钱还与公子。”身后的声音虽不甚大,却坚定沉稳。
江晚樵停下脚步,淡淡道:“钱就算了,我只是不想听见一些有关其双的无聊传言。”
女子一下子飞红了脸,讪讪地低下头,却一眼瞧到江晚樵腰间所挂物什,突然出声道:“公子请留步。”
江晚樵微有些不耐:“还有什么事?”
女子低身福了一礼,问道:“敢问阁下可是织锦堂的江公子?”
江晚樵心中略感诧异,脸上却不表露出来,只问道:“你怎么知道?”
女子低头道:“江公子所配之物民女认得,听少爷说,正是赠与了江公子。”
江晚樵瞅了瞅自己身上的玉佩,又抬头看看她,并不做什么表示。
“不知,少爷现在可好?”女子似有些艰难地开口。
江晚樵心中冷笑,“他好不好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女子能感受到对方言语间表露出来的明显的敌意,绞着衣带不知说什么好。
江晚樵不想再与她纠缠下去,转身便欲离开。
女子忙又深深一福,感激道:“不管怎样,民女代家父谢过江公子,来日必将钱款还与府上,请公子放心。”
“你说什么?家父?”江晚樵突然转过身来。
女子有些诧异,只好答道:“不瞒公子,家父生性好赌,这钱正是他在这间赌坊所输,民女是代父还债。”
江晚樵心中一动,连说话都有些急躁:“这,这么说,以前打你的,也是你父亲?”
女子猛地抬起头望向他,脸上既有诧异,又有羞愤,半饷,才低头小声道:“家父脾气不好,又素爱饮酒,有时,会有些,冲突。”
江晚樵像是一个闪电直劈中天灵盖,倒吸一口冷气。
“民女季沉鸢,与其双少爷自小相识,也算是……算是竹马青梅。”女子咬了咬唇,脸颊微红。
江晚樵执着茶壶的手顿了顿,依旧不动声色地往茶盏里添水。
女子坐在桌前絮絮道来,江晚樵这才知道,原来眼前女子的娘亲生前在陆府做乳母,对陆其双颇为照顾,待陆其双长到十多岁时病故,而她与她爹本不是陆府的人,便搬了出来。说起来季沉鸢也当真是命苦,自打季母去世,季老二便整日酗酒度日,流连赌坊,可怜她一弱女子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整日揽活为父还债,日子过的很是艰难,陆其双顾及往日情分,便经常施以援手。
听到此处,又想起当初对其双的种种误会,江晚樵不由得内心翻腾。
“之前,我和其双有点小误会,闹了点不愉快,”江晚樵小心地组织措辞,“所以一直想和他赔个不是,却没什么机会。不知,季姑娘能否多与我讲些关于你家少爷的事,嗯,越详细越好。”
季沉鸢抿着嘴笑了笑:“江公子不用担心,少爷的脾性我是知道的,心软又好说话,你若诚心与他道歉,必没有被拒的道理。”
江晚樵笑着抿了口茶,心道,心软好说话?我怎么没发现,本少爷在他那吃瘪的次数可不算少了。
“少爷能把那双鱼玉佩赠与你,便能说明在他心目中你的地位不比旁人。”
江晚樵眉梢一挑:“喔?我虽知道这玉佩是件好物,却不知它如此重要。”
季沉鸢继续道:“打从我记事起,这玉佩便没离过少爷的身,据说是夫人生前留给少爷的。”
江晚樵心中一动,这怎么颇有些给自家儿媳的意思。
“后来,少爷身子变得不是太好,老爷又专门带少爷去了趟五台山,拿这玉佩请高僧开了光,所以,”季沉鸢认真地看了他一眼,“足以可见此物之贵重。”
江晚樵轻轻摩挲手中的玉佩,心里像压了块铅石般沉重。
季沉鸢沉吟片刻,肃然道:“我虽不知江公子与少爷因何生了间隙,但就这玉佩来说,足以见得江公子在少爷心目中分量之重,望公子……莫要负了少爷才好。”
江晚樵心中越发愧疚,讪讪地笑了笑。
两人各想各的心思,桌上一时无话。季沉鸢转了转手中的茶盏,突然道:“老爷去世不久,少爷他,还好吧?”
江晚樵楞了一下,随即苦笑道:“我也许久没见他了,恐怕他……此时也不想见我。”
季沉鸢哀叹一声:“陆府原本就人丁单薄,可好歹有老爷支撑着,现下,连老爷都不在了,留得少爷一个人……”说着眼圈便微微发红。
“说起来,陆夫人走的早,陆老爷又只有其双一个儿子,就没想过再娶一个?”江晚樵轻叩杯沿,不紧不慢地问道。
其实,江晚樵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听人说,陆晋则是娶过二房的,然而没两年,就又被赶出来,其中缘由,外人并不清楚。江晚樵虽不是个爱打听家长里短之人,然而关于陆其双的,他却想面面俱到。
季沉鸢闻言神色一动,明显不愿多说,江晚樵也不急,坐在那悠悠地等。
半饷,眼前女子才迟疑地开口:“其实……也不是没有,只是,后来又被老爷休了。”
果然。“喔?那是为何?”
季沉鸢神情更加难看,甚至有些忿忿的:“要怪也只能怪那女人,竟敢对少爷下黑手……”
江晚樵眉心一跳。
“那女人一心要给老爷生儿子,这原本无可厚非,可她狠就狠在,自己儿子还没着落,就担心起少爷影响她母子在府中地位,竟然,竟然故意引少爷到后院荷花池边玩耍,趁着没人,将,将少爷推进了荷花池!”
季沉鸢越说越激动,两只手都握紧了:“那时候少爷才六岁,大冬天的,没一个人发现,捞上来时,整个人都僵了。后来,烧了三天三夜,差点就没了命。”
“哮喘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江晚樵不知不觉握紧了桌角,几乎快把一小块木头扣下来。
季沉鸢点点头:“为这事,老爷一直自责,认为是自己把那女人引进家,把少爷给害了,后来更宠着少爷,也再没提过填房之事。”
季沉鸢饮了口茶,略平复了一下心情,怅然道:“虽然那时候我也不过十来岁,可我永远都记得少爷被人捞起来时的样子,整个人都是青紫的,嘴里还不停地念叨‘救我,救我’,要不是有下人做活正巧经过那里,真不知道……”
“啪”的一声,桌角活生生被江晚樵掰下来。
季沉鸢唬了一跳,抬头见江晚樵脸色阴沉。
“此事也是旧事了,沉鸢多嘴,还望江公子莫在少爷面前提起的好。”
江晚樵沉声道:“这我晓得。”
“我听少爷说起过,公子对少爷有过救命的恩情,可能因为这个,少爷才如此在意公子吧。”
江晚樵挽了下嘴角,眼里却不见笑意。
我救过他,我又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救的他?若他不是陆其双,不是陆家大少爷,我会不会救他?他,现在又会在哪?在那个时候,他是不是也像小时候落水那样无助,只抱着能被人发现的期待?而我……又真的救了他么?
江晚樵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
殷勤
来不及从丧父的悲痛中清醒过来,陆其双已经被接连而来的种种压力砸得直不起身。陆晋则的猝然离世,给了陆家所有人当头一棒,而站在这风口浪尖上的,自然是陆老板膝下的独子——陆其双。
陆晋则为人干练且精明,北到大漠商路,南到江南茶园,上到朝廷人脉,下到贩夫走卒,没有什么是摆不平搞不定的,要说他唯一一个弱点,就是他这个儿子。
听说过玉茶居的人都知道,玉茶居的少东家不仅是家中独苗,还是实打实的病秧子——陆老板疼的不是一般的紧。没有寻常纨绔子弟的娇纵跋扈,没有心思透亮的计谋手段,对谁都是副温和无害的面孔,在其他商家里的同龄孩子都开始参与家中业务时,陆其双还刚刚从最边缘摸索起。唯一一次远行,还是那次差点要了他命的西域之行。这样的阅历,怎能不让人起疑心?
“齐世伯。”依旧是一袭月白色长衫,只是似乎更单薄了点,陆其双起身迎接刚踏进门来的几名中年男子,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微笑,恭谨而又矜持。
“其双啊,好久不见。”被称为世伯的男人亲切地拍了拍陆其双的肩膀。
两边落座,宽敞的雅间里没有小二在场,陆其双的手下安静地为双方斟了茶。
“嗯,当真是好茶。”齐用天品了口茶,赞道。
陆其双笑着执起茶盅。
“没想到去年和你以父亲一别,竟然就是最后一面,真让人,真让人遗憾啊。”陆其双看对面的男人叹了口气,又突然转了话语道:“只是,世侄也知道,你父亲出事的那条商路,正押的是我宝芳斋的货,结果……”
真不愧是商人,说话没一点客套。陆其双笑了下,沉声道:“世伯放心,这点道理其双还是懂的,这次的事故虽是天灾,但按照合约,货是积在玉茶居手上的,损失自然由玉茶居一并承担,再按照往年的盈利份额,府上帐房会尽合算出具体数目,转到宝芳斋帐下。”
齐用天笑了两声,大声道:“世侄果然爽快,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玉茶居做了这么些年的买卖,若连这点信用也没有,不叫人看了笑话?”陆其双轻叩杯沿,缓缓地说。
“哈哈,这是自然,这是自然!”齐用天看了看眼前面色青白的后辈青年,似有些犹豫地开口,“世侄啊,你也知道,近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