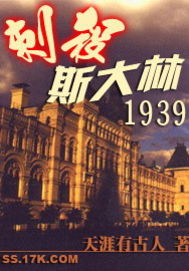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右的东方年轻人。安德列其时已经满16岁,因此列拉非常惊讶,这二人之间何以有共同之处。安德列解释自己与苏汉的交往说,他们都喜欢摇滚乐,并都喜欢当时青年人的偶像麦克·贾柯尔。 记得,有一次,这是在1983年的8月初。我像往常一样12点左右开车回家吃午饭。将汽车泊在地下的停车场,乘着列拉准备午饭的时候,我打算上到楼顶游泳池。穿浴袍时,听见隔壁房间里安德列的声音: “爸爸,给我车钥匙,我想去拿放在车厢里的磁带……” “钥匙在门厅的小桌上,赶快上来,一起游游泳……” 从这幢20层高的大楼上,可以看到城里的美妙风景,以及地平线那边的绿色山丘。游泳池边放着藤椅和躺椅,地面铺着花花绿绿的橡胶毯。在阳光下呆了一会,然后游了一会,没有等到安德列便下楼回房了。 “为什么安德列没有来呢?”我问列拉。 “难道他没有跟你在一起吗?他没有上这儿来。去车库看看,他可能在听那个麦克·贾柯尔。” 在车库里,我在泊车位置没有看到汽车。也许,安德列刚刚学会开车,他想玩会车,然后停在另一层?走遍了四层的车库之后,还是没有找到他。 安德列在哪儿?他会不会出事?车库的大门自动开关,汽车进来时的缝隙足以使坏人潜入。发现男孩之后,他可能将其捆起来,推入后货箱,然后驶出车库。这种事情曾经有过,但我不愿往坏处想。我走出门外,绕楼一周,又走了几个街区,但是安德列和汽车都无影无踪。 回到家里,我问了列拉,安德列有没有回来。她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会去哪儿,那辆庞大的“奥尔斯摩比”又会到哪儿去?它可是用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资金购买的。不过,汽车有保险,如果它被盗,钱还可以收回来。 最重要的,是安德烈怎么啦? 我们一口饭都没有动,作了各种猜测。我们翻看了安德烈的记事本,偶尔找到了苏汉的电话号码。也许,他知道些什么?我拨通电话之后,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我是苏汉。” “非常抱歉打扰你。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最近见过他吗?” “是的,我见过他。” “问题是,他现在不知去哪儿了。我的车也不见了。他会出什么事吗?” “我今天见过他。他好像打算去纽约……” 这真是胡说八道!我们一家三口前不久去过纽约,所以我没有计划再次去那。把这个情况讲给了苏汉。 “这可能是安德列的幻想。非常遗憾,我帮不了你们。” 如果安德列坚持自己可以开车到纽约,又该怎么办?我听说,麦克·贾柯尔将在那里举办音乐会。可是,安德列没有驾照,他勉勉强强能够开动汽车,根本弄不清楚复杂的路线。华盛顿与纽约之间的道路大多是收费的,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在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先不打电话到使馆引起恐慌,而是先找当地警局。十多分钟之后,来了一位交通警。我解释了情况,并告诉他,尽管这不大可能,但安德列现在可能正在通往纽约的某条路上。 “他多大了?”警察问道。 “十六岁……” “噢,这个年纪的人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他们脑子里有时会有些怪念头。不要担心,我们会很快找到他的。您的车很容易发现,您是外交牌照。有特别巡逻队观察这类车子。您还来不及回头,我就会把您的小逃兵送回来……” 他满有把握,这使我们打起了精神。真的,像我那样的车子不难找到,何况驾车的是个男孩子。但是,过了一小时,又一小时,而交警并没有打电话来。又等了一个小时,我又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我们正在办理您的事情,”他回答说,“不要着急,会通知您的……” 列拉已经彻底失神了。不得不通知我们的领事。那边当然会惊慌:苏联孩子失踪了!领事说,马上到我们这儿来。要我们不出家门。又过了一个小时。显然,大使馆的领导们讨论了别列什科夫家里的“意外事件”。 领事最终还是来了。 “安德列回来了吗?”他在门口精神抖擞地问道。 知道了安德列还没有回家后,他开始安慰我们,列举了各种类似的、顺利解决的事例。列拉讲述了安德列与苏汉有些怪异的交往,以及后者推断,安德列可能驾车去纽约。 “让我跟这个苏汉谈一谈。”领事说。 我拨通了熟悉的号码。一个女人声音答了话。“我能否跟苏汉说几句话?” “苏汉已经也不在这儿住了,他出国了。”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这很奇怪。”领事说,“如果苏汉真的跟安德列的失踪有关,那么就大事不妙了……” 这一点不用他说我们也明白。为什么警察到现在不能查清楚安德列的所在?为什么外交牌照的汽车没有被发现?要不这苏汉是个强盗,劫持了安德列做人质,将他连人带车藏在了什么地方?或者,是些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大使馆的工作日结束了。领事跟我们一起又呆了一会,告别时,要我们如果得到什么消息,立即给他打电话。 剩下我们两人,完全不知究竟如何是好。我尽量安抚列拉,虽然我也明白,我们倒霉了。我们的打算全都被打乱了。
永不愈合的伤口(2)
我在美工作的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安德列也将从使馆的八年制中学毕业,应该在莫斯科升入九年级。由于美加研究所还没有物色到接替我的人,我们已经定下来,八月底列拉和安德列回莫斯科,我留下来在华盛顿等待接任者。我已经替他们订了机票。可现在这一切都悬在了空中。我们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大约夜里两点,电话铃响了。 “我在这儿,在大堂里。你们下来吧,”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是安德列,”我急忙告诉列拉。“教训他一顿……” 安德列站在大堂里,有些失神,并且我觉得眼睛有些浮肿。 “汽车在门口……我开不进车库来。” 我们出来走到“奥尔斯摩比”跟前。似乎一切正常,只是速度表上显示,在最近12个小时里,汽车跑了几百英里。看见他可怜的样子,我什么也没有问安德列,泊好汽车,上楼回到家里。列拉,她忘记了要“教训”,扑上去亲吻拥抱儿子。可他站着,不做声,无动于衷。我最后问他: “是不是说说,你到底怎么啦?” “最好明天再说。给我水。” 他一口气喝了两大杯水,用手背擦干了嘴唇,很勉强地说出来一句话: “我困死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衣服都没有脱,一下子就睡着了。 那一夜,我们当然是一眼未合。我给领事打了电话。他也没有睡。他的一句话使我感到刺痛:“我们希望,这事就这样结束……” 早晨,无论我如何查问,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要么故意不回答,要么坚持说,什么也不记得了。列拉和我本来应该去上班了,可是能不能把安德列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得不带上他。将儿子送到使馆的小餐厅后,我上到二楼,向奥列格·索科洛夫通报情况,大使多布雷宁在莫斯科期间,他是临时代办。 奥列格也对于此事是否会这样过去,表示了疑虑。实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个失踪的苏汉的结识,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车,还有安德列怪异的举止…… 我们决定,为以防万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苏航有班机飞往莫斯科。我们跟奥列格关系相当好,我觉得,他在诚心诚意地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 电话响了,奥列格拿起了听筒,但是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在变。他用感叹词作答,挂上电话之后,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纽约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的莱斯里·盖博。他刚刚拿到了安德列写给里根总统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请求在美国避难。这封信将在报纸的晚间版上刊登出来……” 我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但这种打击实在是出乎预料。那时,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里根把我国斥为“罪恶帝国”。并且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即便他还是个孩子,向美国总统请求政治避难!这对于那些“冷战”斗士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安德列跟我什么都没有说? 也可能,这只不过是挑拨离间?不过,骚扰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突然之间,我的儿子成了一桩丑闻的对象,况且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将是毫无限度的…… 奥列格打断了我苦痛的思绪: “我想,最好你们全家马上搬到大使馆生活区来。记者和穿便服的家伙们很快会到你在切维-切斯的家里去的……” 我的脑子一下子还不能消化我们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后果。就向在云雾中一样,我下到小餐厅,安德列正在那里安静地喝着可口可乐。很难不跟他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必须平静,这样才能弄清所有情况。首先得去新闻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儿的《苏联生活》杂志社工作。然后赶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赶到使馆去。 我和安德列走到车旁。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你真的给里根写信啦?说实话。” “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国。我不喜欢在莫斯科的生活。这里好玩多了。”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啦?” “开车去纽约,想去找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拿了妈妈放在床垫底下的钱缴路桥费。实际上,全程都有巡逻车跟着我。警察冲着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没有栏我。” “你看他们是否知道你的打算?” “也许。但是,在纽约他们不见了,而我迷了路,吓坏了,后来决定回家。” “你要这些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中学毕业,上大学,受教育。然后再来这里工作的。” “可是谁会放我来这儿?这会是惟一的机会。” “你在这儿没有专业,没有受过教育,谁会用得着你?他们自己的失业者也够多的了!” “我想试一试。要么成功,要么死了。这比在家里混日子强多了。你运气好,你可以到这儿来。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的。” “可是你想没有想过妈妈和我?” “想过,所以才回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也是这个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剧,“冷战”冲突的产物。由于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进行竞争,我们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老一代的人,经受过艰难的岁月,可以继续忍受,坚持英国人的说法:“不管对与错,这是我自己的国家”。但是,甚至我们这些人,也喜欢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里,伤心于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辈。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组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公开地谈论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能容忍这些颠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处国外时。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却难得多。从学校给他们灌输的,是应该讲真话。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套。 安德列对于假话和虚伪那一套的反感特别强烈。 有一次,大使馆中学的八年级学生要画一幅画,反映苏联维护和平的斗争,安德列画了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