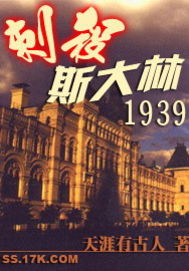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经常跟其他穷苦家庭的大学生一起到一家餐馆里,那里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壶水,和切成大块的面包,都不要钱。在那里,他们可以拿一份新报纸,什么菜也不点,做出一副正在读报的样子,然后悄悄的就着水把面包吃完。为了维持学业,父亲还作过家教。大学毕业之后,他马上就得到了普梯洛夫造船厂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工资很高。他娶了城里有名望,但已经败落的一家人的女儿。当时觉得,生活似乎将是富足幸福的……可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破灭了。一个孤儿付出的巨大努力,忍受的苦难全都白费了…… 外祖母变卖了家传的珠宝,从投机商人那里弄到吃的东西。这可以使生病的父亲营养好一些,我们其他人也要想办法支撑下去。房子里已经不供暖气了,所以我们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没有劈柴烧壁炉,但一个铁皮的小炉子救了我们。它有四个长长的支脚,放在客厅屋子中间的一块铁板上。像排水管一样的管子贴着天花板,弯弯曲曲地通到窗户的透气口。我们已经烧光了一打椅子,还有外公的写字台。现在轮到厨房里的橱柜了。有些精明的商人生产这种小铁炉子。原来富人区的住家户现在就靠这种炉子,因为中央供热系统早就失效了。它很快就能烧得通红,茶壶里的水几分钟就烧开了。但是,小铁炉子凉得也很快。夜里,室内温度在零度以下。 1941-1942年间,当时莫斯科也没有供热,这种小铁炉子再次出现。1942年,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后,在彼得罗夫街分给我们那套房子里,这铁炉子也救了急。 父亲在慢慢地康复,他开始能上街了。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材料,也没有订单,他工作的普梯洛夫船厂早已经关闭了,大部分工人被动员上了战场。城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父亲有一个姐姐叫柳芭,她住在乌克兰,在离父亲老家切尔尼戈夫大约一百多里地的一家乡村医院里作助产士。 “要不,到那儿去?”父亲提议说,“那这地方一直都是富裕,好客……”“你们在那儿靠什么生活呢?”外婆表示怀疑。“我随便找一个工作,无论如何,那里比这边好活一些。您看看,您的外孙多么瘦。在这里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他现在需要牛奶,蔬菜和水果。这些东西在乌克兰多的是……”听着他们说话,我想象自己躺在一个小棺材里。最近几个星期,这种事情我见多了。就像后来四十年代的围城时期一样,悲痛的人拖着小棺材走在彼得格勒冰封的人行道上。我躺在小棺材里一动不动,而他们三个人,弯下腰,撒下了眼泪。于是我开始嚎啕大哭。“你这是怎么啦?”妈妈严厉地斥责道,“闭上嘴,已经都那么瘦了……” “别那么粗鲁,”外婆干涉了,“他那么弱,而且神经也弱。” 我哭得更厉害了。总是受不了别人可怜我,哪怕有人开玩笑地说“小可怜,小可怜见的”,我马上就会放声大哭。 我这一通发作,再加上虚弱的样子,成了出走的新理由。但外婆固执起来了: “你们走吧,我留在这里。” 不管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听。 “我一个人能撑下来,”她叫我们放心,“所有东西都卖了,再说我也不需要太多。反正快活到头了。我已经活够了。这里有父亲,祖父,曾祖父的墓地。我也要呆在这里……” 最终决定,我们自己走。 收拾上路很简单。妈妈把衣服,毛毯,卧具等等放进一个类似箱子一样的藤筐里。她跟外祖母要了一本家族的相册。我加上几册插图杂志《金色童年》。那里面的插图非常漂亮,类似现在的幽默画。后来,我靠这些杂志学认字。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夜半敲门声:“杀死犹太鬼”!(2)
终于该告别了。整整一天,外祖母紧紧地抱着我,她亲手用革命前积攒下来的面粉做了甜馅饼。我头一次看见她流泪。也可能,她感觉到再也见不着我们了:我们离开一年之后,外祖母就饿死了。 南方之行路途遥远,万分艰难,十分复杂:要穿过内战的几条战线,有时要乘坐挤满了人的火车,有时要乘马车,有时候,把行李装在独轮车上,父亲推着车子一路步行到下一站。对于四岁的我来说,路途太艰难了。记得,有时候出现胸部疼痛,就像多年之后心脏病发作时候的那种痛感一样。我自己走不了,甚至连手也活动不了。父亲被长途跋涉折磨得十分疲倦,他生气了,以为这是我在装样子。甚至有一次轻轻拍了我一巴掌。妈妈替我说话,要我们停下来,喘口气。可他还是要我接着往前走。我感觉到再走一步,一切都全完了。我倒在地上,不能动弹。父亲不得不把我放在独轮车上。我知道父亲本来已经很难了,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甚至觉得,如果我消失的话,他们会高兴的。当然,这样想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但是,每当出现疼痛的时候,我自己想死去,解脱他们。我牢牢记住了几件事情。 ……在一个小站上,一大堆人挤在一列货车旁。所有的人都带着背包,箱子,篮子等等。人们挤来挤去,大呼小叫。火车已经鸣笛,马上就要发车了。我们必须赶上去挤到冷藏车厢里去。父亲头顶上顶着筐子,挤进了车厢,他伸出手来给母亲,母亲一只手拉着我。两边的人挤得我很痛。我刚要挣扎着抬腿上阶梯,突然,人潮一下子把我挤到了一边。我从妈妈的手里滑脱了,摔倒在月台上。人群在挤着,我看见妈妈一点点被推进车厢里边去了。父亲想要挤出来,但周围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火车开动了,我一个人留在了月台上。妈妈从一个人的身后伸出头来,大声喊叫着,但没有人注意她。车厢一节节从眼前闪过,但我的脑子里转得更快:我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就像我在各个车站上见过的许多衣衫破烂,饥饿的孩子们一样。突然,什么人有力的手臂把我捞了起来。最后一节车厢的阶梯上,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水兵衫,敞着呢制服的水兵把我放在了车厢里。他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看见了我被人群分开,听到了妈妈的哭喊?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接下来的我全都不记得了。很快我跟父母亲会合了…… 在破败的国内经过三年漂泊,记忆中留下的是痛苦的饥饿感。 记得已经到了乌克兰的什么地方,村子边上有一座歪歪斜斜的房子。一个犹太人家庭给了我们一个容身之地。时间还不算晚,但天色已经黑了。炉子上烧着水。妈妈准备给我洗头。一家之主在屋子角上,披着条纹布,在低声祈祷。两个儿子围坐在桌子边低头读课本。父亲对母亲小声说: “你看看,多么坚强的人。学校现在肯定都关门了。但是他们自己学习,将来一定有出息。”女主人把一个旧木盆放在小凳子上,倒进开水。妈妈加了一些凉水进去,她把我的头摁在木盆上,于是我看见,从头发缝里小小的淡黄色小动物成堆地爬了出来,在热水中挣扎一会,死了。 “快看呀,”我喊道,“这是虱子……” “天啊!”女主人叹了一声,“对不起。现在虱子到处都有。没有肥皂,人们营养不良,可不就是要出虱子的。” “没关系,”妈妈安慰我说,“虱子的确到处都有。现在我们把水倒掉,再用开水烫一遍木盆,都会好的。给你们两块肥皂,这是我们自己存的。” “太谢谢了。”女主人表示了谢意。 回想着这个遥远的故事,我想的是,1990年,莫斯科由于洗剂用品短缺,以及明显的营养不良,许多中学生的头发里也发现了虱子…… 早晨,我跟主人的两个儿子到村子里走了走。村子大半已经废弃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商店。商店的主人,肥胖、上了年纪、典型犹太人长相的约瑟夫叔叔卖给我们一小铁桶煤油,——这是去虱子的最好方法。他送给我了一只粘土作的口哨。 夜里,枪声,马蹄声,喊叫声把我们吵醒了。女主人低声警告说,要我们躲起来。 “这附近有一帮泽廖内的人,”她解释说,“这不,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了……” 突然,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该死的犹太鬼,快开门!”传来了醉醺醺的喊叫声。 “这里没有犹太鬼。我们都是乌克兰人,东正教徒。”父亲还没有忘记乌克兰语,他朝外面喊道。 “那就算了……” 马一声嘶鸣,听见了马蹄声。然后又是几声枪响。 早晨从窗户往外一看,大家都在往商店的方向跑去。我们紧跟着也过去了。在断了一个铰链的门旁边,约瑟夫叔叔躺在血泊之中。他的衣服被掀起来了,肚子高高地鼓着。他的妻子跪在身边痛哭着……
我们的口粮:燕麦粥和青鱼(1)
一家人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基辅,谁知昔日富裕的古都正在闹饥荒…… 艰难的漂泊之中,年幼的我几乎丧命在土匪的枪弹之下…… 火车停在了达尔尼茨。再往前无路可走了。第聂伯河上通往基辅的所有桥梁都被炸断了。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但天色还是黑的。既没有电筒,也没有篝火。勉强能够分辨出来的旅客们,拖着自己的物件,从车厢里挤出来。我们也出来到结着冰的月台上。寒风刮起了雪,扎在脸上像针刺一样。车站的房屋被毁,窗户都打烂了。剩下的一半门悬挂在绳子上,时不时地撞在墙上。我们走进车站,想躲一躲刺骨的寒风。这里也是四面透风,不过在墙角,原来售票处的地方,风小一些。我们席地而坐,等待天亮。妈妈铺开了羊毛毯,安顿我躺下,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起来吧,”我在梦中听见妈妈的声音,“爸爸找到了一辆车。要继续赶路……” 小小的站前广场上积了一层雪,空无一人。乘客们都四处走散了。父亲站在一匹又瘦又小的马拉雪橇旁边。身穿破破烂烂的半长皮大衣的,正是车夫。篮子和包袱已经装上去了,中间把我塞进去,父母亲坐在两边,我们就出发了。到河边只有几里地,但这匹小马拖得很艰难。我第一次发现一种怪事:当我闭上眼睛,老是觉得在往回走。也可能,真的就是这样。是否正因为这样我们怎么也走不到第聂伯河边?我拼命赶走睡意,使劲挣着眼睛,这样才能往前走。这条路通过一片树林。这里的路上坑坑洼洼,雪橇一会儿弹起来,一会儿又滑到路边。这把我逗笑了,有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眼前就是第聂伯河。岸边的河水已经结冰,冰面上露出黑色的一条小径。但是,在河道中间是窄窄的水面。在这里,几个砖桥墩之间,横着被炸断的桥架。再往前,又是覆盖着一层雪的冰,一直到对岸,紧接着是陡直的山峰,那里可以看见基辅山洞修道院的金顶。 “我们怎么才能到对岸?”妈妈绝望地问道。 “没关系,太太,能过去的,”马车夫不慌不忙地说,一边帮着父亲把东西摞在雪地上。“大家都过去了。你们先走这条小路,然后从桥架上走过去。不过要小心些,慢点走,别掉到水里去。” 我们旁边有几个人,刚从对岸过来。他们证实说,桥梁的桥架非常结实。车夫带上新的乘客,调转雪橇,离开我们走了。 我们在冰面上拖着东西,终于挪到了工字钢铆接起来的桥架。有人在桥架上绑了一根粗铁丝,当作扶手。父亲先帮着母亲过到对岸去。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