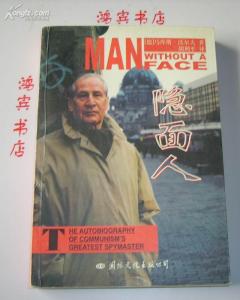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极其乏味。情报这一行说到底其实十分枯燥,从浩如烟海的杂乱无章的情报中筛选来筛选去,只为了找到一粒使人开窍的宝石或是有启发意义的线索。为了换换口味,我坚持亲自掌管10到12名间谍。据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报机构首脑中,这样做的人只有我一个。我得以不时地溜出国家安全部大楼,去位于柏林郊区的安全据点或德累斯顿和其他地方与这些间谍会面。我个人更喜欢是后者,因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们在国外的间谍被捕时,以上工作习惯自然被打断。通常我们先从新闻中得到消息。由于新闻报道有时会把一名间谍的名字搞错,我们必须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们的间谍还是其他国家的间谍。有时,某个处的处长会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不幸的消息,特别是有人叛逃时。平时我们已养成了习惯,遇到这种事时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图避免自乱阵脚。应付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追问已经够让人胆战心惊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后,当务之急是弄清还有谁会因此陷入险境,而不是追究责任。我们会立即用密码发报给间谍,通知他们情况紧急。鉴于间谍不可能每天都打开收音机听广播,有时甚至有必要直接给他们的家打电话,用暗语报警。例如,如果一位间谍是商人,暗语可以是:“下一场会不得不延期举行。”我们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顿的舅母病危”这样明显的警告暗语。此外,还使用一些标记报警,如在一位间谍每天经过的一颗树上钉个钉子,或是在一个邮筒上画个十字。不过这种办法不适用所有的间谍。
我担任情报局长的最后10年里,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每周6天,天天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时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不过我尽量做到每月至少看两次话剧或听音乐会。访问友好国家的情报机构或接待他们访问东德的代表团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借此逛逛博物馆,去剧场看看戏。周末一般都在位于柏林东北方向20英里的普伦登小村的乡间别墅度过。在此其间我尽量摆脱一切公务的纠缠,过一天老百姓的日子。1985年,我在莫斯科时的童年伙伴乔治和路易斯访问柏林时,看到我在乡村自由走动,不带任何警卫,颇感意外。米尔克有一名贴身保镖。有一次还命令我也带一名,可被我想办法打发走了。我的司机出于保卫我的需要受过特殊训练,但从来不带枪。我自己的枪锁在保险柜里。
虽然我对效力的制度心存疑虑,平时过的却是一种养尊处优,位高权重的生活。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都很难放弃这一切,主张改革。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认为任何改革只能自上而下。此话出自一个似乎有权有势的人之口,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可我的权力只及情报局。只有这里才是我的一方小天地。
西德首任驻东德大使高斯是一位悟性极强的人,对我们的困境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由个人小天地组成的社会。许多东德人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对官方政策不闻不问,只顾忙自己的事,求得有自己一方不受外界干扰的小天地。我也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那就是我主管的情报局,虽然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
听了我对自己生活的这番形容,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过的是一种可悲的官僚生活,当初干这一行只为了贪图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错了。我对情报局局长这份工作十分满意。我确信情报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我曾有意避开了担任更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职务的机会。对上面提升我为主管新闻的官员的提议,也婉言谢绝。这一职务将使我掌管宣传工作。甚至连我的孩子也劝我不要去,因为这会使我大接近政治领导人,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磨擦。 1961年8月13日修建柏林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马上会有重大举措出台。柏林东区的居民普遍悲观失望。每个星期,劳动力和商品短缺的情况都在恶化。一天,我从一家商店外面排的长队旁走过,听到一位老太太带着浓重的柏林口音骂道:“人造卫星可以送上天。时值盛夏却吃不上新鲜蔬菜。这就是向我们宣传的社会主义。”
如果青年人选择在边境另一边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谁又能指责他们呢?在西德,他们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水平东德人望尘莫及。这些青年人不觉得自己背叛了哪个国家。他们只不过移居到德国的另一半。多数人在西德有朋友或亲戚,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自从1949年东德成立以来,270万人逃到西德,其中一半人不满25岁。我不禁想,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不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后代的话,是不是也会远走高飞。1961年8月9日那一天,西柏林共接收东德移民1926名,创一天接受东德人数之最。东德好似大出血。它的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地逃向西德。国家为培养这些人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失去他们,东德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下降。我感觉,我们正在泥淖里挣扎。
我方公开提出的指控是,西德正在试图抽尽东德最后一滴血。这一提法听上去显得不无凄楚。其实说白了就是,西德再现繁荣后,它对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人们宁愿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铁饭碗,告别家人,到前途未卜的资本主义社会闯荡。毋需赘言,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官方对修柏林墙做的解释,即关闭边界是为了预防迫在眉睫的入侵,或是阻止敌特的渗透。但随着这堵东德正式称为“反法西斯防御屏障”,西德则称为“耻辱墙”的修建,所有人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
我不仅明了修建柏林墙的真正原因,而且还正式表态支持修建它。我认为,当时舍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我们接管的一半德国历史上一向不如另一半发达,因而一开始底子就薄,再加上后来经营不善,困难就更大。此外,苏联军队还拆运走了东德的工业机床设备,甚至连铁轨这样的基础设施物资也不能幸免。苏联把这些物资统统视为战争赔偿。而西德却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重建了自己的国家。我曾幻想,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合理的国内改革,我们的生活水平会逐步地追上西德。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迟早会显示出来。我们那时戏言,终有一天,西德会接管柏林墙,以阻止西德人去东德。实际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我们在西德的一些间谍和同情者提出疑问,是否还有必要限制出国旅行。当时东德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改善。大多数出国的东德公民都按时归国。但退回到1961年,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不修墙,即投降。
老实说,1961年8月,我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后,和所有人一样大吃一惊。我的坦诚肯定会损害我在东德国内的名声。我能想到的惟一解释是,参与筹划这次行动的米尔克故意对我封锁消息。8月13日清晨,我和成百万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怒不可遏。我们与潜伏在西德的间谍联络的方式因柏林墙的修建一夜间发生了巨变。鉴于我们的人以后仍需在东西德之间往返穿梭,这样的事理应事先通知我。由于修建柏林墙的计划被捂得密不透风,我们甚至来不及事先跟边防军司令部打招呼,允许我们的信使穿过这道突如其来的无法逾越的边界,去西德与我们的间谍接头。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忙不迭地给我们局的人分发匆忙准备好的通行证,使他们可以穿过边防检查站,按时到西德与我们的人接头。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间谍这一行里人与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这一条。一旦断了线,势单力孤的间谍就会惊恐万状。搜集情报这台机器也会随之停止运转。
此后我们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须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边界另一边的警察会怀疑,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西德,其他的东德人却不行。对西方情报机构来说,封锁边界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关闭边界后,大批东德普通老百姓无法再去西德。西方各国的反谍报机构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可以出国的少量东德人。他们通常是因公访问的人员,如外贸官员,事先得到批准的学者等。偶尔还有一些因亲人有急事获准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坐政府提供的轿车去东柏林市内各部门办事时,会让司机绕到柏林墙施工现场,看一眼施工情况。面对正在修建的柏林墙,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亲人都在东德,所以没有体验过骨肉分离的痛苦。但柏林墙造成了无数起荒诞的事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亲一点儿边还涉及到我。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游船游览。游船从特雷普托公园驶出,最远可以开到毗邻西柏林市的新克尔恩区,然后规规矩矩地返回东德的停泊地点。这批游船皆以德国社会主义作家名字命名,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柏林墙竣工后不久的一天,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号游船欢快地启航向西驶去,演出了一场那个时代不寻常的逃亡记。一天傍晚,船上的厨师和他的家人把船长灌醉,诱他开足马力驾船全速驶过目瞪口呆的边防警察,开进西柏林。大厨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获得自由。船长躺在甲板上,醉得像一摊烂泥。酒醒后,他满脸羞愧地把船开回东德。
东德的边防军看见他又驾船回来了更为吃惊,因为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这位船长的妻子绝望中于是给任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档案馆馆长的我的母亲打电话,向她求情。
当天晚上,母亲在饭桌上问我:“你不能帮他一把吗?”我知道,在父亲眼里,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船外逃一事一定显得很滑稽。我于是请求从宽处理这位可怜的船长。在我的干预下,没有判他刑,但还是把他调离了柏林,在一个远离任何边界的工业区开普通轮船。对此我无能为力。
柏林墙修起后,我主管的情报局与负责边界安全的反谍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间谍与反谍报部门的关系从来没有热乎过,凡是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钩心斗角的历史的人都明了这一点。至于东德,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此时已降至冰点。我拒绝提供一份需要过境的我们的间谍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单,担心他们会因为我无法控制的部门人员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在某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上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才摸索出一套新的运作方式。我们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还要严,而且更难有松动的余地。这听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却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让我伤透脑筋的一例。此公是我们在西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内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处隐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让他的家人知道,但瞒不过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雷迪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会民主党决策圈内极有影响。与波恩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他不是什么国王,而是幕后决定谁当国王的人。反正对我们来说一样有用。第二次大战结束很久后,他才被美国人释放,返回德国。那一段经历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