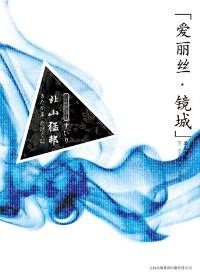第三十九年夏至-第6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肖与凡在一旁不多说一个字,东西已经送到,他自然也该回去了,他说了声告辞,便消失在雨中。
一切由大悲到大喜再到大悲,短短的时间里我却觉得自己活了后半辈子,我无力地跪到了地上,瓦砾硌着膝盖我却不觉得疼,我看着手里的怀表苦笑,笑着笑着,笑出了眼泪。
我突然在一片废墟里歇斯底里:“蒋沐!我情愿你是被炸死在这里面我也不愿听到这样的消息!”
这一句花光了我所有的力气,我觉得我能像戏文里所写的一样,一夜白头。
雨越下越大,路灯又熄了一盏,我拿着信和怀表跪在地上痴痴地缀泣,终分不清脸上的是雨还是泪。
蒋沐,第三十八年你说你要带我去台北。可第三十八年之后,我却连南京都没有离开过。
作者有话要说:
☆、第六十三章 再无年少少年郎
新中国第二年(一九五零年)
“青瓷,青瓷。”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如同剪发一般把我的思绪剪成两半。我猛地睁开眼,喘了几口气———
我倒低在床上躺了多久,竟然把以前我想忘记的事全部回忆了一边。我以为我忘记了,却反而记得更清楚。
“青瓷。”
门依旧被敲着。
我连忙把手里的簪子和信压在枕头底下,起身去开门。
门开了,叶先生站在门外,扶了扶眼镜:“在休息吗?”
我点点头,指着身上的衣服说:“你看我衣服都没有换呢。”
叶先生说:“那真对不住,可是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
我拉叶先生进屋让他坐着,自己先去换衣服。叶先生是去年年底回来的,到现在已有半年了,如今他依旧是北立大学的老师,但同时也是什么政协的什么,反正我记不清。他回来的时候模样衣着都没有变化,只是深色意气风发,笑容比以前多的多。大约是师哥说的那个原因,他的使命完成了。
叶先生回来后对我说,青瓷,新的时代来了,所以我如约而至,回来了。
多好,大家又在一起了。师哥,叶先生,戏,一个都不少。
这么想时总觉得少了什么,却又不愿意去深思。
我换了衣裳出来,叶先生已经喝了半杯茶,见我出来,问道:“听云楚说你这两天都不去唱戏,怎么了?”
我笑了笑,坐下来,“想休息两天,上半个月每天都唱全场太累了。”
叶先生点点头,“也是,你看你的脸色,真的很苍白。”
我失神了一刹那,拿手摸摸脸,“是么?休息下就好了。”
叶先生帮我倒茶,一边拿茶壶一边道:“我有事情和你说,我说了你不要太激动,因为这事我也拿不准。”
我端起杯子戳了一口茶,掩住眼里的疲惫,笑问道:“什么事?莫非你喜欢上哪位小姐了?”
叶先生摇摇头,“当然不是,是……国'民'党那边有人回大陆来了,就在南京。”
“哐铛!”
我手里的茶杯刹那间就摔了下来,茶水溅了一桌。我失神地看着叶先生,茶水沿着桌沿滴在衣服上我也没察觉。
我诧异地问:“叶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叶先生重重出了口气,回答说:“他们今晚会在戏堂听戏,也许……也许是他回来了,回来找你……”
天地都在我脑海里翻转。该喜还是该悲?我一时无法言说我的心情,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吗?
我一把抓住叶先生的手,说:“叶先生,你快去和师哥说,说今晚的戏我唱,我一个人唱!”
叶先生顿了顿,看着我摇摇头够走点点头,惋惜道:“青瓷你不必这样,同时,也不要抱太大希望,情报不一定精准的……”
我点头:“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不去我这辈子都会后悔的。”
叶先生最终出去了。我欣喜若狂,又满面悲伤,我打开柜子拿出珍藏着的戏服,摸着上面金盘针的一阵一线,叹气,我到底是傻。
我要化了此生最细致的妆,穿此身最美的行头,吊最婉转的嗓子,掩盖住所有悲伤,所有的疲惫,去迎接一个人,一个叫蒋沐的人,一个我想了,恨了一年的人。
蒋沐……多就没有念这个名字了,念起来别扭到心伤。
师哥听说我要出来唱戏,一时又惊又喜,看样子叶先生没有同他说什么,因此他不知道我来是因为一个人而不是一场戏。
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感觉到多大的变化,依旧唱我的戏,只是称呼换了不少,没有老爷,军爷,这些称呼了,百姓也不能直叫,非要叫人民群众或者劳动人民。要说我觉得好的,大概就是台下少了土豪和乡绅什么的,看着舒服了些。叶先生曾笑话我不懂世事,我只说,我没打算去了解这世事。
就唱戏吧,唱一辈子。毕竟我现在除了戏就没剩下别的了。
我扮好了扮相,问师哥:“好不好看?”
师哥连说:“好好好,特别是这眉,和柳叶一个样儿。”
我看了看镜子里的人,凤冠霞衣,眉梢挺翘,唇色红润。美,是美,我化了那么久,能不美么?叶先生说的,女为悦己者容。
戏快开始吧。我心里迫不及待地想上台看看台下。
“青瓷,该你了!”经理唤我。
“来了。”我忙起身上台去抖得凤冠上的珍珠哐哐作响。
“铛!铛铛!铛铛铛铛!”
“啊!妃子啊,只是累你劳顿,如之奈何 ———”
戏已开锣。
我从上场门上台来,第一眼就往向台子底下的听众。人那么多,一眼丝毫看不出什么来。
我碎步过去,同师哥对上眼:“ 臣妾自应随驾,焉敢辞劳。 ”
唱了没几句,我直步上前,师哥的眉头微微皱起,因为这里不应该上到台边的,我却偏要上,我是来找人的,不是来唱戏的。
我轻扶长袖,“ 匆匆的弃宫闱珠泪洒——”
又转身移步,兰花指指着台下:“叹清清冷冷半张銮驾,望成都直在天一涯 ——”
我目光在台下扫了好几遍,有老人,也有学生,还有小姐和妇女,满座衣冠,形形j□j,竟无相依。
心里的那份期待突然落了空,我刹那间明白了,就算台下有他又如何,他若真的回来了,自然会来见我,他若不愿见我,他回来了又如何。
我不由地苦笑一声,眼泪唰地下来,湿了妆。
“哟,你看,唱哭了。”
“入戏深啦,不愧是名角。”
“我也是他的老戏迷了,可他以前从没有唱哭过啊。”
台下一片哗然,师哥忙走几步拉住我,随机改了戏词:“妃子莫要悲伤。”
我以水袖掩面:“陛下啊——”
这出戏我不知道我唱的好不好,我心里空洞极了,脚步都有些凌乱。唱到贵妃自缢之时,我又哭又笑,想这到来的巧,死了一了百了。
我想把我那段情缢死在台上,但下了台才发现这是徒劳。哪怕他没有开找我,哪怕我再恨他怨他,我也止不住要去想他。
戏唱完经理跑来说大家都说我唱的好,有很多地方请我去唱戏,给军队义演,给人民群众娱乐。经理高兴地喋喋不休,我换了妆,一句话都没说就回了戏园子。
回去了我就躺在了床上休息。心跳平稳,呼吸顺畅,似乎这一场戏是一帖药,治好了我的心病。
“青瓷。”
又是敲门声,又是叶先生的声音。我没动,说:“门没锁。”
门就被叶先生推开了。叶先生的脚步慢慢移到床前,他在床边坐下,询问道:“累了吗?”
我慢慢睁开眼,说:“累了。”
叶先生不多说,帮我扯好被子,替我把被角压了压,压着压着,叶先生似乎看到了什么,把手伸到枕头边上,下一刻就扯出了那支簪子,簪子的末端还有些血迹。
叶先生惊道:“青瓷,这是什么?”
我看了一眼那簪子,不慌不忙地从床上坐起来,拿过簪子,摇摇头,“没什么。”
“你不能这么做。”叶先生立刻说道,“云楚会伤心的。”
我低头看着簪子,那翠绿如同青葱年华,只是再也不配我了,我抬头看着叶先生,痴痴道:“他没有来找我……”
“青瓷……”
“他没有回来找我……”我喃喃,“都民国了三十九年了,他还没有来找我。”
叶先生忙拉住我的手,“青瓷,这话你不能再说了,现在是新中国的第二年,民国早就成历史了。”
新中国……几个字在我脑袋里盘旋,我突然反抓过叶先生的手,狂摇头,“不是的!不是的叶先生!现在还是民国,是民国第三十九年。”
“叶先生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食言,我不相信他会对我食言!”
“一定是肖与凡骗了我!肖与凡怀恨我害死了千涟!是他骗了我!蒋沐不可能对我食言!不可能!”
我越说越激动,越说越觉得喉咙里堵着东西,我眼睛酸得发疼:“我不信……”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下半句话就被从喉咙里涌出来的血淹没。
先生惊呆了,回过神来,连忙转身去拿手帕。
我一把抓住叶先生,拿袖子抹了一把嘴上的血,摇摇头,苦笑道:“叶先生,不用了。”
又把手里的滴了血簪子塞到叶先生手里,说:“这簪子就送给叶先生你了……还麻烦你一会儿去告诉师哥,我以后只唱《寄情》了。”
叶先生握着手里的簪子,张张嘴还想说什么似的,最终他合上了嘴,紧握着簪子出来房门。
我低头看这被褥上血染出的牡丹,拿手抚摸,低声道:“你啊,认命了,就等他一辈子吧。”
不等他,我没有活着的力气。
我记起什么似的,从枕头底下拿出那张早已不能再用的支票,那是他当初给我的,我笑了笑,撕成了两半。
是夜,戏院里散了场,我一个人在后台梳了妆换了衣,把凤冠戴好,上了台。
没有司鼓,没有听众,满堂寂静,我开口,回音阵阵———
“”相思透骨沉疴久,越添消瘦……”
我挽水袖,偏头凝目:“ 望断仙音,一片晚云秋。 ”
整个戏院回当着我的声音,没有锣鼓的戏把我的声音显得更加突兀,尖细,婉转,柔美。
我兰花指往台下中间一指,我蓦地一笑———那座位上分明有一个人,他身着黄色军服,马靴锃亮,带着白色手套的手跟着我的唱腔打着拍子,他在笑,那么自负而温柔,是我最初见他的模样。
我转了一个圈,本该哭啼啼的戏我突然笑吟吟地唱:“ 对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