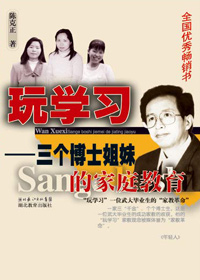读心博士-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说完我又看见一个路牌,装作对知道他的身份表现得毫不在意。
“靳博士,你不用再留意路牌了,我们一直都在绕圈,这是环城高速。”他看了我一眼说道。
“看来每个人都低估了你的智商。我只是很好奇,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吗?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在你的计划中吗?”看来,除了继续交谈,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觉得自己陷入了疑问的旋涡。与此同时,我的脑子也在高速运转。见到江瀚让我的内心有些激动,我曾对他抱有希望,根据我的分析江瀚也不一定是凶手,现在他找到了我,看得出来不仅是出于被逼无奈,而且他能相信的也只有我了。那么江瀚到底是不是凶手呢?我的分析又是否正确呢?看来一切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事情,如果你是指谋杀案,那你太高估我了,我才是受害者。至于找到你并让你现在坐在车上,这我确实计划过。”他打开收音电台,半调侃地接着说:“让我们听听音乐或者新闻吧。”
“江瀚,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被警方抓到是迟早的事,既然这样,你还不如去警察局自首。”我想通过说自首来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想不到,靳博士你也是如此官腔啊!看来人都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苟且偷生的动物。”江瀚讥讽十足地说道。
“那你凭什么感觉我不一样?”我看着他说。
“我只说一次,人不是我杀的,你信不信?”他扭过头冰冷地看了我一眼,我没发现他有任何说谎的迹象,只是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深深的恐惧。
“关于你是否杀了人,我不能随便断言。不过你可以先说说,在这次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吧?”我想,既然能找到江瀚,不是正好符合我原先的意愿吗?虽然不是我找到了他,而是他找到了我。现在我暂时也“无计可施”,听他说又何妨,可能会将所有的谜团都解开。
“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现在扮演的角色就是我自己,是江瀚,而另一方面……”讲到这儿他稍微有点哽咽,然后继续说道,“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阶段。”
“什么意思?”
“既然你负责我的案件,应该了解我的情况——我之前的病史。”江瀚很不情愿地说出这句话,就像别人在揭他的伤疤一般。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自己的病复发了?”我们之前就这样推论过,那么他说人不是他杀的,“他”也仅仅是指江瀚此时的这个人格。看来情况非常棘手,我不能掉以轻心。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只是在出院后没多久,我曾经出现幻听和幻觉。”江瀚不情愿地说道。
“幻听和幻觉?”我自言自语般小声重复道。虽说人格分裂的前期是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仅凭这个还是难以推断江瀚是否病发,毕竟我不是他的主治医生,再加上病历的丢失,更无从判断了。
“你有没有怀疑过是自己的另一个人格杀了他们?”我单刀直入地问道。
他默不出声,看似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车子继续在环城高速上快速行驶,我尝试挣脱手腕上的绳子,一点一点用力。但是江瀚就在旁边,如果动作太明显而刺激到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另一方面我在思考,即使我挣脱了绳子,下一步又该如何呢?现在车子的时速接近一百三十公里,万一有什么闪失,两个人都可能性命不保。看来,江瀚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才会选择这样一种谈话方式。
“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之一。”江瀚低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
“既然这样,就请你继续从你的角度将事情说下去。”我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你知道,当你在类似监狱的地方待上那么一段时间,然后被放了出来,你就会对自己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千万不要再回去了。因为那里等待你的不仅是没日没夜的孤寂和痛苦,还有各种骇人听闻的噩梦。”说到这里,他哽咽许久之后才接着说:“当我发现自己又出现幻觉、幻听的时候,我很害怕,担心自己会再返回皮诺克。但是同时我也很清楚自己这样的情况若是置之不理,终究会让身边的人受伤。”
“既然你意识到了自己出现的问题,就应该回到皮诺克复查甚至治疗!”我试图通过在言谈中提到皮诺克,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我不会回去,也回不去!”他的反应有些激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从他的表情里我看到了沉重的悲伤。我想:是这个社会出了毛病把人逼疯了,还是人自己把自己逼疯了呢?
“这些幻觉刚出现的时候,我真的犹豫了很久,到底应不应该告诉我的监护员苏慧珍。”说完最后三个字,他冷冰冰地看了我一眼。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江瀚说这话的意思,也领会到接下来那些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显然他暂时还不愿意跟我谈关于皮诺克医院的事情。
“正当我最需要帮助,内心最挣扎的时候,罗琳像朋友一样走进了我的生活。可能你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还有人愿意当我朋友,虽然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甚至已经做好孤独终老的打算。但是罗琳却从不计较我的过去,只有她才会在我难受、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我一直当她是朋友。”话语再次被他的哽咽所打断,一直保持冷静、面无表情的他,终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在一旁看着他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此刻到底应做何感想,是江瀚杀了罗琳吗?他会杀掉如此信任自己的朋友吗?
有时,即使面对这种伤感画面,我也会变得无比冷酷,不知道是否因为现实已经磨平了我的心。
“但是你后来发现罗琳也已经死了。她的死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替他把话说完,引导他告诉我罗琳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
他没有看我一眼,只是说道:“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我跟罗琳在皮诺克就认识了,刚认识的时候,她以记者的身份来找我,但我并不想接受她的采访。我是个罪人,但事情过了这么久,我也不想让外面世界的人再对自己指手画脚,甚至去打扰我前妻家人的生活,当时的我只想用剩下的时间好好赎罪。”他还是避而不谈罗琳的死和他有何关联。
“那后面是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想法?”我已经改变角色,从心理医生的谈话方式跟他交流。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需要言语抒发,同时也需要一个有所回应的聆听者。
“是罗琳改变了我。她把外面世界的阳光带给了我,用热情温暖着我那颗麻木的心。”透过江瀚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对罗琳那种含蓄的感情。我很难相信自己在跟一个杀人犯谈话。
“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怎么搭理她,她也只是随便问了问医院的情况。后来她经常来,还开始带一些外面的照片,以及她去旅行所拍的景色,然后一个人在那里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知不觉间,我也开始被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辞所打动,甚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慢慢对她敞开自己的世界,与她分享自己内心里的一点一滴。”江瀚接着说。
“难道医院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咨询吗?”身为一个心理学家,我非常质疑如今医院所奉行的形式化的谈话治疗,还有那套自称有效的快速药疗法。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日新月异的科技已经揭示了大脑对心理的影响,也从很多方面成功地研制出对直接控制脑部区域的药物,但是我还是觉得传统的谈话式心理治疗更能真正地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毕竟我们所能认知的心理学还在起步阶段,在我国更是如此。
“这不一样,不一样。”江瀚哽咽道。
不知道是受了江瀚情绪的影响,还是感受到了现实的无奈,我开始静静地听他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江瀚出现幻觉幻听,神志不清,最终他下定决心联系苏慧珍,而苏慧珍在最后一次送药后就音讯全无。直到冬至日我们发现了罗琳的尸体,江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此消息后,匆忙地离开了家,这跟我的推断一样。
“为什么要选择逃跑呢?”我思考后问道。
“难道你认为除了逃跑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江瀚冷冷地说。
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像他这样连自己的精神状态都难以断定的人,警方毫无疑问会将他定罪;就算是自首,像他这样有前科的人,也会被宣判死刑。
“这几起案子发生的时候,也就是冬至日前一晚以及二十四号凌晨两点,你人在哪儿?”
“自从我出现精神混乱以来,我就很早睡觉了,可是……”江瀚显得有些犹豫。
“可是什么?”我接着问。
“可是,我经常想不起自己做过些什么,明明记得穿了睡衣,第二天却穿着外出的衣服躺在床上。”
“那有没有血迹?”我接着问。
“没有。”他说完便沉默了,像是在思考。仅仅从没有血迹这点还不足以断定他有没有杀人。
“如果真的是我精神失常杀人,我是不是要被枪决?”他突然问道。
“怎么说呢?我不是法官,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并转移到重度看守的精神病牢房。”这让我想起电影《禁闭岛》中的情节。
他沉思许久。车子继续飞驰在环城高速上。对于陈龙案发时的时间段,江瀚并没有不在场证据,但也不能确定他当时身在何方。过大的精神压力以及难以承受的惊恐让他短暂地失去了记忆。眼下所有证据都指向他,尽管我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及部分所谓的证据,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凶手“正常”的人格基础上。这里的“正常”并非指平时所说的“正常”,杀人已经是极度缺乏同情心的变态心理行为,无所谓“正常”;而刚才所说的“正常”是指凶手的人格并无崩坏,也没有出现过因其复杂人格体系导致的杀人事件。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整个社会所争议的话题。到底我们应该遵循道德的底线还是遵循法律的规定呢?
江瀚这次的停顿时间比前几次都要长,或许他正在思考。而我仍旧被牢牢地绑在副驾驶上,唯一让我安心的是,他现在并不想要我的命,但是“他”也只能代表一个神志不清的精神病患者的其中某个人格罢了。
我尝试再跟江瀚说些什么,但是在这种连自己的安危都无法保障的状态下,我很难打破这沉重的寂静。尽管刚才的谈话都还算顺利,不过从江瀚现在的脸色来看,情况比我想的糟糕多了,或许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是死罪难逃了。因为他一手策划了这次绑架,他对自己感到怀疑才会跟我进行这样的交流。
我刚开始思考事情的时候,该死的头痛让我难受极了。
“能不能开点窗,让我透透气?”我打破僵局,对他说。
但是他没有理睬我,似乎还沉浸在思考中。
“你应该知道这是罗琳的车子吧?”江瀚终于说话了。
我看了看方向盘上的车标,说道:“刚知道。可能是你下手太重,以至于我已经忘了很多事情。”我略带调侃,以缓和这凝重的气氛。
“抱歉让你受苦了,现在我要你打电话给你的头儿,告诉他你没事。”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