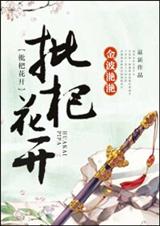陌上花正开-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修彦愣愣地看着离开地那抹蓝色背影,他好象就是当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帮他解围的那个人吧!难怪就觉得怎么越看他越眼熟,原来他就是钱茗啊!跟陶砜一个年级的体育全能生。
楚易又一次回到他住的那栋楼下,抬头确认似地看了看五楼,没有灯光,“还是不在家……我怎么可能知道他跑哪里去了……你要去同学家帮别人补课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我又不管你,至少让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家啊!现在怎样,人到现在还没回家……当然要继续找,混蛋……”捏着手机他恨不得能往墙壁上砸,想到楼下屋子去看看,没想到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隔了一个小时后又去看了,还是没人,打电话问陶砜怎么回事,没想到对方居然跟他说在同学家帮别人补课呢!他在外面可屋子里本应该在的人却不见了,站在楼梯上又喂了一个小时的蚊子却始终没等到要等的人,这下子两个人彻底开始担心了,洗过澡的身体因为到处找人而弄的满身是臭汗,期间他跑回来几次打了好几次家里的座机,可就是该死的没人,远处跑回来的人满脸的焦急,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已经快十点半了,白修彦没有理由会玩得这么晚还不回家。
“姨妈说他没有回去,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什么时候不见的?”陶砜气喘吁吁地靠着树。
“我怎么知道,你不在家也不跟我打声招呼,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去的,”楚易一向淡定的脸上挂着愤怒和着急,拎起陶砜的衣领一把将他拽到自己面前,“陶砜我今天告诉你,如果他出了什么事纵使你是他哥,我也一样不会饶过你。”
“你觉得现在是讨论这种事的时候吗?”是他粗心了,白修彦被他憋在家这么久肯定是闷坏了,可他住的这个小区的治安一直都不太好,老有混混勒索学生的钱财,甚至有时候还会抢劫妇女的首饰,“我们必须分头去找,每半小时打一次家里的电话。”
将手里的人往后一推,楚易似乎有些泄气,“白修彦,你最好给我没事,真是天生来要我命的家伙,臭小子真是……”他从来没有为了任何人这样担惊受怕过,白修彦是第一个让他有生以来会这样担心的人,也是从小到大以来唯一能牵动他全身神经的人。
楚易的父母都是教授,很早以前就久居国外,在这里他算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类。也许正因为父母都是教授的关系,他遗传到了优良的基因,所以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聪明,光小学就连跳三级,初中进去直接上二年级的课程,三年级的时候别人都在紧张地复习,惟独他还悠闲地用半年时间开始学高中的课业了,中学的时候经过学校各方面的测试校长破例让他一个高一新生坐在了高二的班级里,谁曾料想高二快结束的时候他又向校方提出要参加当年的高考,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校长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后又向教育局申请,那一考真是差点没把人吓死,大学四年他只念了一年半,自己读了半年时间的书就准备考研,当时带他的教授是他父母的学生,那老头看了他的论文后就问他想不想去医院做临床实践一下,所以在念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医生,被病人称为‘未成年医生’,那年正好十五岁,用了三年的业余时间念到博士后,期间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手术,可谓是身经百战,经验老道了,十八岁拿到身份证的那年不知道S医大的校长怎么联系上了他在国外的父母,竟然让两位老人家来当说客把他弄进了医大当教授,吃了两年的粉笔灰他算是呆的够够的了,教授的工作枯燥又了无生趣,周围总围绕着一个个戴着厚厚眼镜片的呆板学生,还好在他当教授期间经常去医院逛,有时候甚至帮别的医生值夜班,就因为那样,所以在有一年的夜晚,遇见了得了盲肠炎独自一人去医院的陶砜,他帮别人顶班给他做了手术,当时陶砜还满脸不信任的看着他,毕竟不认识他的人谁也不会知道这个年仅二十岁的医生已经是S大的医学教授,而且在不久前还在这间医院做了无数个手术,所以当术后还在康复期间的陶砜听到小护士称楚易‘未成年医生’的时候,正在吃药的人差点被药给卡的就此丧命。两人的相识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楚易住不惯S大的教师宿舍(其实是他觉得那些学生老去找他实在是很烦,还有时不时对他好的过分的年轻女教师)就出去找房子,那个时候陶砜脸上虽然还带着孩子特有的单纯和青涩,可心理却很早熟,他一个人住在现在五楼的套房里,当他说他家在楼上还有间空屋子的时候楚易二话不说就租了下来,房东就是当时还在上初二十四岁的陶砜,后来两人经过更深入的了解后楚易才知道房子是陶砜父亲的,而他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已经车祸去世了,他的母亲是做保险的,为了他和家庭的开销总在外面奔波,就在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母亲改嫁了,他并不反对那样的事情发生,改嫁后的母亲将父亲的房产划到陶砜的名下,每个月会在他的卡上存一笔零用钱,他的继父来过很多次,每次来都是希望陶砜能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但那都被他拒绝了,母亲改嫁了之后就应该有他们的新家庭,陶砜觉得他不应该去破坏,只要他们还能记得他就好,继父经过两年的劝说还是没办法让陶砜妥协,所以只能放弃了,但总会每两个月就去看看陶砜,去的时候也大包小包的总要把家里的冰箱里都塞满才会满意的离开,楚易觉得陶砜似乎并不会因为失去了亲生父亲而不幸福,现在的他活的也很不赖。和陶砜楼上楼下做了一年的邻居后楚易在陶砜升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见到了小陶砜一级利用暑假去补课的白修彦,当假期结束的时候他也决定了再做S医大一年的教授,得知了陶砜报考的高中后他毅然地辞去教授的头衔去现在的学校做了校医,白修彦中考的时候他和陶砜两个人疯了一样帮他补课,为的就是让白修彦能上那所高中。二十岁的时候遇见了十四岁的陶砜,二十一岁的时候遇见了十四岁的白修彦,今年他二十四岁,陶砜十八岁,白修彦十七岁。
看到害他找了半夜跑的快晕厥的人时楚易眼睛里有了血色,被别人扛着走过来的白修彦额头和鼻子都流着血,嘴唇已经破裂,血液将唇染的更艳丽,手臂上到处是瘀青和被殴打过的痕迹,白色的短袖衬衣上印着肮脏的脚印和血迹,原本扣地严谨的领口早就因为没有了扣子而大大敞开着,白皙瘦弱的胸口上也布满了被施行了暴力而留下来的痕迹,衬衣的下摆一部分垂在裤子外另一部分被凌乱地塞在裤腰里,原本扣紧的皮带松垮垮地半垂在腿边。
“修彦,怎么回事?”楚易跑过去一把将满身是伤的人抱住,紧紧地要把那人揉进自己的身体里,被用力搂住的人吃不住疼地哼哼了几声,“为什么会这样?出什么事了?”
白修彦被他又搂又抱的弄的很尴尬,何况他身上还有瘀伤,一碰就觉得特别疼。
“老师!你怎么在这里?”扶着白修彦的人有些吃惊,他从来不知道这个在学校不光学历让人惊讶到叹为观止,而且还以冷面又严厉出名的校医竟然也会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
楚易意味深长地看了眼钱茗,他是全校的体育全能生,每次学校跟外界有体育赛事都归他揽,而去诊疗室最勤快的当然也就是他。
“我来找他的,”手臂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受伤的人拉到了自己身边,“你,似乎不是住这一片的吧?”在学校做了两年多的校医除了看医学书有时候还能免费听一些有意思的事,其中就不乏他钱茗的风光大事了。
作者有话要说:
☆、第 8 章
学校里时不时的会有很多受了伤的学生去他那里包扎治疗,那种伤看一眼就能知道并非是在学校期间弄出来的,尽管如此他不会多问也不会质疑什么,有受伤的学生来他就治疗,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本校学生带着外校的学生去诊疗室包扎的情形,对于那些他也是闭口不问,久而久之那些学生就以为他不爱多管闲事,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难得的好校医,虽然总是用冷冰冰的态度帮他们处理伤口,但并不会对他们说教让他们觉得烦,所以他的冷面也就是这样得出来的。其实他心里都明白,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男孩子都这样,即使对他们训话也不会得到更好的效果,那只会让他们在心理上更反叛,何况他也只是个校医。跟那些受伤的学生接触的时间久了双方似乎都有了默契,有时候帮他们处理伤口的时候他们疼了还会骂骂咧咧的,有的就骂娘,有的就暴粗口,还有的人就讨论对方那些跟他们干架的人,至于钱茗,有些时候也会出现在他们嘴里,学校的体育全能生在校外也是出了名的能人,打架斗殴对他来说似乎也是家常便饭,在老师们口中也有听说钱茗是学校附近那一块地方道上的混混,只要他不惹是非基本上学校不会对他怎样,老师们也都对他挺客气的。
钱茗笑眯眯地看着眼前平常总是冷着脸帮他处理伤口的校医,顺带把楚易将白修彦搂进怀里的小动作也都一并收进眼底,“我家在学校附近,那是以前,现在我家已经搬到这附近了,老师也是住这边的吗?”
楚易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转身心疼地擦掉白修彦脸上的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白修彦疼地龇牙咧嘴地哼哼,钱茗看着楚易的背影眼神冷硬,“他遇到了这边的小混混,那些人大概是想抢劫。”
“是这样吗?”楚易双眼一刻不离地盯着白修彦,声音里有些颤抖,此时此刻已经顾不得追究钱茗的出现了。
垂着卷曲的睫毛白修彦留给楚易一个沉默的头顶,“陶砜也在到处找你,我先带你去医院处理这些伤,钱茗,谢谢你。”抱起瘦弱的白修彦快步离开了钱茗的视线。
站在路灯下的人勾起了诡异的笑,在他身后的阴影里又走出了三四个高矮不同的人影。
医院的很多护士都认识楚易,见他脸色铁青地抱着个年轻人进来直接将急诊室的门打开让他进去,随后动作迅速地将药物以及需要的工具一一送进去,值班的医生在门口探了个头,随后出来吩咐护士去取拍片室的钥匙,自己则坐在门口等着。
一把将没剩几颗纽扣的衬衣扯下,红紫色的瘀痕一块块遍布身体的前后,快速地止了额头和鼻子的血,将嘴唇上破裂的皮肤组织处理干净,修长冰凉的手指触碰上细腻的肌肤时白修彦打了个颤,他不知道这么热的天楚易的手怎么凉成这样,他也不会知道楚易体内的血液正随着他目光所到之处在一点点地寒结成冰。
修长的手指仔细地从肩膀开始摸索, 一寸寸不轻不重地捏着,甚至不放过两肋和腰侧,白修彦不明所以地看着抿紧了唇一言不发的楚易,停在他裤腰上的手指捏着那里的纽扣突然放开了,楚易闭了闭眼吐出一口气,修长的手指轻轻顺着裤腿捏着里面的脚,直到脚踝的地方才发觉不对,暗暗一用力白修彦疼地脸色苍白。
“没事,应该是扭到了,”拉过衣架上的一件白大褂盖在白修彦半裸的身体上,对着门外叫了声,值班的医生立马就进来了,“脚扭到了,帮我按住他,”医生有力的手臂将躺着的白修彦压制地根本无法动弹,“修彦,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