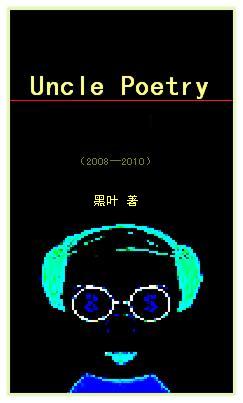secret garden-- rednight-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遥望已经改换过面貌的美容院招贴画,和它对面遥相呼应的大宾馆繁星般的窗口。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漫不经心地接起电话,话筒中传来的声音让我骤然跌入冰窟。
“哟,朱医生,你好呀。我是TAKUYA。现在我正好能看见你呀,值班呐?”
那是泰雅的声音,腔调有点职业性的近乎。我“嗯”了一声,既没肯定也没否定。他继续说着:“我在你对面的宾馆里,很近哦。好久没和你一起,正好今天有些朋友在这里,下班后过来一起玩玩?”
我脑子昏昏的,只有TAKUYA这个名字在里面无意识地旋转,为什么?为什么好不容易就快把他忘记,他却钻出来搅和?
他还在电话里说着,声音变得更加柔软更加妩媚,隔着手机壳似乎也能触到他丰满的嘴唇,夜空中似乎传来若隐若无的香气:“你没空啊?我这几个朋友很特别,很有意思的。反正你也睡不着吧?你和他们聊聊?告诉他们我们以前…嗯…说说我们在一起的事吧。喂,这电话清楚吗?向我的朋友们挥挥手吧。他们看得见的,就在你对面的宾馆里,不远呢。”
混蛋!他这是干什么?喝醉了?吸过毒脑子不清醒了?我的身体僵直着。
他的声音近乎乞求,是真正的而非职业性的乞求:“还记得我告诉过你的,总有一个光明的地方,能让我们宁静地生活在一起吧?那个地方,就要到了。相信我,来吧,你就…”
“你打错电话了!”我嘎着声挂掉,顺手关闭手机电源。熟悉的尖锐的刺痛再次在胸中翻搅,使我五脏俱裂。自称从来没有说过爱我的人,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提起这种不着边际的话?也许过一阵子又会反过来说“你理解错了,我从来没有过那个意思,变态。”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给我预留宁静地生活的空隙?为什么老是要让痛苦、烦恼追逐到我逃避前的最后一夜?
可是他分明是在哀求我,那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可以轻易脱身离开病房去对面宾馆那不知名的房间里,揭穿他到底在搞什么鬼。但是我最终放弃这个念头,因为我太害怕再次目睹恶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他没有权力强迫我看让我恶心的东西,不是吗?我没有义务,而且更多的是没有能力拯救他堕落的灵魂和肉体,假如有什么已经让他如此神智不清。
压抑厚重又燥热得象毯子一样的空气里,几乎无法呼吸。沉沉的黑暗,浓得化不开,使人渴望暴风雨的来临,能撕裂出透进新鲜空气的口子,又使人怀疑阳光是否能一如既往穿透它,再次给世界带来光明。尽管病房里很太平,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接近凌晨才勉强浅睡。6点多于纪理起来去给病人换药。我在值班床上呆坐着,闷闷地看着窗外,一点也没有太阳即将露脸的样子,空气已经和揭开锅盖一样蒸腾起来。今天又会是个热死人的阴天。这时,护士台的电话铃响了,我听见露露走去接电话,然后…
“急诊病人,你们谁去?朱医生,你吗?于医生忙着。”
我点点头,穿上鞋子,不太情愿地走向急诊室,去尽我最后的义务。
关于那个早晨,我唯一明确而清晰的记忆就是:泰雅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还活着。
我不记得看到揭开的被单下血肉模糊的身体后自己对送他来的警察和急诊室的护士大吼大叫了些什么,也不记得麻醉科值班还来不及赶到前自己怎样神奇地给他插上了气管插管;我不记得监护仪上血压的数值如何可恶地坚持在“0/0”,也不记得心率是如何160…100…80…而后很快地45…30…直到报警声响彻整个抢救室;我不记得自己怎样操起手术刀划开他的肋间隙把手探进胸腔里,也不记得握着他还温暖的心脏挤压、放开、再挤压、再放开,一共多少次;我不记得他的血和输进去的还来不及加温的库存血如何混合在一起继续无望地从破裂的肺叶涌出,也不记得到底是他自己的血先变冷还是混合了太多冰冻的库存血所以变冷抑或是抢救室的空调吹得太冷所以流出的血浸透我的白大衣,贴在身上变得象冰块一样沉重;我不记得外科总值班命令我不要再无谓地折腾尸体时到底说了什么,也不记得警察们和院总值班怎样合力把我拖出抢救室,怎样剥去我的白大衣,护士怎样在我上臂打了一针…
在郭警官和孔警官来询问我以前,我已经在留观室躺了一个白天。师傅拒绝了院总值班叫救护车把我送到精神卫生中心急诊的建议,如果有在那里就诊的病史,以后将永远记录在我的档案上,跟着我一辈子。
我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丁非的脸。他咧嘴笑了:“你这臭小子!把我们吓坏了。来!看我的手指,这里有几个?”他伸手在我眼前晃动。我无神的眼睛失去焦距地注视着天花板。镇静剂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永远不会消失的,是那种失去的空虚感。“喂!你配合一点呀!”见我没有反应,丁非拿手电筒照我的瞳孔。我闭上眼,偏过头去。他笑道:“哈哈!装死!你倒是快点醒过来呀!我都奉命在这里陪了你一天了!你家里还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呢。如果你现在乖乖地起床,还可以没事人一样回去吃妈妈烧的晚饭。”
“我什么也不想吃。”嘶哑的声音说,几乎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声音。慢慢地,意识和习惯思维开始回到我空白的头脑中。这时,我很奇怪丁非为什么不在意我是个同性恋,这实在是太明显的事实。然而他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暧昧的讥笑。
目睹罕见的犯罪致死使他有点激动,他告诉我法医把尸体带走了,他听到初步验尸的结果,说看泰雅手腕和脚踝上的淤痕说明杀人犯最后决定怎样处置他以前将他捆绑过挺长一段时间,可能有几个小时,一直到他们动手。除了头部、胸部重物反复打击造成的多处骨折以外,左上腹、左胸的刀伤本身就是致命伤。听说他被装进大号手提箱,假装成行李带下宾馆楼。在杀手把箱子装上车的时候,因为血迹从箱子边缘渗出而被服务员发觉,报了警。警车追了半个多小时才截住罪犯的车,又辗转把他送到我们医院。
他继续说:“严威说你傻,就算那个病人是警方的重要证人,伤到那个地步又被耽搁了那么久没有可能抢救成功的,死了就死了,还能怎么样?不会算你医疗事故的,连糗事都算不上。你走了也没人会老牵着你的头皮,说起你某年某月某日抢救一个该活的病人却送他上了西天。激动成那样干什么呢?”
“他是这么说的?”
“对啊。”
“他凭什么这么说?”
“喂!你说什么怪话呀!你是不是热昏啦?还是看到警察吓昏啦?来!空调对着你吹。”
他起身去调节老式窗式空调的开关。
我淡淡地笑了一下。没想到严威是这么细心的一个人,给我保留了继续过表面普通而宁静的生活的机会。可是,我的内心能平静吗?
“谢谢。”
“唔?”丁非扬起眉毛,似乎很不习惯我对他说这种话,“嗨!我看你脑子确实不对劲。回医学院好好修养一阵子,我看你值班值太多了。”
“我起来了。”我撑着床沿坐起来,“好渴,有水吗?”
“有!足够淹死你。都是小护士送来的,没想到你那么有‘人气’。”他扬扬手里的罐子,“可乐?还是乌龙茶?哦!警察来了!”
院总值班、师傅和郭警官、孔警官鱼贯进入。师傅点点头,丁非会意地离开。
院总值班清了清嗓子,发表了一通“朱夜同志积极抢救重危病人配合警方调查重大案件”的官样文章,接着郭警官也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与其说是为了讲给我听,不如说是出于礼貌对院总值班的回应。师傅一言不发。当院总值班和师傅走后,孔警官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切入正题:“昨天夜里为什么不报案?”
“我?报案?”我已经完全清醒,但空虚和麻木的感觉还没有过去。突然我想起了那个电话,熟悉的刺痛再次从我本以为成为鸟不生蛋的荒漠的心底深处扎出来。
“我们已经掌握了事实,你要配合我们工作,否则对你没好处。”孔警官继续说,“12:00打给你的手机都说了些什么?”
我张着嘴,半天没发出声音来。
孔警官有些失去耐心:“抵赖是没有用的,现在有的是先进的技术手段,就算你不说晚两天我们也能查出来,到时候…”
“小朱,”郭警官长者的口吻打断了孔警官气势汹汹的威胁,“你累了,没关系,好好说,把问题说清楚,对我们有利,对你自己也有利。你想想看,那时你在干什么?”
“我…”我在干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要完全解释清楚也不容易,“太热了睡不着,趴在窗台上闲看。”
“后来呢?”
“后来?手机响了。”
“哪个电话打来的?”
“没注意。”说到这里,我摸出手机,找出最后一个打进来的电话,那果然是对面宾馆的电话,还有1012的分机,老天!郭警官和孔警官传阅我的手机。
“于医生和我一起值班,他已经睡了,怕手机声吵了他,所以一响就接了,没注意对方的号码。”我说的是真话。
“对方是什么人?一共几个?”
“当时我也弄不清到底是谁,以为别人打错了电话。我没听到别的人的说话声,但是打电话的人说旁边还有别人。”我说的一半是真话。
“对方说了什么?”
“说了…”我豁出去了,反正泰雅已经死了,没有人再能伤害他本人,“说要找我一起去玩什么的。”
他们反复追问泰雅到底说了些什么,要我写下每一个能回忆起来的字眼,相互之间不时用眼光交流着。
“他就这么死了,”我说,“你们一点也不在乎吗?”
“如果知道他身份暴露,我们会提前行动的。”孔警官有点懊丧地说,话出口后又觉得自己多嘴,没敢看郭警官,径自低下头。
“我们早就告诉过你,如果有什么异常发现要向我们报告。”郭警官说。
“是的,你说过的。”我木然重复着郭警官的话。他们放过我太久,以至于我几乎忘记他们的特殊存在。突然我打了一个寒颤,一些混沌的东西在我脑海里渐渐凝集,结合,变得开始有些轮廓:“他的身份?你们的行动?那么他是你们的卧底?”两个警察看着我,脸上平板如没有生气的戈璧滩。我激动起来:“那么说是你们介绍他去那种地方?你们让他做卧底,却放手让别人杀死他?他到底作了什么孽了?你们为什么不放过他?”
我眼前浮现出泰雅疲惫苍白的脸,忧郁的眼神,无奈的凝视,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交汇的一部分快速得在我眼前闪过:短暂的幸福和平静,渐渐产生的裂隙,无形之中的压力。最后,我的意识集中在一句话上:如果知道他身份暴露,我们会提前行动。如果…如果我能撇开自己的怨怒好好思泰雅为什么说那些话,如果我能看一眼手机上来电显示的号码,如果我感到不那么对头的时候能够稍稍多花一点力气去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那时肯定是危急之中想找个无关的人证明他的身份,在对面宾馆10楼的房间窗口看到了正在闲望的我。当时哪怕我咬牙切齿地对那些人说:“哈!对!他就是这么个无情无义的男娼。”甚至只要在窗口做个什么动作让他们看到泰雅果真是在给我打电话而不是纯粹拖延时间,也许他就不会死。
都是因为我!就是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