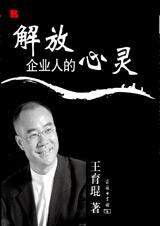两个人的车站-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染咕哝了一句“去你的吧”,就不再理他了。
整地也是件枯燥的事,不过对白染来说不成问题。他似乎特别喜欢这种周而复始的一板一眼的工作,还有点乐在其中的意思。别人都是各自管一畦,余锡裕却跟他并排,一人一条沟,他太专心,也就没有留意,余锡裕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没话找话,他也是哼哼哈哈地答应著。
快到中午的时候,白染突然想起来:“今天中午咱们没带吃的过来。”
余锡裕说:“还等你想起来。不过,今天可是有优待的,因为咱们做了精英劳动力,所以呀,中午有人送饭给我们的。”
两个人的车站109
整地比不得收割,是项还要费工夫的工作,直花了两天,才把苗地整完。整完之後很仔细地灌了水。
前面的程序完成之後,天又阴了下来。
白染说:“下点雨比较好吧,出芽比较快一些。”
余锡裕说:“也不是这麽说。黄平乡并不缺水,灌田一点都不困难。可是如果下大雨的话,肥料都会被冲走,咱们之前整地的工夫都白费拉。”
眼看著天越来越阴,所幸最後只是洒了几场毛毛雨。落雨的时候正好两人可以缩在棚里歇一歇,等雨稍住就是播种了。
播种的时候领的工具竟然跟整地时是差不多的,只是推斗装著的草灰里混著油菜种子。做法要更费工些,拿个小铲,挖出一道小沟,把种子洒进去,再小心翼翼地用土盖好,做不到多大会,头就晕了,脖子也疼,就做一会儿歇一下。虽说这样,大家也是不敢松懈,误了出苗的最佳时期,对整个收成都有严重的影响。
播种的第一天结束,白染累得全身像散架一样,一回去就倒在床上。
余锡裕一看白染那样,非常无奈。他自己也是累的,但哪能就这样放著白染不管。靠著床歇了一会儿,看白染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忍心叫他,随便煮了一点面,端到床边,说:“小白,快起来吃点东西再睡。”
连叫了好几声,白染也没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说:“我太累了,吃不下去,你先吃吧。”
余锡裕说:“明天还是播种呢,你不好好吃东西,明天又要怎麽办?”
白染再不回答,也不动。
余锡裕只能把他硬抱起来,靠在自己肩上,端过饭盒来,把筷子硬塞在他手里,对著他的耳朵大声说:“大少爷,我伺侯你,你就张张嘴还不行吗?”
白染被他吵得受不了,睁开眼睛一大饭盒面条正放在鼻子底下,本来不想吃,可一股葱花的香味直冲鼻子,肚子一下子就“咕咕”作响了。接过面条,稀里哗啦几口就吃了个一干二净。
白染还没来得及下床,饭盒就被余锡裕抢了过去,说:“得了,饭盒我来洗。”
白染说:“那怎麽好意思。”
余锡裕说:“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了一块儿洗。”一边从白染的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给他擦了擦嘴,一边说,“你累了就快躺下睡吧,我吃完面也睡了。”
吃完了面也并没有好受多少,肚子里暖哄哄的,可脖子碰到枕头还是生疼生疼的。白染抓住余锡裕的衣服下摆,说:“我还没洗脚呢,昨天就没洗。”
余锡裕说:“那个简单,我再辛苦一下,待会烧了热水给你擦身。”
余锡裕当然是开玩笑的,白染睡梦里面也知道行不通,脑袋直摇晃,说:“不用不用,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洗脚也没关系的。”
余锡裕不再逗他,呼呼地吃完了面条,把灯一吹,眼皮子重得快要塌下来,躺到床上,也是一动也不能动了。
两个人的车站110
第二天、第三天,继续播种,间隙里就培水。天一直阴著,所以没有日晒雨淋的麻烦,不过持续不断的劳作,让白染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才发现,余锡裕到了必须努力的时候也并不偷懒,而且体力上明显比自己好很多。
余锡裕也不再劝白染别拼命,总之都是能做多少算多少了。
播种完成之後没有歇息的时间,紧接著就是去大田里去帮忙整地。就跟收割时一样,漫山遍野地走。好在大田里的活儿就没有苗地里那麽精细。大多数地方已经有牛犁过了,现在就是培一培水肥。白染一开始不相信可以做得这麽粗糙,留心看了一下别人培过的大田才放心下来,於是也稍微缓过了一口气。
去大田里两天之後,白染突然牵肠挂肚的,揪著余锡裕说:“我们去苗地里看看吧。”
余锡裕耸耸肩,说:“行啊。”
苗地里眼下空空的,只有赵保贵一个人悠悠闲闲地坐在田埂上守著。看到两个人过来,说:“怎麽过来了?今天我这儿可用不著你们了。”
余锡裕说:“你就说便宜话吧。现在整个乡里最闲的就是你。”一边指指白染,说,“他说没看到过油菜苗,所以一定要过来瞧个新鲜。”
赵保贵对白染笑一下,说:“这也要看一下?那就随便看吧,别一跟头摔到田里就行。”
白染非常吃惊的是,只过了两天,地里就冒出了密密麻麻的细芽,嫩绿的茎几乎只有头发丝那麽粗,顶上两片小叶还没有绿豆大。白染说:“这些苗怎麽出得这麽快?这麽细?”
赵保贵说:“你想想油菜籽有多小,刚冒出来的芽当然细拉,长几天就粗了嘛。”
白染说:“那怪不得得专人守著了。”说著就想起一个问题,抓著余锡裕说:“既然出了苗了,就得移栽了吧?大田里的地还没整完呢。”
赵保贵“嗤”的一声笑出来,说:“小余,你跟他解释吧。”
余锡裕说:“现在还不能移栽呢,刚出的苗碰都不能碰,更不用提移栽了。”
白染说:“那得什麽时候。”
余锡裕说:“就数叶子,长到八九片叶子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
白染说:“那还不是一样的问题吗?长到八九片叶子大田还没整完呢。”
余锡裕说:“长出八九片叶子得过一个多月呢。你说大田整完了没有?”
白染“呼”地出了一口气,说:“原来是这样,也不早说。那我们就不用那麽著急了。”
余锡裕笑说:“本来就没人说要著急呀。”
心情一放松下来,白染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手里的锄头也轻巧起来。一天下来,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痛了。
这天回去得比较早,天还没有完全黑。余锡裕就没急著煮饭,开始整理外面的煤炭柴草,说是因为怕近来下雨弄湿了,得垫高了放著还要盖点油布什麽的。他一边弄一边说:“小白,我算了一下日子,你这是有多久没洗澡了呀?”
两个人的车站111
白染自己早就在暗暗苦恼这个问题,可余锡裕一提起来,必须嘴硬,说:“没多久啊,有什麽不对的?”
余锡裕说:“我就问问。明天下午不用去上工。”
白染说:“为什麽?”
余锡裕说:“乡里的一辆拖拉机坏了,赵保贵要我明天下午一块去修。”
白染说:“那别人都还是要上工吧?”
余锡裕说:“我都不去,你也可以偷偷懒。”
白染说:“这什麽逻辑呀?”
余锡裕说:“小白,我实说了你别生气呀。我觉得你有什麽事情都可以直接讲出来,咱们俩谁跟谁呀。”
白染心虚了,但嘴硬还是必须的,说:“我本来就是个有话直说的人。”
余锡裕说:“你还当我没看出来吗?你来了之後都没洗过澡,就是因为我在、你不好意思吧?这是多大点儿事啊?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白染心想,这是什麽道理?我要是不好意思,又哪里说得出口呢?但关键还是在於,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麽会不好意思,所以才加倍地不好意思。
余锡裕行若无事,白染却并没有觉得更自然一些,晚上仍是别别扭扭地睡了。第二天中午收工回来,正吃著饭,赵保贵就来了。
余锡裕跟白染一人端著一个饭盒子,里面照旧米饭洋芋什麽的。赵保贵也不客气,笑嘻嘻地自己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说:“你们俩洞房之後我还没来关心过呢。来看看你们吃得怎麽样。”
白染脸上有些挂不住,余锡裕自然要掩护他一下,骂:“滚你个远远的,吃什麽也没你的份儿。”
赵保贵也不生气,说:“你们吃你们吃,别介意我啊,反正这年头哪家的夥食都是一个样。”说著拿出个小烟斗,像个老头子一样吸起烟来。
余锡裕跟他扯了几句农机之类的话题,吃完饭就打算出去。赵保贵也没有叫白染一起去的意思,摆了摆手就走了。
余锡裕头天讲的话又在白染脑子里浮了出来,有种强烈讽刺的效果,尽管这样,白染还是毫不耽搁地开始烧水了,因为不知道余锡裕什麽时候会回来。一边烧水,一边拿出澡盒脸盆肥皂、找齐换洗衣服。
满满的一大壶烧好了还觉得不够,倒在脸盆里,又另烧了一壶。先从头开始洗。
说实话,白染从小到大还没这麽脏过,脑袋看上去也许没什麽异样,可感觉上却好像积了多年的垢一样,打了肥皂冲完觉得没舒服,又重来了一遍更彻底的。这样洗了两遍第二壶水也烧开了。哗啦哗啦地倒进大木盆,脱掉了衣服,跨进盆里。这一洗果然不是开玩笑的,总是嫌弃余锡裕脏,其实真正脏的是自己。细看自己的身体又瘦又干,也没什麽可看的,真不知道自己这几天在别扭个什麽劲。也许真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是一个人长大的,没给别的小孩一起玩过,夏天邻居小孩吵著下江里游泳,父母总是说江里危险,自己也没什麽热情,所以现在跟余锡裕同住,虽然同是男孩子,也还是不自在。
两个人的车站112
余锡裕赶在天黑之前回来,白染已经把衣服都洗完,东西也全都收拾好了。白染想著不该在这上面总闹别扭,可从此余锡裕总是有意无意地找机会出去转悠一下,给他留出一些单独的时间。慢慢地,白染又忍不住暗暗嘀咕,余锡裕之前怎麽久都不这样做,不过也说不定是在观察自己到底会不会不好意思到坚持不洗澡的程度吧。相应地,余锡裕自己晚上洗澡的时候,也会尽量找个角落一点的让油灯照不到的地方。这样一来,两个人同吃同住的生活就完全找不到一点问题了,只要白染有某种期望,余锡裕都会尽量配合,之前打扫卫生是,现在洗澡洗衣是,以及各种生活琐事都是如此。即便白染从来没有吃过与合不来的人同住产生的苦头,也觉得与余锡裕同住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以至於时常会想,之前搬过来真是明智之举。
中秋之後天气逐渐转冷,余锡裕也不再是日日穿件衬衫了事,而是不得不把秋衣毛衣一件件往身上招呼。被子早被白染订成了厚的,床单下面也多加了一层棉絮。余锡裕说天冷些反而有利於油菜苗生长,白染却有另一层心思,自从天冷了,尴尬状况也少了,盖著厚厚的被子,跟余锡裕似乎也隔开了,睡觉总是很安稳。
一个月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平时的劳作有规律但又不特别紧张,生活上又安逸没有压力,很快就过去了。白染觉得这真应该算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等到有一天余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