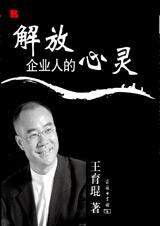两个人的车站-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白染说:“是啊,跟他挺谈得来的。”
村长说:“那你别管二狗讲的,他就喜欢瞎说。”
白染说:“本来麽,我差不多都忘了。”
村长说:“那你现在好好听我说,我也算是你的长辈吧,肯定不会害你对不对?别跟小余走得那麽近。”
白染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看著村长。
村长说:“二狗是在乱说的,小余嘛其实没什麽不好。问题的关键不在那里。我一直都挺看重他的,又聪明又能干。但是呢,党组织把他安排过来,我就说了,以後不许再派别的男知识青年过来,所以麽今年就派来七个女孩子,哪知道,最後人过来一看,怎麽还是夹带了一个男孩子呢。”
两个人的车站72
白染觉得自己的表情肯定很僵,想笑一下都挤不出来,假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带著大量免费学习班材料突然回到人间亲自送来黄平乡,他也不会有这麽错愕。白染想说话,可自己突然变得像条傻乎乎的胖头鱼,光会动嘴不会发声。
村长说:“你们一群知识青年,我把你们安排在村子上头,跟我住得这麽近,就是想让你和小余保持一点距离,免得搞坏了名声。”
白染模模糊糊地想起,当时二狗说的话虽然没头没脑,其实跟村长说的是一个意思。“搞坏了名声”到底是什麽意思呢?来了这些天,自己没有看到过小余的任何一点不道德的地方,也从来没听过别人谈起他任何一点实际的罪状,相反,大家背後的评价,跟自己的感觉也差不多,能干拉有才华拉。要说“搞坏了名声”,自己跟七个女孩子住一屋不是更坏名声?白染说:“名声什麽的,我不讲究。”
村长说:“真是孩子话。人活一世,谁能说是只为自己活?总得牵扯到别人。不说别的,就说我,组织上把你们交给了我,虽说跟我当初交待的不一样,也还是我的责任,要是有什麽事,不说别的,我心里就过不去。”
白染说:“我觉得小余是个很好的人,如果他愿意跟我打交道,我是很高兴的。我很信任他,也很喜欢他。”
很难说此刻白染对余锡裕的感情究竟有几分,也许是自然而然真情流露,也许是无心地把余锡裕当成了好朋友,总之他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使村长一听就愁闷不已。村长想管想骂,但这毕竟不是自己的儿子,想把两个人强行隔开,可两个半大小夥子有手有脚的,他想拦也拦不住。
村长琢磨了半天,摇摇头说:“我想你应该还是一时糊涂,年轻人嘛,总归还是会放纵一下,等到大了,都还是娶老婆生孩子过日子。身边的人,除了亲爹亲妈,最可信的还是老婆孩子。别要死要活地整那些没用的,也别往弯路上走。我也不能强迫你什麽,只要你有空闲的时候好好想想我的话。”
村长不说话了,低著头专心致志地磕烟斗。白染也没什麽要辩解的,就站起来自己回去了。
整晚村长的话都在脑子里回旋,似乎明白又不知所云,心里变得异常沈重,睡梦里也似乎充满了挣扎。
第二天早上起来,天有些阴,走到屋外的时候,有一股清凉的水气直扑胸臆,昨晚的事情似乎也被冲淡了。白染很快吃完早饭,不顾旁人的眼光,出去找余锡裕了。
走到稻草垛,余锡裕正蹲在外面喂上次那条杂毛狗吃什麽东西,抬头一笑说:“来拉?吃了早饭没?”
白染笑起来,说:“你该不会把我跟它一块儿喂吧?”
余锡裕说:“怎麽会?给它吃的,都是吃剩下的隔夜的,给你的,都是好的,连我都舍不得吃的。”
两个人的车站73
白染明知道这是哄自己玩的话,听到耳朵里还是很高兴,说:“少肉麻了。就好像我贪图你的好东西似的。”
余锡裕说:“哪儿能呢?从来都是我心甘情愿的,用不著你来图谋。”
村长昨天的那些话对白染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没事偏要跑来找余锡裕也的确很奇怪,可现在见了面,白染觉得果然很愉快。白染想,人与人本来就应该能有简单自然的关系,没有利害,没有算计,只因为互相谈得来,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同时,这种关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否则怎麽自己过去的近二十年生活里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人呢。
白染把两个人相处时的和谐舒服归因於奇妙的缘份,於是坚定了要跟余锡裕当朋友的想法。可这时候的他自然不能明白,他与余锡裕固然有天性相投的地方,但如果没有余锡裕挖空心思的讨好,又哪来这麽愉悦的相处?
不过归根结底,过程已经不重要了,结果是白染越来越跟余锡裕贴近了。
两个人看了一会儿杂毛狗吃东西,在稻草垛外散了一会儿步,回到小棚子里。余锡裕继续刻板子,白染继续看书。这一整天过完了,余锡裕的板子才算差不多刻完,说:“晚上我再整理一下,明天早上开始就可以印了。到时候就需要你的帮忙了。”
白染回去歇了一夜再来,余锡裕果然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白染一看原来跟油印很不一样。
棚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被挪开留出了一块空地,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的破门板,支起了一个临时的台面。台上放著朱红的颜料,和一个小包裹一样的东西。白染掂了掂,“包裹”里面用沙土和糠壳塞得很实,很沈但又相当软和。油印的时候,把纸放在油印机的最下面,盖上绷好的刻写过的蜡纸,用辊子沾油墨辊过去,油墨浸透刻在蜡纸上的笔划,印到纸上,就算成功。而拓印则是把刻板放在最底下,刷上一层颜料,覆上纸,用“包裹”拍一遍,颜料就沿著板上的图案印到纸上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都不简单。
白染以为要印得好,必得多刷点颜料。余锡裕看了他拿刷子沾颜料的手势,就说:“慢著,这颜料可不能刷太多,得薄得匀,不然印得不清楚。”但要刷得又薄又匀谈何容易。
余锡裕很大方,解释了几句,就让白染自己试,果然不大好。余锡裕也不说什麽,就一边看著。印出来的不好的也不能浪费扔掉,还得订起来。白染有些不好意思,说:“印得这麽磕巴,能行吗?”
余锡裕说:“画上的人能看到鼻子眼睛就行,大家都不讲究。”
白染练了几回,慢慢地才好了一些,说:“怎麽这个就不用油墨,要用朱红的颜料呢?”
余锡裕说:“油墨印这个不灵的。颜色嘛,当然不能选黑的,除了黑色也就只有红色了,印革命精神的,当然要红彤彤的。”
两个人的车站74
白染做事非常认真,每个动作都一板一眼的,旁边印好的画渐渐堆积起来,他没有变得草率急躁,反而印得越来越好了。
余锡裕在一边看著,第无数次感叹,这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说:“你都印了好多了,手酸不酸,脖子累不累,要不要歇会儿。”
白染太过专注,几乎忘记身边还有一个余锡裕,突然听到他说话,吓了一跳,说:“好,那你来印一会儿,我去裁纸边儿。”
余锡裕说:“真的不急,你坐一边歇歇吧。”
白染乖乖答应:“哦,好。”
转身一看,却找不到自己坐惯了的那张铁凳子了。余锡裕为了腾出地方放台面,把零碎日用物品胡乱堆到了一块儿,而那张小凳子不知道被堆到哪里去了。白染探著脑袋四处看看。余锡裕突然想起什麽,转过身想叫他别乱动,已经来不及了。白染的胳膊肘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铁架子,上面一个桶没有放稳,翻了下来。
原来那就是一桶新开的朱红颜料,刚才印画用的就是从这个桶里倒出来的。余锡裕倒了颜料,就把这个桶顺手一放,没有盖盖子,也没收到角落里。这时候颜料打翻,全泼到了白染身上。
白染一时间呆住了,看到颜料把自己下半身都染成了鲜红色,还滴滴答答地淌到了地上。余锡裕赶紧从炉子边找出一条大抹布在他身上一阵擦拭,可是越擦越是一塌糊涂。
余锡裕说:“你这身衣服不能穿了,我找一身给你换吧。”
白染这才醒悟,说:“你先别管我了,先擦擦地吧,免得把别的东西也染了。我回去换了衣服再说。”
余锡裕想说,你这麽一身怎麽回去,还没来得及说,白染已经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走出棚子,发现已经变天了,虽然还没下雨,风却凉飕飕的。白染这一身像杀了人一样,实在可怕,一路快步回去,幸好路上没遇上人。回去发现院里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大概都去小学校油印去了。白染冲进灶边用来洗澡的小布幔子里,急火火的把衣裤全都给脱了,这才想起,自己忘了把换洗衣服先拿出来。更糟糕的是,里面穿的内衬短裤也被颜料浸透了。白染迟疑了一会,终於不愿意把脏衣服穿回来,连短裤也一起脱下。其实院子里晾著的也有他的衣服裤子,只需要走几步就拿到了。他拿著毛巾就著早上洗脸剩下的水擦干净了身体,掀开布幔走了出去,正准备取衣服,就听到院子门口一声刺耳的尖叫。
白染抬头一看,齐芸竟然站在离他不到十步路的地方,眼睛直楞楞地盯著他身下。齐芸像傻了一样一动不动地盯著他看了一会儿,又捂著脸大声惊叫起来。
白染也是过了半分锺才反应过来,摘下晾衣绳上的衣服把自己遮住。可齐芸已经尖叫著转身跑了。白染心想,这有什麽大不了的呀,自己才是被她吓到了。
两个人的车站75
白染穿好衣服正往外走,就看到一群人从院门口涌了进来,带头的是李红英,齐芸被她拉著,哭得两眼都红通通的。李红英走上来一把重重地揪住白染的衣领,说:“你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做出这种事。”
村支书赶紧过来把李红英拉开,说:“先别激动,我们先问清楚再说。”
李红英也不含糊,说:“行,我们就听听他怎麽解释。”
村支书说:“小白,我们一起到办公室去,开个会,把事情解释清楚,对你也没坏处。”
一群人围著白染,就好像在逮捕犯人,白染无话可说,只能主动走出去,只差没像革命电影里面一样说“我自己会走”。
办公室就在小学校隔壁,不知道谁传播的消息,这时候门外围满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办公室里没有桌子,围了一圈椅子,大家团团围坐。村长和支书并排坐在上首,两边各是白染和齐芸。
支书说:“小白,你说吧,我们都仔细听著。”
白染对齐芸说:“你是女孩子,你先说吧,我做了什麽?”
齐芸说:“我看天要下雨了,回去收衣服,正好碰上你,你把衣服全脱光了。”
白染说:“你回想一下,当时是我先回去脱了衣服你再进来的,还是你回来了我才当著你的面脱衣服的?”
齐芸恼羞成怒,说:“讲这些有意义吗?谁先谁後有区别吗?”
白染说:“是支书的意见,我们面对面地把当时的情况讲清楚。你既然没别的话了,那我来说。其实刚才真没发生什麽。我跟小余在一块儿印版画,不小心撞翻了颜料桶,衣服全染了。我跑回来急著脱了脏衣服,才想起来忘了取干净衣服了。衣服就晾在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