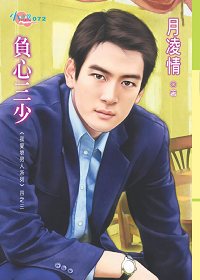不正当关系-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严俨头也不抬:“先把你的鼻涕擦干净。”
“……”魏老板很狼狈,但是再狼狈也不会忘记邀功,“这个……我替阿绿找了个住的地方。”
“嗯……”严俨继续垂着脸,觉得帐本上的数字比魏迟的脸更好看。
魏迟蹭啊蹭,从帐台外边,蹭到帐台里边,手指头轻轻点着严俨放在桌上的手:“阿绿他不用跟你一块儿住了。”
严俨不为所动地回答:“嗯,我知道。”
“那……么……”手指头在光滑白皙的手背上游移着,从修剪整齐的指甲尖一直到被衣袖覆盖的手腕,魏迟故意把话尾拖得很长很长,一半窃喜,一半掩饰,“你什么时候搬去我家?”
“魏迟。”严俨猛地抬头,目光犀利。
“嗯?”
“阿绿的话都是你教的吧?”那个被耗子训一句就吐不出半个字的小笨蛋,打死他也编不出那么多贴心话来。
“这个……”被戳穿的魏迟脸不红心不跳,提溜乱转的眼珠子眨呀眨,“今天不适合讨论这个。”
于是严俨也跟着笑了,咬着笔杆子,利落地甩开他再度搭上来的爪子:“我觉得,今天也不适合讨论搬家的问题。”
※※※※※※
严俨搬家的日子是在一个星期三。一周的正中间,绝大多数人上班,他刚好休息。
天天开门迎客的理发店没有“双休日”的说法,伙计们两个一组,按照墙壁上的月历轮流休息。有时做六休一,有时做四休二,也没有定数,全看店里的生意忙不忙。背井离乡的人们没有亲戚要走,也没有同学朋友要聚,什么时候休息都是一样,床上昏天黑地地躺一天就过去了。只不过事情一多,严俨就会犯迷糊。脑子里乱轰轰搅成一片,连他自己都算不清,今天到底该不该上班。
于是干脆披上衣服往店里跑一趟。大清早的,宽叔曲着胳膊往上抬卷帘门,看见严俨走过来,满脸都是惊讶:“你怎么来了?今天你不上班。”
严俨抓抓头,恍然大悟:“哦,这样啊。”
转身又往回走。
宽叔在他身后边笑边摇头:“伙计们的上工表还是你亲自排的呢,自己倒先记不清了。”
认识魏迟以后,严俨就再也没闹过这样的小笑话。
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的魏老板每月一早都会准时扑进店里,嘴里一边扯着不着边际的闲话,一边不露声色地站到被伙计们用彩笔划得面目全非的月历下,埋头对着手机一阵猛戳。
然后隔三差五地,他就会挨到严俨身边,附到他的耳朵边轻轻吹气:“严俨,下周一你休息,跟我逛街去吧,我请你吃饭。”
或是在和旁人的高谈阔论里,魏迟不经意地转过头,漫不经心地对严俨说上一句:“喂,严俨,星期五胖子约我打球,你去吗?”
严俨皱起眉头思索:“星期五我上班。”
“瞎说有什么好说的?你上周五上班,这个礼物五是休息。”嘴里“啧啧”嗤笑两声,他早就把头扭了回去,和别人说上两句,忽然又回头,“哎,严俨,说好了哦,星期五去打球。”
反正问也问不出什么,一双滴溜晶亮的眼睛眨巴两下,魏迟嘴里的话就翻得比女客们翻脸还快:“哦,是阿三告诉我的。”
“咦?昨天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哦哟,你什么时候休息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我怎么会清楚?”
他最无辜,他最委屈,他就差没把“白莲花”三个字刻上自己的脸。
严俨揪着他的衣领狠狠瞪他,他勾着嘴角,两手一摊,一脸的宽容大度外加一丝丝窃喜:“那就当是我刻意记住的好了,反正你开心就好。”
看,多无辜,多委屈,多么亭亭玉立的一朵白莲花。
不甘心地松开他的衣领,严俨胸闷到不行。
后来,严俨也习惯了。偶尔还会主动跑去找他:“喂,魏迟,我下周什么时候休息?”
不管手边在干什么,魏迟总能头也不抬地脱口而出:“星期二。”
于是严俨再施施然地跑回去跟客人讲:“张阿姨,我下周二不在店里,你找我们宽叔或者蹄膀吧。”
众人绝倒:“原来魏迟还有这个功能?”
严俨笑笑不说话。背后,一路跟过来的魏迟慢悠悠地推开门,又慢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干嘛?不行啊?”
青面獠牙,张牙舞爪,甚霸道,甚嚣张,甚有腔调。
严俨的行李很少,大大小小归置到一起,不过一床被褥,一个行李箱,外加一个装满梳子剪刀的工具箱。
袖管挽得老高的魏迟大失所望:“这么少?”
严俨先把被褥扔上他的助动车,然后毫不客气地把沉甸甸的行李箱拖到他脚下:“你以为有多少?”
连同严俨手里的工具箱一并夺过来,魏迟一边用绳子把东西捆上车,一边拖长了语调叹息:“早知道这样,昨天晚上就不请胖子喝酒了,害我还白白搭进去一条烟。”
“干什么?”严俨弯下腰抓住绳子的一端好方便他打结。
手指头绕着手指头转啊转,魏迟忙忙碌碌地说:“找他借辆搬场车。”
“借车干什么?”
魏迟的手停了,眼珠子黏在严俨身上到处转,一口白得可以去做牙膏广告的牙齐整整地咬着下嘴唇:“你真的要听?”
“你真的敢说?”知道他接下来没有好话,严俨挑起眉梢对上他笑得跟狐狸似的脸。
找车干什么?搬嫁妆呀。这种话能说吗?不能说吗?严俨会生气呢?还是会生气呢?还是生气呢?会生气吧……
魏迟识相了:“那我还是不说了。”
手脚利落地把行李捆扎牢靠,他站起身,重重在被压得直往下陷的助动车上拍了一把:“好了,走吧。”
“嗯。”严俨点点头,迈步往社区外走。魏迟的车放了行李,坐不下人。
魏迟就在他身后喊:“哎,等等我。”
严俨站住脚,疑惑地看他,魏迟还站在车边扶着车把,没有要走的意思。
“怎么了?”
“我找个人。”
身体后仰,魏迟伸长脖子,猛然对着六层高的居民楼一声大吼:“阿三,下来!”
不知谁家有刚出生的婴儿,“哇——”一声大哭。
不等严俨扑上去拽他,阿三一溜烟地从楼里蹿了出来:“魏哥,有事?”鞋带都还耷拉在地上。
宽叔找他都不见他这么勤快。魏迟店里的游戏机快赶上大麻了。
“嗯,车钥匙给你,把车开到我家楼下。”潇洒地把车钥匙抛给阿三,魏迟这才走到严俨身边,眯眼,咧嘴,手牵手,“好了,走吧,我们回家。”
社区里的绿化都枯黄了,玉兰树的叶子掉得一片不剩,光秃秃的树干刷着煞白的石灰,照不到太阳的阴暗角落里还留着昨日的残雪,湿嗒嗒地化成一滩水渍。
魏迟牵着严俨的手面不改色地从一群坐在楼下晒太阳的阿婆阿姨跟前走过。她们一个个从脚边五色缤纷的绒线团里抬起眼:“哟,这个不是对面社区六号楼阿婆家的小魏嘛?”
魏迟就停下来跟她们打招呼:“沈家妈妈又在做棉拖鞋啊?去年我外婆就讲你做的棉拖鞋又暖又好看,你送给她的那双她喜欢得不得了,一直穿到现在。”
“真的?那我再做一双,让她替换替换。老人家冬天最关键就是一双脚,脚暖和了全身就都暖了。”
魏迟忙不迭道谢。
女人们说笑着,目光在魏迟和严俨的身上跳过来跃过去,间或扫一扫两人牵在一起的手,像是看见了又像没看见。
严俨的手被攥得发疼,他撇过眼偷偷打量魏迟。魏迟却还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表情,游刃有余地和那些阿姨阿婆们聊着。
“小魏啊,女朋友肯定有了哦。年纪不小了,可以结婚了呀。早一点结婚,就早一点让你外婆抱重孙子,她不要太开心哦。”
“哈哈,现在没有三百万讨不到老婆的,谁肯把女儿嫁给我喝西北风?”
“哎,你没有女朋友,阿姨帮你介绍一个。我一个小姐妹的同事的女儿,长得不要太漂亮哦,照片拍出来跟明星一样,工作也很好的。”
魏迟敷衍着说:“再说,再说,人家看不上我的,对吧,严俨?”
好像是终于想起来严俨的存在似的,女人们终于把重点放到了严俨的身上:“这个是理发店里的严俨嘛,今天店里不做生意?”
严俨僵着笑脸说:“不是,今天我休息。”
“哦……”她们齐齐开口,七八双经老板娘的手纹过眼线的眼睛又一次飞快地从两只始终不曾松开的手上掠过,“和小魏一起出去玩啊?”
严俨支撑着嘴角:“嗯,不是……是……”
魏迟接过话:“不是,我来帮他搬家。”
“严俨搬家了?”
“嗯,搬到我家,和我一起住。”
她们都不说话了,丰富的面部表情一瞬间被集体定格了似的。
魏迟还是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模样,没心没肺地招呼了一声,大大咧咧地拉着严俨继续往前走。严俨走出一段又回过头去看,女人们凑在一起,看不清表情也听不清她们的谈话,只瞥见她们脚边的绒线团一下一下蹦个不停。
“不太好吧?”严俨说。
“嗯?”魏迟的心情却很好,胳膊用劲,把两人牵在一起的手甩得越来越高,仿佛要高过头顶。好像现在的小学生都不会干这么幼稚的事了。
“传出去不好听。”理发店是个是非八卦的集中地,从电视里的大明星到住隔壁的小二黑,谁挖谁的墙角了,谁和谁婚外恋了,谁家夫妻半夜打架了,只要不是出在自己身上的事,什么都可以拿过来随口编排,严俨听得太多。
“他们想说就让他们去说好了。”红灯灭,绿灯亮,魏迟走得很笃定,一步步牵着严俨跨过斑驳的横道线,“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没什么好偷偷摸摸的,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只不过双方都是男人而已,没有法律规定,同性情侣只能在旁人看不见的角落里拥抱接吻。无论投来的目光是何种非议或是鄙夷,那都是旁人的事。
我只遵从自己的感觉,我喜欢你,我要同你十指相扣掌心相贴,不管四周是悄然无人还是众目睽睽。一如天底下所有的普通情侣,肩并肩,相携走过每一个春秋冬夏,每一季雨雪风霜。
严俨止不住停下脚步,魏迟的眼神从未有此刻这般明亮而灼热。男人敢于担当一切的表情像极了游戏中那个始终冲锋于众人之前的英雄。
以至于到了之后之后的若干年后,回想起这个冬日午后的一切,严俨依然觉得手心发烫。
不过魏迟的那位至交死党——胖子却破坏了他的一切美丽遐想与感动:“切,魏迟这个人啊,不炫耀会死星人嘛。无论什么东西到了他手里,不拿出来显摆一下,他晚上睡不着觉的。”
※※※※※※
宽叔时常端着他那把从地摊上花十块钱淘来的紫砂壶,有板有眼地忽悠小学徒:“你们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却失败了吗?”
机灵的小学徒搬过小板凳围坐在他脚边,睁大双眼四十五度仰视:“宽叔,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站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到了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做人不能光凭一身本事。学本事谁不会?练呗,再笨的人练久了也总能出师。可是真正的聪明人却很少,这要靠悟性,得有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