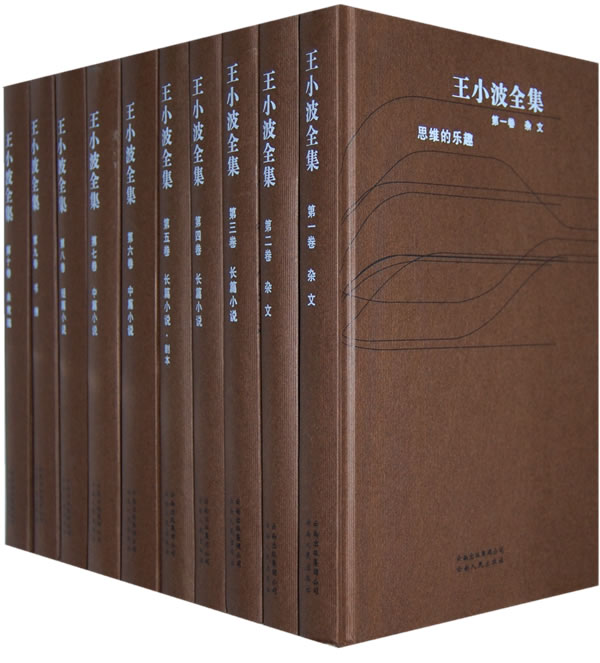正邪不两立-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电显示是个不认识的号码,已经响了两分钟了。他狐疑地看了下,按下接听键:“喂?”
电话那头半天没有声音,只隐约听到沉重的呼吸声。
这个……难道是传说中的情色搔扰电话?
谢鄂正要挂断,电话那头传来不太稳定的声音:“你胆子真不小,手机号码居然也不换。”
“……郑直?”
“哈,拨错号码了。”电话那头说完就挂了。
这人在搞什么?谢鄂莫名其妙放下电话,回浴室先把身上泡沫彻底冲干净,擦完身子出来已经是十分钟后。
这十分钟里,他想了想,还是放心不下。郑直说他打错电话。在他接电话前,铃响了那么久,不可能没发现打错号码。
说他烂好人也好,圣母也好,遇上别人有事,他总是无法袖手旁观。
单手擦着头发,另一手拿起手机拨了回去。那头响了很久都没人接,一直响到电话被自动切断。
谢鄂很有耐性地又拨了一遍。
拨到第三遍时,头发已经擦干燥,电话终于被接起,郑直语气不善地吼:“什么事,一直拨你不烦啊!”
“你现在在哪里?”谢鄂在找衬衫。
电话那头顿了顿,郑直嗤笑:“我在藏地。怎么样,要来么?Anne姐很掂记你。”
“藏地没那么安静。”谢鄂穿好裤子,在找袜子。
“在藏地的小包厢里,隔音良好。”电话那头的呼吸依然沉重:“……刚渡过美好的一刻哟。”
“都十分钟了还没回过气来,确实美好。”谢鄂耸耸肩,用肩颈夹着电话,拎起外套穿上:“你现在在哪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谢鄂怀疑地拿下手机看一看电话是不是已被切断。终于,电话那头悻悻地传来一个地址。
郑直说的地方是河滨公园东门的长栈桥旁。
谢鄂打车到河滨公园东门,兜转半天才找到郑直,他躺在栈桥旁的草地上,懒洋洋地向谢鄂挥手:“嗨,你还真敢来啊,勇士。”
声音听起来还好,没有电话里听到的严重。谢鄂一瞬间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受骗了。再走近几步,在栈桥头晕黄的路灯下打量,郑直眼角乌青,脸颊和嘴角都挂着血迹,长发乱糟糟地没扎起,外套看起来还算干净完整,里面的衬衫则被拉扯得变形,领口高一边低一边,染着些深色的痕迹,也不知是血迹还是泥土。
“你看起来象被人**过一样。”谢鄂蹲下身。
“难道不是看起来象刚**过别人?”郑直放声大笑,一笑扯到嘴角伤口,又停了下来:“我保证他们这辈子都忘不了我。”
“那你现在是**太多人所以肾亏站不起来?”郑直的手背可以看出他所言不闻,骨节处各种破皮、乌青和血迹。想想他在教室里放倒壮汉的利落,能打成这样,看来之前的围殴很盛大。
“月色这么漂亮,懒得动。”
谢鄂抬头看天上,一片浓云。
“刚被遮住了,之前还是有月亮的。”郑直笑眯眯回答。
谢鄂扶住郑直胳膊,郑直脸色不变,被握住的地方轻颤了颤。
谢鄂放开手:“你扶着我的肩站起来?”
“不用那么麻烦。”郑直单手撑地,不借外力自己站了起来。站起身体晃了晃,到底还是站稳。
然后他就站住不动了。
谢鄂苦笑地上前扶住他,小心地避开容易被人打到的胳膊外侧,搀在他腋下,将他带出公园。
准备打车时,谢鄂问他:“要把你送到哪去?”
郑直摇了摇头。
谢鄂一想也是,他现在要还有其他去处,也不会打电话给自己。
“那就去我家吧。”谢鄂说:“我一个人住。”
————————
谢鄂住的地方不是什么高级公寓,地段不好,房间也不大。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装修时充分利用了镜面交叠和层次扩充,看起来还不算狭隘。不过一个高校生一个人租公寓住,到底也挺奇怪的。
郑直进来后就一直打量房间,作为了一个单身男孩住的地方,未免太过干净,几乎没什么杂物,书柜茶几餐桌样样摆得井井有条,只有扔在沙发上的微湿毛巾显示主人出门前的匆忙。
谢鄂找出药箱要给郑直涂药,可惜在明亮的光线下他发现郑直身上泥土尘埃什么要比他受的伤多——伤不重还走不动,谢鄂叹了口气,先收起药箱,打电话叫外卖顺便问下店里有什么甜食。
郑直大爷状地坐在沙发上听谢鄂打电话,听着听着就有点困了,盖上眼皮。
谢鄂打完电话,看郑直一脸奄奄一息的神色,想想外卖至少也要十五分钟才能送来,就去厨房找找。他不喜欢吃甜食,家里也没什么甜的食品,只有谢姐煮菜时调味用的砂糖。
端起糖罐嗅嗅,没什么油烟味道。找出杯子,不太确定地用调羹倒了两勺,想想,又加了半勺,用热水冲开,略一搅拌,再加半杯冷水,端了出去。
“先喝杯糖水吧。”摇摇快昏睡的郑直,将杯子递给他。
郑直搭起眼皮扫了谢鄂一眼,再看看他手上端着的杯子,勉强抬高身体,将鼻子凑到杯子上嗅嗅,没什么奇怪的味道。他也懒得伸手,脑袋一探,直接就着谢鄂的手咕嘟咕嘟喝起来。
……这人也太懒了吧。谢鄂着着手边黑色的脑袋心下嘀咕着,手上很有耐性地将杯子配合郑直的速度慢慢抬起。这种喝水的样子,简直象只小猫,让人忍不住想为他顺毛。
当然,有过之前惨痛教训的谢鄂再也不会把眼前这只收起爪子的老虎当成猫猫狗狗看待。收起爪子的老虎还是老虎,不小心会被抓伤的。
闲话时间:
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良心隐隐做痛地纠结要不要保留最后六百字放到下更去,喷。双更什么,压力果然很大啊,这样下去我根本攒不够可以出门旅游的字数》_《
昨晚码字码到邪恶同学一直追问正直同学在哪里时,突然觉得微妙地眼熟——跟隔壁档的阿苍同学再三追问老大有点异曲同工ORZ不过这段情节是上上周的松果(上周只难产了半章下周的松果T…T),所以只能说,大家都心有灵犀地认为事不过三是个限度,爆
设了下字体,希望不会太大。屏幕比较大,默认的字体看得我快成斗鸡眼了
不知这一章会不会有**
清静
正邪不两立 5…6
#天下无双剧场#
谢鄂打完电话,看郑直一脸奄奄一息的神色,想想外卖至少也要十五分钟才能送来,就去厨房找找。他不喜欢吃甜食,家里也没什么甜的食品,只有谢姐煮菜时调味用的砂糖。
端起糖罐嗅嗅,没什么油烟味道。找出杯子,不太确定地用调羹倒了两勺,想想,又加了半勺,用热水冲开,略一搅拌,再加半杯冷水,端了出去。
“先喝杯糖水吧。”摇摇快昏睡的郑直,将杯子递给他。
郑直搭起眼皮扫了谢鄂一眼,再看看他手上端着的杯子,勉强抬高身体,将鼻子凑到杯子上嗅嗅,没什么奇怪的味道。他也懒得伸手,脑袋一探,直接就着谢鄂的手咕嘟咕嘟喝起来。
……这人也太懒了吧。谢鄂着那黑色的脑袋心下嘀咕着,手上很有耐性地将杯子配合郑直的速度慢慢抬起。这种喝水的样子,简直象只小猫,让人忍不住想为他顺毛。
当然,有过之前惨痛教训的谢鄂再也不会把眼前这只收起爪子的老虎当成猫猫狗狗看待。收起爪子的老虎还是老虎,不小心会被抓伤的。
喝完糖水后,郑直苍白的脸渐渐有点血色,他咂咂嘴,一脸不满:“太甜了。”
“你不是喜欢吃甜的。”谢鄂收杯挺直弯下的腰身:“要不要再来一杯?”
“不用了。”郑直笑嘻嘻道:“我等外卖。”
谢鄂无语地将杯子拿回厨房冲洗一下,出来边擦手边道:“外卖送来还早,你要不先洗头洗澡一下。”
“没替换的衣服,你要我裸奔?哎呀,真不好意思~”
谢鄂回卧室找了会儿,拿出一套睡衣和内裤:“新买的,刚拆封洗过,还没穿。”
“谢啦,其实你穿过的我也不介意~”补充完糖份恢复了点精神的郑直冲他戏谑地眨眨眼,接过衣服。
带他进浴室讲解一下构造和使用方法,又从置物柜拿一条干净的浴巾给他,锁门出去后,谢鄂开始收拾有点乱的房间——沙发套上沾了不少草屑泥埃,明天恐怕得让谢姐拆下来送去干洗。
还有自己,跟他扶抱了半天,等下也得再去洗一次。
对讲机响了,外卖送到。他按下开门键,找出钱包,等外卖小哥大包小包送进来后付款给他。
负责这一区的外卖小哥跟他也算熟了,找钱时笑问谢鄂:“谢少今天家里有很多客人啊?订了这么多。”
“客人是有……”谢鄂看向浴室,含糊地叹了口气。
郑直同学的胃到底是几人份的,他心头可真没底。
第四章夜舞还有怪人
郑直洗完澡出来,餐桌上已经放了好几个外卖盒子,有饭有汤有意面有煎饺还有甜点。谢鄂正将它们从盒子里挪到盘子里。
“没必要那么麻烦,吃完直接扔掉。”郑直懒洋洋地单膊挂在谢鄂肩上。他打理得清爽干净,又马上可以吃到食物,心情大好,难得也客气了一把。
“快餐盒子受热后容易产生二恶英,对人体不好。”谢鄂倒好最后一碗汤,回头看到郑直湿答答的头发,皱起眉毛:“我有告诉你电吹风放哪里,怎么没吹干就出来?”
“饿了。”郑直笑嘻嘻坐下来拿起筷子,继续用他看起来不很快但效率惊人的速度扫荡桌面食物。
谢鄂看他还在不断滴水的头发,默默纠结一分钟,还是去浴室拿出电吹风,接上电源为他吹头发。
“你这人比女人还鸡婆。”郑直停下在吃的面,翻了个白眼。
“不吹干容易头痛。”谢鄂小心调整吹风角度,不把热风和水珠吹到郑直身前。
郑直更用力地翻了个白眼:“你妈一定是为了弥补起名的错而将你教育成一部会走路的真理全书,说出的全TMD真理。”
“不是我妈,是我哥和我姐。”谢鄂用手指拨动郑直的长发。老来得子的父母哪里舍得管教他,他的教育几乎都是兄姐们一手包办的。
“还真好猜。”郑直啐了声,感觉谢鄂的动作并不会妨碍到自己吃饭,索性也不管,埋头继续吃。
潮湿的头发比较僵涩,手指插入不好穿梭,只能轻轻抖动。吹了两三分钟,发丝半干,部分黑发随热风飞扬,带来一种似熟悉又陌生的香气。
熟悉是因为那是自家洗发水的味道,但不同人使用,产生微妙的区别。很难说明到底哪里不同,只能确定与使用在自己身上时的气味并不相似。
同样是草香型,大概就是森林里和阳光下的不同吧。
谢鄂有一丝闪神,思考为什么会觉得香气不大一样,与家人分享时就没有这么明显的区别。
郑直又吃完一份炒饭,嘴里得闲,一边喝汤一边转头问:“你吹头发动作这么娴熟,不会是经常帮女朋友吹头发?”
“是帮姐姐们吹。”谢鄂转回他的脑袋,说得有点怀念:“很久没帮她们吹了。”
“噗,难不成你恋姐?”
“帮她们吹有奖励。”渐渐干燥的黑亮发丝滑过肩头,谢鄂伸手撩向身后,手指无意间勾过郑直左耳冰凉的坠子,撞击出清脆的声音。靠近看了才发现,郑直耳上这块红色石头不是大家以为的琉璃,而是鲜红的石榴石,金属花纹包覆着长菱形的主石,一撮藏银流苏中间和底下不规则地杂坠着小石。他对珠宝价格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么大一块主石到底值多少钱。
“我还以为你视金钱如粪土,那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不是钱,而是她们会带我出去。”谢鄂笑笑,确定郑直头发干得差不多后,关了电吹风。
“哦?”郑直挑了下眉。
谢
![[死神同人]我的名字叫听花立雪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0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