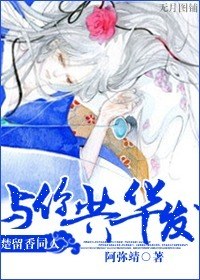藕燃索[楚留香传奇]-第6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我突然发现我一张嘴足以对付各种武功高强或正直或邪恶的各种人,可是却完全对付不了这个过于热情的大娘。
她就这么残忍的把我往虎口里送,我还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我被推进房间里的最后一眼我看到楼下银子爱莫能助的眼神,终于感到了绝望。
我看着从外面被关上的门,靠着门深吸一口气,抬头,摆出一脸职业性微笑看着石观音
"我有什么能为姑娘做的吗,若是嫌我们这茶不好,我们免费给您换。"
石观音完全不管我在说什么,用手转着桌上的茶杯,淡淡的开口
"过来。"
我瞪着石观音瞪了半晌,终于认命的走过去,手背在身后,习惯性的摸着我掌心因为捡回那条红绳而划出的伤痕。
虽然已经愈合但还是留着淡淡的痕迹,就如同我身上那些鞭痕一样。
我垂下眼坐到她对面,避免和她的一切目光交触
"原随云是被你支走的?他表兄的婚礼是怎么回事?"
她轻轻的回答
"我只不过派了个姑娘过去罢了,原随云的表兄不在江湖,是个大商贾,所以没什么名气,但是却确确实实是无争山庄的人。"
"然后你就让那男人爱上你派去的姑娘,并让那姑娘说想看看名满天下的无争山庄少庄主,是吗。"
我把手放到了自己身前,盯着自己的手,依旧在无意识的摩擦掌心的伤痕,顿了很久才说
"你总是这么聪明。"
"你比我更聪明,你尾随我们到了这里,只可惜我们一进镇子就被太过热情的邻里拉着到处打招呼,你没法继续跟下去。接下去你发现了我的茶馆,等了几天发现我不来。你知道良大娘一定知道我的住址,可你要是突然问良大娘一定不会说,所以你在这里塑造了个好形象,等到你再问时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
我平淡的说着好像再说一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突然手被她抓住,她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我急忙想缩手她却拉的紧紧的。
"是,不管怎样的计划只要给你看到了一丁点提示你都可以猜的□不离十。那么你能不能猜到,我现在在想什么。"
她凑在我的耳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抚上我的脸。我试图偏了偏头,躲开她的触碰,结果自然是无果。
"你想?你不想我再跑,所以才把原随云支开,没有原随云我根本不可能不被你找到的去任何地方。只可惜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石观音也是不守承诺之人,说五年现在才不过五个月。"
我调整好乱七八糟的心情,抬起头把目光从被迫和她交缠的手上挪开,定格在了桌上的茶壶上
"我只说五年内不把你强行带走,不代表我不能来找你。你说的那是我之前想的,我现在想。。。"
我正等着听她继续说下去她却顿住,抚上我脸的手用力,被迫我扭头,然后她的唇就覆了上来。
我一手抵着她,另一只被她拉着的手试图挣开,被迫的承受着她的吻,热烈而张狂的吻,如同在宣告她的所有权一样,让我感觉无可适从。
不经我同意的撬开我的唇,舌头抵开牙关就开始疯狂的攻城掠地。
石观音的吻一贯是霸道的,掠夺的不只有呼吸还有感情。你不能不沉沦,不能不跟着她的步调,陪着她沦陷。
她终于放开了我,我轻喘着把头扭过去,她从身后整个的把我抱住,抓着的手仍旧没有放开。
"你有感觉了。"
"放开我!"
她说的没错,我有感觉了,身体如同曾经的记忆被唤起,渐渐涌起的燥热和心底无法压抑的感情都在昭示这一点。
听到她这一句,原本还平静的我突然象被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跳起来,用力要从她怀里挣脱。
"你太不坦诚了。"
我站起身手肘用力顶着她,激愤的开口
"你要我坦诚是吗?那么告诉我,你来做什么,来让我难堪的吗?石观音你确实很厉害,我承认我和那些男人一样,为你而沉沦。我贱,我再抗拒也有感觉,所以来嘲弄我是吗?吻我?证明我是你的?是这样吗?简直莫名奇妙!"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会突然而起这么股无名火,听到那句话我只觉得自己很悲哀,所有的感情都被她玩弄在鼓掌之间,原本心底无法压抑的感情都被怒火烧了个干净。
我的余光看到她,面纱已经取下,她的表情变化很微妙。
我很早之前就发现,石观音不是总是面无表情,只不过因为把情绪掩饰的很好,不太看得出来罢了。
发现这点之后我就学会了看她的微表情,眉头的高低,眼睛睁眯,嘴角扬抑等等,这些才是我猜她心理的关键东西。
虽然凭余光看不到太多细节,但足以让我感受到她从有些愉快到失望的情绪,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看错了,因为那些情绪大多都不应该出现在她的脸上。
她沉默了很久,我的手也被她捏的生疼,她才缓缓说
"不是,我只不过。。。"
"只不过?"
我轻笑着
"石观音,于你什么都可以是只不过,而于我,我有不起只不过。银子你可以想杀就杀,因为他只不过是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小孩子是吗。原随云你可以想操纵就操纵,因为他只不过是个碍事的东西是吗。那些为了引我出去而被你杀死的人,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你利用的棋子是吗。而他们对我,是弟弟,是亲人,是无数我被迫背上的血债!"
我心口有些针扎的疼,毒发的预兆。早就发现,情绪激动会引起原本应该在午夜的毒发提前。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被她发现我的毒。我努力冷静下来在脑子里飞快的打着算盘。
不管她爱不爱我都不能让她知道,她若爱我不想她伤心,她若不爱我不想被她嘲弄。
我试图平复下因激动而加快的呼吸,咬着牙忍着渐渐明显的痛楚,原随云不在,看来我今天难熬了
"放开我,我要下去了,你若还想见到我就不要跟着我。我知道我威胁不了你什么,算是我求你,现在,放我走,让我冷静下。"
我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用,如果还是那个黄山上与我一起过春节元宵的石观音,会放开我的吧。
我只能赌一把,我别无他法。
身上的束缚松开了,她一直桎梏着我的手垂下,放松。转到我正面,拉着我手的那只手顺着把我的袖子向上推开,红绳手链就滑了下来。
她用食指指腹顺着那条手链摩梭,她用另只手与我的这只手五指交缠,她把自己的袖子也向上推了推,相似的手链滑下,两条手链撞在一起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和她都没说话,视线在手链上相撞,我垂下眼帘把视线挪开,她终于开口,缓缓的
"好,我等你回来。"
我突然一怔身子晃了晃抬头看她,直直看进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澄静很真实,似乎原来那层让人琢磨不透的白雾散去了一般。
我赶忙垂下眼,抽出手,快步下楼。
银子就在楼下站着,看到我下来松了口气,就好像我跟去鬼门关里溜了圈儿似的。
但他看到我额角的汗和煞白的脸色立刻脸色一变跑过来扶我,连抱带拽的把我拽进后院
"怎么会这会儿子毒发!姐你到底在里头跟那疯女人干了什么啊!"
他也急的满头是汗,我苦笑着按着心口,我能说是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不知道为什么吼她了一顿,然后把自己害得毒发的吗。
"就是聊了会儿天。。。你快点吧,家里才有药,我没带着,我还不想死石观音面前。"
他立刻解了马的绳子,把我扶上马,飞身跃上一拍马屁股就往山上冲。银子内力不够,不可能用轻功带我,最快的办法就是骑马。
他边喊着边打着马屁股,好像指望马能打出对翅膀似的
"早说过让你随身带的!"
"那药伤身,不是迫不得已不要吃。这可是医嘱。。。咳咳,我要是昏了就不要给我吃药"
血腥已经漫进了喉咙,我几乎是整个人匍匐在马背上,全靠坐在后头的银子抓着我。
心口疼的要窒息,又不断地咳嗽,眼前开始慢慢产生幻觉。
那些被石观音杀了的都浑身是血一步步象我走来,眼神怨毒而愤恨,渐渐的所有的脸都变成了银子,一句句控诉着我的自私,控诉着我爱上一个不断想要他命的人。
我痛苦的按着头,明知是幻觉还是一样的无能为力,我没有强到能抵御幻象的精神力,这种精神折磨比身体的痛苦更要恐怖。
接着场景变了,四周都是石观音和各式各样的男人翻云覆雨,盼目巧笑,说着一句句情话,然后是嘲弄的表情,一道道鞭刑,明白的诉说着,你这个贱货,不过是个玩具还想奢求什么。
"不!"
我按着太阳穴终于忍不住哭叫出声,我不知道是幻觉要把我的心撕碎还是确确实实的身体的痛苦将要了我的命。
。。。
"姐,姐。。。"
耳边是轻轻的声音,费了好大劲才撑起眼皮,我已经躺在了自家床上,银子一脸担忧的坐在床边,手里还拿着快毛巾在给我擦着额上冷汗。
动了动就觉得浑身酸痛,果然我不该骑马,特别是在被那毒折磨的时候
"你总算醒了!我派小银给少爷,不对,给哥送信去了,我还怕等他回来你就是具尸体了,你刚那声惨叫,山猪都要被你吓晕过去。"
我抬手就有气无力的一巴掌糊他脸上
"那感情好,我们今天晚饭就有山猪了。你给我吃药了吗,什么时候了现在,石观音没跟来吧?"
他把我的手按下去瘪着嘴
"天都黑了,给你煮了粥,等我热热给你端来。药没吃,到这里时你已经昏过去了,那女人跟没跟来我不知道,我只急着把你弄回来况且她真跟着我也发现不了,我又不是少爷。"
我也懒得纠他对原随云的称呼了,爱少爷就少爷吧,反正人前给我好好的喊着哥就成。
他说的倒也不错,石观音想跟,江湖上能察觉到的也没几人,何况是才练武不久的银子跟差点死过去的我。
至于那药,说是药本质也就是大剂量毒品。石观音给我下的药本来就是大麻萃取的毒和别的什么玩意儿的混合,这种不能压制毒发却可以缓解毒发的痛苦的药,除了是毒品还能是什么。
作为一个从小接受过禁毒宣传的新时代青少年,我不想碰毒品,一点都不想,就算是当作麻醉剂使也绝不要。
银子蹬蹬蹬的去给我热粥,我躺在床上理着乱七八糟的思绪,今天发生的事太多,实在得好好消化。
或者说,不是事多而是受的冲击大,石观音的出现,那个突如其来的吻,说等我回来时的眼神。。。还有我不要命的心里话。
我不知道我干嘛真的就坦白了,真的把心里的所想都跟泄愤似的说出来。
其实我真的很想她,看到她时心底的悸动不由我来控制,甚至我还试图回应她那个吻。
但为什么我还要说那些话,为什么要把一切都摊开说清。也许真的是我在南中太长时间了,这里的人太淳朴,让我一瞬间忘了要伪装,忘了说话要有取舍,忘了石观音不是那个我什么都能说的人。
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么激动的说出那些话,如果我顺着她的吻告诉她我想她我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