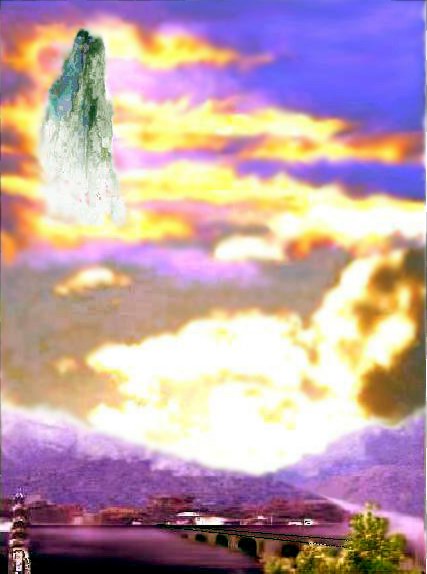[袁成] 青山遮不住-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门在他身后无声地关上,他没有来得及开口叫一声“师傅”,就被拥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别说话,先让师傅感觉一下,和五年前相比,你是瘦了还是胖了?”
那个低沉的有些沙哑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说着,熟悉的语调带着温暖的呼吸摩挲着他的脖子有些痒,成才闭上眼睛,体会着这个从天而降的拥抱,感觉着拥着自己的那个力量越来越紧。
熟悉的声调,熟悉的力量,熟悉的拥抱,熟悉的记忆。
这是第二次,上次是分别,这次是重逢。
都是在南京。
这个留给自己痛苦和欢愉的城市,这个还会带给他欢愉和痛苦的城市。
成才没来由地鼻子有些发酸,这些日子以来的挣扎和纠结一下子从心中涌腾,顺着放松的身体和发热的脑袋,喧嚣着马上就要冲出理智的堤防。
“瘦了。”袁朗却迅速地松开了双臂,身体往后了半步,仰着头,认真地看着成才的脸,说话的口气却像是玩笑,“难怪,心事不少啊!”
在袁朗面前,成才不知道为什么,从来都有一种精神世界无所躲藏的感觉,袁朗在他面前,仿佛有一种洞悉一切的天赋,自己心里的波澜总是轻易就被他点破。
或许是一开始放弃旧我主动追随袁朗和他的理想开始,就决定了两个人关系中谁是主动者和控制者。就好比婚姻,有过来人说:谈恋爱时谁的气场强,结婚之后谁就做主。
有时候,成才觉得,或许这也是自己甘心如此或是乐得如此,他在袁朗面前,不想遮掩什么,不想显示什么。两个独立的人,时时要面对惊心动魄的斗争,时时要伪装自己到变态,如果在信任和珍视的人面前,再不放下面具,敞开心扉,那么就真的异化成革命的机器了,在成才心里,那只是工具而已,而不能当得上“人”这个称谓了!
“喝点红酒吧!”袁朗总是这样,导演一样掌控着场景的切换,成才刚被挑起的前一种情绪轻易地被他摁了下去,后一种情绪对话之间又被开启了瓶塞。
成才点点头,抬头瞥见屋角的酒柜上,放着几瓶法国红酒;袁朗没有提烟,桌上的烟缸里却有不少烟头,成才记得在上海的时候,自己在他面前流露过不喜欢烟味。
“红酒要比抽烟健康,师傅,你进步了!”
袁朗一边递给成才高脚杯,一边笑出声来,“就许你军衔高歌猛进,不许你师傅进步啊!北平站抄没了不少大汉奸的家财,别人眼睛里都是金银珠宝银票房契,只有我看上了他们家里的美酒啊!那可是成窖的葡萄酒啊,你知道吗,北平郊外的密云县,气候条件和烟台不相上下,很适合藏葡萄酒!”
袁朗难得这么多话,成才敏感地收到了他的意图,几句话,说的是酒,其实是告诉自己他目前的身份和任务。
成才会心地轻轻笑了一下,酒窝也是乍现即收。接过袁朗递过来的高脚杯,深红色的葡萄酒灯光下折射着奇幻的光芒,他盯着透明的红色液体看了一会儿,才慢慢开口,“你呆多久,师傅?”
“我和齐桓代表北平站来参加双十节庆祝大会,会完了再走。齐桓住楼下,不过今晚不在,他原来的老同事请吃饭。”袁朗再一次切换了场景,快得出乎成才的意料。
看见成才吃惊的眼神,袁朗举起自己的杯子,伸到成才眼前,“叮”地一声碰了一起成才拿在手中的酒杯,“吓你一跳吧,齐桓现在是我的手下,他不知道我的身份,不过,我可跟延安打听清楚了!你小子挺能干啊,当初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你发展下线,你倒好,把你师傅的话忘脚后跟了吧!”
袁朗的话一下子让成才红了脸,“师傅,这不是情况特殊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您现在是他的上司,您说说我发的这支箭怎么样?”
“箭不错,弓箭手更不错!”袁朗眼睛里带着笑意,满意地注视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年青人被自己夸得脸色更红了,刚进门时眼神里的躲闪和无措隐去了,袁朗有些心痛,他猜得出那些躲闪和无措是因为什么。
“听国防部二厅的人说,你双十节结婚?”袁朗尽量装作不经意地开口。
听到这句问话,成才还是猛地抬起头,“国防部二厅的人?谁啊?”
“老白,你认识的,五年前在南京,我的联络人,军统老特工了,不过一直不得志,他是郑介民的老乡,所以戴笠死了之后,就到国防部二厅了,也算是你现在的同事吧!”
“噢,想起来了,老白,国防部大院里好像碰到过一次。看来,我结婚的事,南京城知道的人不少啊!”
“那可不是!齐桓也知道,可不是我说的啊,他还说要去参加你的婚礼呢!”
“是吗?”袁朗说的这些正是成才这些天所烦恼的,“唉,我那个二舅哥,高城高旅长,也不知道他在南京城撒了多少英雄贴呢!”
“他这样做没错,高国将军是抗日英雄,他的妹妹结婚,新郎还是除奸杀敌的抗日义士,当然应该大办一回!”说完,袁朗喝了一大口红酒。
“那是他们的婚礼,不是我的婚礼!”袁朗的话让成才有些吃惊,更有些失望,他赌气似地仰头一口喝光整杯的红酒。
“你这么说,有些不厚道。”沉默了片刻,袁朗应了一句。成才喝酒的样子让他有些怜惜,但是他还是得这么说。
“你凭什么说我不厚道?我欠着他们高家的吗?就因为他高国提携我当副官还是他高城把我从豫东死人堆里救了出来?我可以赔上他们高家这条命,我舍得!可是我条命不属于我啊,它属于组织啊!我的爱情,我的婚姻也一样,它们都不属于我支配啊,它们都属于组织!你不也一样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睡在中央领导的屋里,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叫过你爸爸!咱们一样,什么都不属于自己,一切的一切都交给组织交给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了!”
那一大杯红酒一下子倾进胃里,红酒灼烈的后劲释放着成才郁闷与痛楚,放大着他的不甘与不忿,多少年压抑着的情感和伪装着的个性在酒精的鼓励下终于冲破了适才被袁朗通过重重切换场景控制着的理智堤防,倾泄而下,一发不可收拾。
“呯啪”一声,袁朗把手中的酒杯使劲扔到地板上,酒杯裂成几瓣,刚才还鲜亮的红色落在地板上便成了混浊的棕色。
成才被酒杯落地的声音怔住了,他失魂落魄地看着地板上的棕色液体,耳边都听到袁朗的低低的喝斥声,“混话!虚无缥缈的理想?!当年是谁说的要让你的兄弟许三多那样的人,人人都能上得学堂,人人都能有自己的田地有自己的尊严,这个理想虚无缥缈吗?这个理想不值得你付出一切的一切吗?你在乎你的爱情你的婚姻,可是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有人在乎吗?”
成才的眼睛暗了下来,他瑟缩着蜷在沙发里,捂住自己的脸,声音呜咽着从指缝里传出来,“可为什么必须结婚?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不怕死,我早就把生命献给理想和信仰了,可是我不能这样欺骗自己的感情,也欺骗高梅生的感情,我痛苦,我知道她也痛苦!”
袁朗走近他,紧贴着成才的身体在沙发上坐下,右手搂过成才肩膀,左手伸出去拉下成才捂住眼睛的手,轻轻托住成才的脸,深深地看着那双眼睛,那熟悉的黑眼睛里满是痛楚和迷茫的泪水,苍白的脸颊上却有一抹红酒一样醇的颜色,袁朗盯着那双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沉陷进去的眼睛,心里叹着气,开口却是成才不熟悉的郑重语气,“成才,你痛苦,你也为高梅生痛苦,可你知道吗?看到你痛苦,我也会痛苦,心很痛,为你心痛。那年看到你受刑,小原那些变态的刑罚,你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不比你好受,你上刑场,其实我也在下地狱。你说的不全对,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不属于自己,生命,婚姻都是属于组织的。可是感情,感情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我是你,我会向高梅生坦白自己,就像现在的袁朗,此时此地的我,要向你坦白,我在乎你,为你心痛,心里惦记着你。”
成才没有想到自己心里藏得深深的话竟然从袁朗的嘴里说出来,他从来都以为自己是在一厢情愿地爱慕着袁朗,却不曾想到袁朗竟然对自己抱着同样的情感,看着袁朗凝视着自己的眼睛里真诚的殷切的神情,他一时间大脑有些空白,失语一样地手足无措,想开口确认袁朗是不是在安慰他?却又怕袁朗收回刚才的话。
袁朗抬起左手轻轻拉过成才的身体,把他拥进自己的怀抱,成才刚才绷得紧紧的身体一下子松弛下来,几乎是靠在袁朗的身上。
成才身体很热,红酒的灼热的酒劲从头脑中消退,却燃烧着躯体的火焰,滚烫的气息透过美式制服衬衫薄薄的面料撞击着袁朗的触觉,他下意识地用力把成才抱得更紧,紧得连他自己都觉得胳膊发疼,可是怀抱里的那个人都似乎很享受这用力的拥抱,似乎越紧他越舒服,皱着眉头,明显有些疼,可是嘴角却露出那对今晚难得一见的酒窝,那对酒窝绽放在自己的怀抱中,让袁朗一时间意乱情迷,不能自持。
《青山遮不住》第二十八章(上)
一切都那么自然,就像春天的河,太阳闪着金光,温和安宁,暖风轻轻地拂过封冻了一冬的河面,冰面之下一直缓缓涌动的暖流听到了阳光和风的呼唤,带着冲动,配合着风的热情,努力去融化寒意与冰冷,转眼间,一河清亮亮的水活泼泼地奔流起来。
无论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的袁朗,还是在德国有过“纸上谈兵”情史的成才,此前的所有经验都无法解释今天晚上两个人的缠绵与激情。那样深入而绵长的吻,那样默契而自然的配合,仿佛不是第一次,而像是做ai多年深深了解对方身体的多年情侣,湿润得那么快,前戏那么长,高潮那么久,那么持续――像沙滩的波浪,巨浪过后,平息一会儿,又有更大的浪头翻涌。急促的呼吸与滚烫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在心里只期望着时间停止,只有两个人紧紧的拥抱,只有唇齿之间甘甜的纠缠。
作为过来人的袁朗体会着无法形容的欢愉,那一种到达山顶羽化成仙的感觉,是他在短促的婚姻中没有感受过的,那时的他,带着年青的冲动发Xie着激情却无暇体贴温柔,也迟钝于爱的表达和经营。
身下的人闭着眼睛,脸颊潮红,眼睑上竟然也蒙着淡淡的绯红色,那个年青而健美的身体在最初的不适之后,迅速的湿润起来,袁朗深深地进入,撞击,那幽暗湿润的世界似乎是没有尽头却散发着神秘诱人的气息吸引着自己一次一次要到达最深的终点,隐约中,他听到有沉哑的吼声从自己的喉里发出,他听到身下的Shen吟,带着欢欣,不连贯的,低低的,听起来像是哭泣,又像是哼唱。
这是他们的第一夜,是他们唯一的自由,唯一的放纵,唯一可以互相拥有对方的机会,他们不愿意停止,他们带着忧虑珍惜着每一分时光,一次一次地在温存缠绵中到达那座铺满绿草的山顶,然后在黎明到来之前,沉沉睡去。
像是在梦中,袁朗听到那人在耳边轻轻地说话,“袁朗,我们死了,葬在一起吧?如果我先牺牲了,找不到我的骨灰,我今天就把我身上的玉坠留给你,好吗?”
袁朗睁开眼,黑暗中,身边那个人的眼睛愈发地明亮,带着忧伤和满足,静静地看着自己,袁朗嘴角牵动一下,想给一个笑安慰,却笑不出来,他伸手捂住成才的嘴,“我牺牲了,可没有信物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