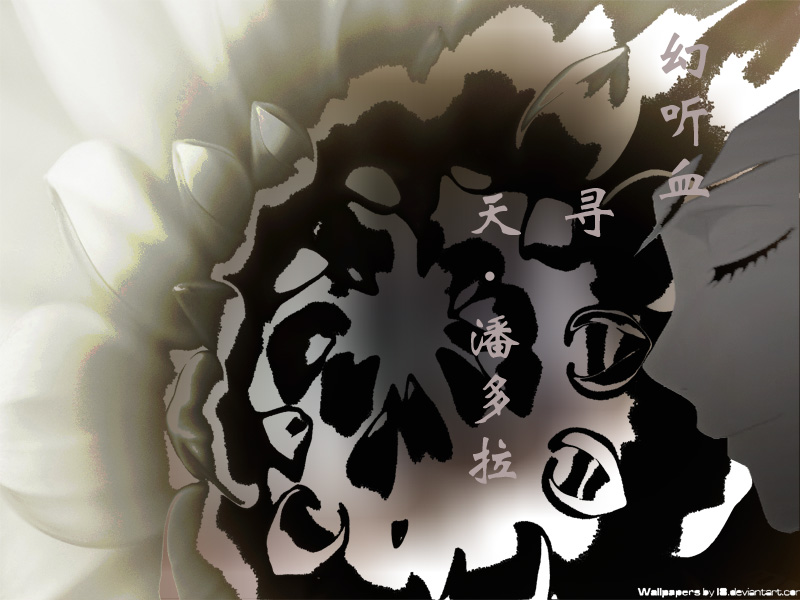潘多拉之子-曙光圣战 by 时禁-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缇苏却仅仅回了个意义不明的微笑,情人般温柔抚摸赛德伤痕累累的分身。有技巧的上下撸动、搓弄,却不见在他离开时软垂的小东西恢复精神,想是一次次伤害累积下的伤痛彻底爆发,令它失去了生气。
时间不等人,赶场的缇苏显然无法陪它慢慢耗著,当机立断,弯身亲吻印著红痕的可怜头部,张开小口,灵巧的舌头探出红唇,技巧的舔弄,紧接著,将它含入口中。缇苏没有亚罗尔洁癖的毛病,闲暇时又以调教为乐,嘴上功夫绝不是纸上谈兵之人可比,故而,即便是赛德因创伤难以享受快感的分身,亦无法抗拒的逐渐精神起来,直至完全勃起。
满意的吐出口中物什,灵活的手指描摹出它完美傲人的形状,“啧啧,就这里了~~”在赛德眼神的追随中,缇苏取过与火炉配套的长镊子,伸进炭火,翻动下徽章後,将之夹到乌黑有神的眼眸前,“你看这枚胸章如何,是不是很美?我决定把它送给你~~”
缇苏的声音如同他的人,是一种蛊惑人心的音色,却无法对赛德造成半分影响。这对赛德来说,即幸运,又不幸。幸运,因为他不会成为这个披著美丽外皮魔鬼的俘虏,从此万劫不复,不幸,因为他必须清醒著面对加诸於自身,残暴的酷刑。
“滋滋”细小的声响,带著些许血腥味、些许情色气息的空气中,添加上一种令人充满食欲的香气──烤肉味。
滚烫的蔷薇徽章被印在勃起的柱体上,位置是龟头下方两毫米处。赛德绷紧肌肉,鼓胀的仿佛要撑破皮肤,眼角因眼皮过度的拉扯呲裂,流下两道眼泪般的血痕。
缇苏对手中器具的挑逗一直没有停止,但灼烫造成的伤害,不可挽回的对敏感器物造成影响,失去硬度的柱体躺在白皙的手掌中抽蓄,本应激流般奔射而出的乳白色浓稠汁液,像肾脏衰竭的老人尿尿似的缓缓流出,在地面上留下一小滩渗著缕缕血丝的精液。
扔开镊子与徽章,认真的欣赏了下自己的杰作,兴高采烈的说道,“怎麽样,很漂亮吧,你绝对找不到比我技术更好的人。”这麽说著,看向赛德面容的缇苏猛的愣住,细长的眉宇挤到一处,犹豫著伸手探赛德鼻息。
还好,呼吸虽然微弱,总算还有口气在。
男人最重要的器官受到这种惨无人道的伤害,再顽强的毅力亦无法扭转肉体强制敲响的警锺。赛德瞪大到极致的眼睛仿佛随时都准备反击般,死死瞪住缇苏,但那对黑珍珠却已经失去光彩,连瞳孔都隐隐有放大的趋势。
赛德晕过去了。
门外再度传来手下的催促声,缇苏深深看了那个失去意识都未放弃与自己对峙的男人一眼,转身,大步流星的向门外走去,与审讯室门口的兵士错肩而过时,淡淡吩咐了句,“找个医生给他治下。”语毕,头也不回的离开。
士兵望著长官远去的背影,心中虽然疑惑,军队中严明的纪律,却令他不假思索的将命令付诸行动。
监控室内,伪造视频形象和声音,骗过缇苏的亚罗尔,一直关注著正对走廊门扉的监控摄像头画面,当看到缇苏终於从中走出,并一路往顶楼停机坪而去,提著的心放下一半。
不是不担心被带进审讯室的赛德,但凭亚罗尔对大主教的了解,百分百肯定那个昏庸、自私,除了对自己还不错外一无可取的老男人,绝对会要求亲自制裁,那麽缇苏就绝不会下杀手。只要不死,倚仗变异罪子变态的恢复力与第三国际的顶尖技术,亚罗尔有理由相信,只要能将人活著带到第三国际,无论受到怎样的重创,都能够治好。
缇苏的身影消失在关闭的飞艇舱门後的瞬间,焦急等待的亚罗尔迅速站起,一直蹲在人身边的贝斯特更是弹簧般弹跳起来,一双兽眸期盼的盯住美丽的紫罗兰。
深深的吸口气,捏捏一直拽在掌心的大手,亚罗尔坚定道,“走吧,我们去救赛德。”
“走”字方出口,贝斯特已经反被动为主动,拉著亚罗尔,闪出门,全速向赛德所在的审讯室而去。路上遇到的圣裁军士兵,能避则避,避不过的,全为贝斯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扭断脖子。
戒五十二 抵达
将赛德平放到地上,阖起无神的眼眸,亚罗尔边挑拣出有限物资中可用之物,简单处理伤口,边安抚的亲亲贝斯特,让他不要冲动。
“缇苏下手太狠了。”当灵活的素手来到伤痕累累的分身,连同样心狠手辣的亚罗尔都皱起眉头,以他的知识及专业程度,从重叠的伤口上便能大致猜到过程。反复勃起後受伤疲软,会使快感成为传递危险的信号,形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惯性循环,这样下手,说是想将作为男人的赛德废了都不为过。
贝斯特忍住嚎叫宣泄愤怒的冲动,兽眸闪烁著危险诡异的红,恨不能将伤害同伴的人撕成碎片。好在情绪并未蒙蔽他的心、他的耳、他的鼻,听到由远及近的细微脚步声,便警惕、迅捷的转到准备用外套包起赛德带走的亚罗尔身後,用保护的姿态挡在门与两人之间。
已经十分了解贝斯特的亚罗尔当然能明白他行为的含义,压著声音问,“有人来了?”
“嗯,刚刚拐到门外的走廊上。”贝斯特回答。
“还有多久到?几个人?”
“很快,来了两个人。”
只有两个吗?或许,是个好机会,亚罗尔心中思忖,对贝斯特道,“宝贝,你到门口准备,这两人一进门,直接杀了,不要给他们任何发出警讯的机会。”
“好!”贝斯特言简意赅的应下,同时飞速窜到门边隐藏。
片刻後,亚罗尔也能听到军靴叩击地面的声响。
此时,前去医务室找医生的士兵正站在门外,稍侧过身子,为手提医药箱的医生开门。
门方打开一半,士兵还来不及看清审讯室中的情况,骤觉颈间剧痛,来不及感到惊骇的眼睛疑惑的看向医生,歪斜的视线中,映出蹲在抽蓄著、生机尽绝的医生旁边,回望自己的冷酷兽眸,这是他人生中看到的最後一幅画面,接著,脑袋耷拉在肩上的身体,直挺挺仰面倒到地上,发出沈闷的撞击声。
亚罗尔抱著赛德走出来,冷眼看了看一左一右躺在门两侧的男人,士兵已经断气,但上下身被撕成两半,肚肠、内脏洒了满地的医生,还张著嘴,一口一口喷著仿佛吐不完的鲜血,发出痛苦的“嘶嘶”声。
把赛德交到贝斯特怀中,亚罗尔踏著血泊,踱了两步,从怀里抽出一条淡紫色手帕,弯腰,轻轻拭去医生脸上的血迹,却阻止不了更多鲜血从他口中涌出,“真可怜,我帮你解脱吧。”一束光线穿过医生额心,结束了他的生命。
恼怒的瞪了贝斯特一眼,早就警告过他,结果还是把现场弄得这麽难以收拾,责怪的话语却在纯粹的眼神中化为一声无奈宠溺的叹息。
搜刮干净两人身上的武器、药品、证件,血腥的现场意味著有入侵者这个事实很快会被发现。亚罗尔不得不改变计划,带著贝斯特,驾轻就熟的前往医务室,将留守其中,缺乏战斗力的医疗人员全数绞杀,迅速用消毒水消除身上的血腥味,换上白大褂,并将穿上病号服的赛德安置到病床上,两人似模似样推著往直达顶楼的电梯而去。先一步救出的思力和弗轧,早在接到“缇苏离开”消息的时候,已经摸到停机坪,等待会合。
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基地,一队队士兵从两人身边经过,有好心的,还会顿一顿步子,提醒两人不要四处走动,避免遇上危险。留守的军官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入侵者能在这麽短的时间改头换面,并胆大包天的行走在士兵中间,等到他们发现一架直升机未经通报起飞时,为时已晚。
乘坐在飞艇上的缇苏第一时间收到汇报,稍微想一下,即意识到这是亚罗尔用的一招调虎离山计,对於自认十分了解好友的他来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局面。
亚罗尔是个谨慎的人,他布局,向来讲求一切尽在掌握,不轻易涉险,像直闯敌方老巢这样大胆,甚至可说有勇无谋的做法,绝对不是他的风格。这也是缇苏如此轻易中计的原因,换作任何一个其他对手,都不可能在军事才能出众的年轻统帅面前耍这种花样。
对贝斯特的认识仍旧停留於在花丛草堆中无忧无虑扑蝴蝶的小兽的缇苏,当然不会想到提出大胆设想的人不是聪明的好友,只道亚罗尔了解他,就像他了解亚罗尔一样,才会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坑了他一回。
不得不说,亚罗尔的运势非常强,收到消息打算调头指挥追捕的缇苏,接到来自真正大主教的通讯视频电话,内容居然与他先前调开缇苏编造的完全一致,军情告紧的大事面前,亚罗尔几人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指派基地驻军继续追捕後,缇苏依照原计划,迅速赶往前线。
失去了缇苏这个运筹帷幄的大将,亚罗尔凭借聪明的头脑和书本上学来的理论知识,在与追击部队的周旋中居然稳占上风,终於在迂回了一个月後顺利到达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是传承了上百年,早在潘多拉病毒爆发前已经独立於世的科学岛,所有研究人员梦想中的天堂,即使是圣谕院,也无法干涉。对此,圣谕院高层即是眼馋又是忌惮,情绪极其复杂。第三国际拥有最顶尖的科技力量,意味著他们掌握著最先进的武器军备,为了保证安全,科学家们以相当优越的条件,与第一佣兵团“远征”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一方免费提供装备、药品等重要物资,一方负责捍卫第三国际的安全。圣谕院也曾想破坏双方关系,却是无疾而终。
赛德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後,大部分伤势已经痊愈,唯独私密之处,那不堪的伤口依旧鲜明,每每见到,摆脱不了的恐惧感和屈辱感就会将他包围。其实,以现在的技术,这样的烫伤并非不可治愈,完全可以抹消得连疤痕都不留下,关键是心理上的创伤,就像亚罗尔说的,只要赛德无法对此事释怀,即使看不见伤疤,它也依然存在。
戒五十三 温馨
亚罗尔呈交上伦斯诺夫博士的回信,很快得到第三国际的通行许可,并由向导直接引往“潘多拉”研究大楼的会客室。
“你跟伦斯诺夫博士很熟?”等会客室只剩下他们五人,赛德提出疑问。
“不熟。”亚罗尔盯著好奇的在房里每一个角落嗅嗅摸摸的贝斯特,避免他做出些令人头疼的举动。“之前送过贝斯特的血液样本过来检验,伦斯诺夫博士回信中邀请我带贝斯特来第三国际,做一次全面检查。”
赛德点点头,表示了解,便沈默下来。
不多久,贝斯特突的窜回亚罗尔身边,四肢著地,摆出随时迎战的防御姿态,紧紧盯著会客室大门。其他四人立刻知道有人往这里来了,也打起精神,做好应付任何变故的准备。
紧接著叩击门板的敲门声,会客室大门被人朝外打开,一个看来六十多岁,身高方及贝斯特胸口,胡子拉碴、蓬头乱发的小老头儿走进来,若是脱下那一身显眼的白大褂,到繁华的街市上溜一圈,绝对没有人能想到他是当世最有名的潘多拉专项组组长,反而会有九成人怀疑那只是个疯癫老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