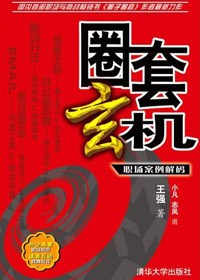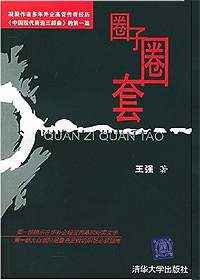樱的圈套-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不是打听三宅吗?三宅的太太就是菲律宾人哪。”老油条摸摸眼睛,狐疑地看看我,又看看文件夹。
“对了,千绘的母亲是外国人。”我掩饰地找补了一句,接着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对不起,这上边没有记录。”老油条翻弄着文件夹说。
“三宅先生没说过他们一家要搬到哪里去吗?”
“好像没说过。对了……”
“您想起来了?”我又往前探了探身子。
“说是要关了这边的店,搬到很远的地方去。”
“很远?”
“具体什么地方,他到底说没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千绘的母亲是不是……做女招待的?”
“嗯,在菲律宾酒吧。”
“您知道那个酒吧的店名吗?我可以到那个店里去打听一下。”
“店名我可不知道,只听说在堀之内那边。诶?小学毕业?他们搬到大仓公寓的时候,孩子有那么大了吗?”老油条说完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
“麻烦您了!”眼看谎话就要被拆穿,我慌忙撤退。跑了很长一段路以后,回头看看没有人追上来,我才气喘吁吁地放慢了脚步。
老安的太太是菲律宾人,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他为什么没向我说明呢?当然,他主要说千绘,没怎么提到太太的事,但是不是觉得娶了个菲律宾老婆觉得很丢脸呢?我还不是一样,在不动产公司听到他的太太是菲律宾人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可见歧视穷国的意识还是根深蒂固的。
堀之内是首都圈内有名的红灯区,有泰国浴,也有很多酒吧。所谓的酒吧,既没有酒也没有菜,也没有桌椅板凳,只有两三个浓妆艳抹的女郎站在里边抽烟聊天。她们身上穿着几乎透明的衣服和超短裙,只要客人一进店,她们马上就会色迷迷地靠上去,浪声浪气地打招呼,“玩儿玩儿吧”。对,她们是妓女。堀之内的酒吧都是为嫖客提供短时间性服务的店,可以称之为“性快餐店”。
横滨的黄金町也是这种地方。想到这里,我想起了江幡京,心里一阵难过。可是,现在的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多愁善感。我不单单是个过路人,我的目的是找到千绘的母亲当过女招待的店。我走得很慢,不时四处观望,结果被误认为是在找妓女的嫖客,路两边的妓女们不停地向我打招呼。
为了躲避妓女们的纠缠,我在一个路口往右一拐,走进一家叫做“玛布提”的店。
店里黑乎乎,静悄悄的,收款台也没有人。正面挂着黑天鹅绒的帘子,好像鬼屋的入口处。我掀开帘子往里看的时候,有人说话了。
“4点才开始营业呢!”一个推着拖把拖地的男人出现在我面前。
“请问,您这里有外国小姐吗?”我爽快地问。
“有啊,我们这里是菲律宾小姐,1个小时3千块,便宜!”
“我想打听一个人,有个叫三宅的菲律宾小姐在您这里干过吗?”
“你是干什么的?”男人的声音和表情都变了。
“我是她前夫的亲戚。前些日子,她前夫的父亲病逝,遗嘱中说,要把财产分给孙女一部分。这孙女就是这个菲律宾小姐和前夫生的,叫千绘。大概是因为老爷子只有这么一个孙女,才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吧。可是现在不知道千绘住在哪里,所以我就到这边来找找看。”我信口说完上述谎话,把一盒事先准备好的点心递过去,“这是一点小意思。”
“真啰嗦,总之一句话,你是想知道那个菲律宾小姐的住址,对吧?”
“对,后来她又跟一个姓三宅的日本人结婚了,应该姓三宅。”
“三宅?是辛迪吧?”男人用手顶着太阳穴思索着。
“有个女儿,叫千绘。”
“啊,你说的这个菲律宾小姐,大概就是辛迪。”
“那么,三宅辛迪辞掉这里的工作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我就势追问道。
“辛迪是她的艺名,本名叫——”
“维拉亚!”从帘子后边闪出一个女的,清秀的眉眼,乌亮的黑发,棕色的皮肤,修长的身材,圆圆的小脸蛋上洋溢着异国情调,典型的南亚美女。
“哟!萨布丽娜,今天来得够早的呀!”
“井口先生好!我去医院拿了避孕药以后直接过来的。”
这个叫做萨布丽娜的妓女对我说,辛迪本名叫维拉亚,不是菲律宾人,而是泰国人。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在不动产公司的那个老油条眼里,什么菲律宾,泰国,越南,都是一样的。
“辛迪有个女儿,”萨布丽娜继续对我说,“叫千绘,辛迪天天带着女儿的照片,我见过的,特别可爱!”
“辛迪是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我趁热打铁。看来辛迪就是千绘的母亲。
“很早了,大概有五六年了。”
“您知道辛迪离开这里以后到哪儿去了吗?”萨布丽娜并没有穿高跟鞋,但我跟她说话的时候也得仰着头,她比我高一大块。
“名古屋。”
“您知道具体地址吗?”
“不知道,她只告诉我是去名古屋。”
我看了看井口,他也摇头表示不知道。
“您没问她到名古屋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吗?”我继续问萨布丽娜。
“辛迪说她要在那边开一家自己的店。”
“她自己开店当老板?”
“是的,她又找了一个老公,是新老公给她出钱开店。新老公是名古屋人,所以要到那边去。”
“新老公?这么说她跟三宅先生分手,又跟别的男人结婚了?”
“当时还没有结婚。按照日本的法律,女人离婚以后6个月以内是不准结婚的!”
这个妓女日本的事情知道得还不少。
“她的新老公的名字叫什么?”我继续追问。
“不知道。”
井口也摇摇头。
“店名呢?”
“我没问,落合经理也许知道。”
“落合经理?”
“卡萨布兰卡的。”
井口补充道:“就是拐角那家泰国浴。”
“落合经理说他在川崎火车站见过辛迪。”
“什么时候?”
“辛迪从这里消失的那天。”
我把萨布丽娜的这句话理解为辛迪离开川崎去名古屋那天。我向萨布丽娜说了声谢谢,转身对井口说:“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托你们的福,我寻找千绘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喂!有完没完哪?”
“我想现在就去见卡萨布兰卡的落合经理,请您给他打一个电话,就说有个人要去找他问问辛迪的事,这样我会更顺利一些。”
“你直接去有什么不可以的吗?”井口表现出厌恶的神情。
“我带你去!反正我现在有闲工夫。井口,不许把点心都吃完了!”萨布丽娜说着就往门外走。
我又问了井口一个问题:“有辛迪的照片吗?”
“没有没有!”井口不耐烦地挥挥手。
我只好追着萨布丽娜走出了店门。
卡萨布兰卡是一家装饰成中世纪城堡模样的泰国浴。刚到门口,一个长得女里女气的负责拉客的家伙就贱声贱气地跟萨布丽娜打招呼说:“哟!打算换个地方,来我们店上班呀?”
“落合经理在吗?”
“在呀。我说这位大哥,现在是优惠时间带,每次优惠5千日元!”负责拉客的家伙好像没有看出我是萨布丽娜带来的,大声冲我嚷嚷着。
我指指萨布丽娜又指指我自己,紧跟在她身后进了店。
萨布丽娜跟这里的人很熟,连个招呼都不用打就顺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往里走。左拐右拐来到里边一个房间,敲都没敲一下就推开门就去了。
里边一个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的家伙正在看电视上的赛马直播,看见萨布丽娜进来,大声叫道:“哎唷,我当是谁呢?身体怎么样?”说着伸手摸了摸萨布丽娜那丰满的臀部。
萨布丽娜一把打开他的手:“色鬼!我告诉你老婆去!”
“你在店里的时候不是让我摸来着吗?”
“不到我们店里来就不许摸!”
“嗬——分得到挺清楚。这位是?”那家伙注意到我的存在,问道。
“辛迪的亲戚,在找辛迪。落合经理,把辛迪的情况跟他说说吧!”
我向落合鞠了一个躬,说了声请多关照。
“辛迪?”落合歪着头反问道。
“我们店的辛迪嘛!你这个没良心的,已经把人家给忘啦?”萨布丽娜鼓着腮帮子生气地说。
“噢——去了名古屋的那个辛迪呀?记得呀。”
“果然是名古屋啊?”我不由得凑了上去。
“好啦,那我回去啦。下次请作为客人到我们店里来,今天也可以哟!”萨布丽娜塞给我一张名片,冲我摆摆手,走了。
“关上门!”落合冲萨布丽娜喊了一声,回头把电视的音量调小,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坐下。
我把刚才在“玛布提”说过的那套谎话又对落合说了一遍。
落合听完我的话,说:“我是在川崎火车站碰上她的。当时她拉着一个大箱子,还领着一个小女孩。我问她是不是去旅行,她说她要搬到名古屋去,我吃了一惊,因为太突然了。”
“您没问她名古屋的住址吗?”
“没有。当时我要请她吃顿饭,可是她说火车就要开了,来不及了,只说了两三句话她就匆匆走了。”
“都说了写什么呢?”
“她说要在新横滨换乘新干线去名古屋。”
“还有呢?不是说她跟上了一个名古屋的男人吗?”
“好像是。不过在车站我只看见了她和孩子。”
“名古屋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不知道。”
“她要在名古屋那边开一家店?”
“好像是。”
“店名是什么,大概在什么位置?”
“我没问……不对,问来着,你等等啊。”落合说完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在里边乱翻起来。
过了一会儿,落合拿着一张名片大小的纸走回来对我说:“店名是‘山下’。”说着把纸条放在了茶几上。
我看见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山下。
“这是她跟我分手的时候亲笔写的。”
那是辛迪在“玛布提”的时候的名片,“山下”两个字写在名片的背面。
“是日本式酒吧吗?”
“从名字上看好像是。”
“辛迪是泰国人,为什么给酒吧取这么个名字?会不会是名古屋那个男人的姓?”
“不,是店名,她还对我说,有机会到店里来坐坐呢。”
我觉得也许是辛迪直接把新丈夫的姓用作店名。这时我忽然看见在名片的一角还写着“市场”两个小字,笔体跟“山下”不一样。
“这是什么?”我指着“市场”两个字问。
“这是我写的。对了,我想起来了,我问过她的店在什么地方,她说是名古屋那边的市场,那是我回来以后补记的。”
“市场?”我感到困惑。莫非辛迪不经营酒吧,改行经营海产品了?“山下”这个名字挺像一个海产品批发公司的名字。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嘛,有些大商业街就叫市场嘛。比如说大阪的黑门市场。”落合虽然这样说,也是满脸困惑。
“您没听错吧?”
“那也说不定。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回忆不起来了。”落合摇摇头说。
“谢谢您!托您的福,我觉得距离辛迪越来越近了。”说完我把名片还给他。
“不要了,你拿走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收好那张名片,又说,“对了,再求您一件事,您这里有没有辛迪的照片?”
“没有吧。”落合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站起来再次走到办公桌前去翻抽屉。过了一会儿,他笑眯眯地回来了,“只有这么一张,我们俩好的时候照的。”
那是一张大头贴。心形的框子里,落合跟一个黑头发大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