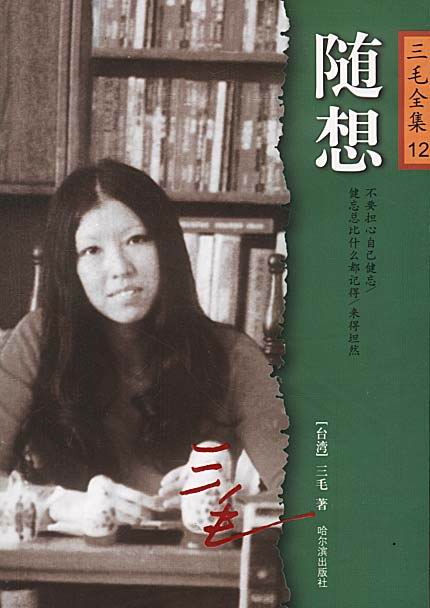����¼-�ͽ�-��8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Ǻ�����һ���������Ҳ��ܲ����ۣ�����
������˵�����Ҿ�������Ӧ�ø��ˣ����ҵĺ��Ӷ����������å��������հ�����Ȼ������ô�죿�����������溦�¡�����
������˵��������ģ����ҵĺ��ӻ�û�������ڵ��ʸ���Щ�����ǡ��ܺ��ߡ��������ֺ��˱��ˣ������Լ������Σ�����Ҳ�����Ρ������ҵ��ĵĵ�����һ���¡��Ǹ�ʱ�����ǿ��ڱտڶ��ǡ����������Һ�ֻ�ǿ�˵���ѣ����Dz�û�С��������Ļ��ᣬ�������ҽ���Ϊ�����˰��צ���ų������ˡ��뵽����Ҳ��ܲ���һ���亹����ʮ���ȥ�ˡ��������쿪����ᣬ��Ҳ�����Ҳ����Dz���ҲҪ��һ�������ĸ��ʮ���������ף�����˰��̨ʮ���ꡣΪ�˲�������ţ������Ҫ���Լ�������˼����վ������ͦ��������һ���ˣ�����
�����������װ�������ҡҡͷ˵��������˵��������Ӧ�����ǹ�ȥ�������˰�һ�ж��Ƹ����ĸ��������һ�ʹ������ĸ�����������ٸ�һ�Ρ��ĸ�������á��ĸŪ�ü����������������ˣ����˴ӡ��ĸ�õ��ô������������¾��Σ�ϣ�����л���ʩչħ�������˱䡮ţ��������������������Ϸ�������������ƣ�����ȴ����ս������������˵����ʮ��֮��ʹ��˼ʹ���ܵ�����ضԴ�������⣬����ضԴ��Լ������뾿�������Լ�����Щʲô����Ҷ�Ӧ����һ���ܽᡣ��ý���һ��������ݡ���һ�����ĸﲩ��ݡ����������ڰ����������ʮ��Ļ�˵�����ˡ���
������˵�����Ҷ�����д����ƪ����˹��������Ӫ�Ĺ��¡������ܵ��ܴ�����Һ��������ι����Ǹ��ɴ�ɱ�˹���һ������Ҳ�������룬Ӧ�ð���һ�г��ġ������ġ��п�ġ����µġ�Ѫ���ܵĶ�������������չ���������������Σ��ô�ҿ���������������μ�ס�����������ٷ����������¡��������ٰ����ǵ�ţ����������Ҫ�����Լ�����ţ�����ˣ���һ���ܹ����Լ�����˼�����ˣ�����
�������ԣ��ԡ�����������ʾͬ�⡣����Щħ�����Ǵ�������Ϸ��ʼ�ġ����Ǻúõ���һ�롢��һ������Щ�仯����Щ���̣���Щ���ԣ���Щƭ�֣���ЩѪ���ܵIJҾ磬��Щ���Ķϳ��ı��磬��Щ���Ķ��ǵij�磬��Щ�п�����Ķ���Ϊ����һ�е�������Ϸ��Ϊ���ǿ��µ�ʮ�꣬����ҲӦ�ö��л�������������һ������������
����������Ҫ����һ������ݣ�һ������ݣ�������������ȫ�ɡ�Ҫ����μ���ʮ���м��Լ��ĺͱ��˵�һ��һ�У������Dz��������ǹ�ȥ�Ķ�����ֻ����������Ҫ��ס�Լ������Σ����Ǹ��������˴��������ѵġ��ĸӦ�ø������Σ��������ܺ��ߣ������Ǻ����ߣ���������һ����������һ����������û��Ϊ���ĸ�ٹ��ֵ��ͷ���������췴�ɣ������ɣ�������ң�ɣ����������Ƿ������ţ�����ô�Ҷ������������վ��ӣ������Լ�Ϊ���ĸ����ʲô����Ϊ���ԡ��ĸ����ʲô����������������ô������������Ƿ�µ���һ��ծ���DZʷǻ����ɵ�ծ��������������˻���ˡ���
�����ҽ��������������֡���
��������һ�ա�����
�������뿪����1��������
����һ��
����ȥ����ڳ����Ϊ�˼������괴����ʮ���꣬�ٿ���̸�ᣬ��ӡ�����ļ����м�λ����ϣ����������ʾ���һ����ڼң����ܵ���ף�أ���д���£�˼�벻���У��Ӻ���������ֻ�ð�һ���Ƹ���ã��δ�����������Ѿ���Ϊ�κ�Ӧ�����·����ˣ���˵��������ҩ��������������Ӧ����ϧ������Ҫ�װ��˷ѡ������������Լ����뷨�úõ�����ʱ���أ��Ҳ���˼����ȴ�������ҵ�һ���𰸡���
������ʼ������δ������ʹδ������ʮ�ֶ��ݣ����Ҳ���������ץס����ʹδ������һƬ����ɫ������ζ��Ũ������ҲҪӭ�����߹�ȥ���Ҳ��£�����������ǰ��һ���й����������뿪������Ȼ�DZ��˳�����Ŀ�������ع˹�ȥ��ȴ�����Լ������顣ÿ�����磬����������������ɢ�������߱��롣ɢ�����Ҷ����ϰ�ߣ����������߲�����Ȧ���е�ʮ�ֳ������·�ˮ����ڽ���ҡ�Σ�����Ҳ�����ȡ���ֻ������������Ϣ��������δ���̵IJݵ��ϵ����⣬����˼�������ڻعˡ������뿪���������Ŀ��δ��ͬ��ȥ������һ���ˡ���һ�γ�ʱ����Ҳ�����ֽ����ʣ��ҵ�˼��ȴ��һ��С�����Ź�ȥ�ļ�ʮ��ת��תȥ�����ڵ�ȷ��Ӧ��д�ܽ��ʱ���ˡ���
��������˵���ҵ���ѧ�����Ǵӿ�����꿪ʼ�ġ��ҵĵ�һ��С˵���ڿ������棬�ڶ���Ҳ�ɿ������С��ڶ���С˵��ԭ����������С˵�±����˻أ������˵öԣ����Լ�Ҳû�����Ľ�ԭ�����ͳ�ȥ����������һ��ʱ������ԭ�������˽ϴ�ĸĶ����͵�������꣬û���뵽�ܿ��������ӡ�˳�������С˵���ǡ���ȥ��̫����������һ��ʧ�ܵ���Ʒ��������̸������ʱ��������˵����������������壬���ӵ�һ��С˵���ҵ��κ���ƷֻҪ�͵�����ȥ�����Ƕ�����ҳ��档�������Dz��������ϵ��Ҳû��������ϰ�����κβ��ŵĸ���������Ҳ����˵�Һ������һ����ͨ��ϵ��Ʃ�磬����������ɡ���������衡��ϰ塱�����뿪����ӡ��ݴ��졶��Ů�ԡ���ʱ���Ҹ�����¿�Ͷ���壨�ҷ����һƪ���ꡤ�ߵ��������ġ���Ů��ŵı��硷������������ȥ������ǰϦ���ҵ����������������������ְԱ����д���DZ�����¼�����мǡ�Ҳ���������ӡ�ˡ������ҵ�С˵����������д���뷢���ľ��������Լ����úܶ࣬�����ن����ˡ�Ҷʥ��ͬ־�����ڿ��������Ҵӷ����Ļ�����ԭ�壬��ȥ�����Ժž����������ġ����ǽ��������������ں���֮ͬ־�Ľ��ܣ�������֮��ѧ�����������ʶ��֮����һ�Ŷ���������ɳ�ࡪ���ﵽ���裬�ŵ�һ�μ�����֮����֮ǰֻ��һ�Ŷ�һ���ڳɶ�ͬ��ͨ��һ���š����ڰ����Լס�������£���������֮����ȥ����֮��ʱ���ǡ�������־����һλ�����ˣ��Ǹ�ʱ��ȫ�������ڼ����з��ж�˹̩����һ�����꣬�ͱ�������ġ����硷�Ϸ�����һƪ����Ļ��ġ��ж�˹̩�ۡ�����֮Ҫ�Ұ���������������ڽ���������������˸����������ͽ𡱡��Ҽĸ����ǵġ�������ԭ�������Ҳ��������֡������ҵ�С˵��һ����ڡ�С˵�±����Ϸ��������أ���������־�����ۺ��Եİ��¿��������з��ж�˹̩�������ڱ���ͷ����ˡ��������á��ͽ�������ַ����ĵ�һƪ���¡���
���������������ڡ��±������ص�ͬһ�꣨һ�Ŷ����꣩�ɿ��������棬���������ǽ�ȥ�ģ���Ϊ������ġ������顷��һ�֡�������䱾�Ĵ����ڿ���һ�����˰��֣����л��������Լ�д�ġ����мǡ�����������д�ġ���ȥ��̫������������ձ�������ȸ�Ķ̾硶���õ����衷�����������ж�˹̩�Ķ�Ļ�硶����֮��������������С�鶼�Ǵ�����������ġ�����һ�֡�ޱ�ȡ������ǰ�������Ķ�ƪС˵����ʯ���ľ�����Ļ�硶ҹδ�롷�༭�ɲ�ģ�������ͬһλ����IJ��������Ρ��������Ʒ����ޱ�ȡ����ҷ���ĵ�һƪС˵����ֻ֪������д����ҹδ�롷������ʮ������ʱ�Ͷ��������ҵ������ǻ��ڳɶ��ݹ��Ȿ��дһ�š�������������ĺܸ��˵�Ϸ��һ�Ŷ��������ڰ�����ҹδ�롷�ķ��ı������ױ���С˵��ޱ�ȡ���һ����֪��������д���Լ���һ�Ŷ�������������꡶ޱ�ȡ�����ɳ�ࡪ����ĸ����ǣ����������Ѯ���뿪ɳ�ࡪ����ʱ���յ����������DZ�С�顣�����ڽ��������µİ���Сס�У���Ϊ��Dz�ҷ�����ȫ����ҹδ�롷���ع�����һ����꿯�У��뱾����������ǡ�ǰҹ����ӡ��һ�棬һ�����������Ļ�����������ʱ�ұ������ʯ���ù��ľ���������Ϊ������ġ�ޱ�ȡ�����ͣ�棬�Ǹ���ƪҲ���ұ�����һ�����ļ����ż����ˡ���
������ԭ������������߶���뿪��Ŀ��Ұ�������ȷ���Ҽ�ʮ����ѧ�������β��õ���ë������������������Ҳ����˵�����Ǽ����˼������;���״̬���Һ����ɣ�˼�뵥�������ǰ����dz�ǿ�ң�����Ҳ����ֿ����һ��ʱ����������Ϊ����ı�Ҹ��������ͻ�������̫��һ����֣�����һ��ʱ����ÿ�쵽�����������㳡��¬ɧ����ͭ��ǰ��˵�ҵ�ʹ�࣬�ҿ�������������д��ֻ��Ϊ���������·��������Ҳ����˵������̽����Ҳ���������������Ϊ�����������鲻����˼��ȡ��ѣ��һ��߰ѡ���˰�������ѣ����߾ͷ�����ꡣ��Ȼ����������ո�����˰���ġ��������Һͽ�ʦ�����꣬��˶�ÿһλ���߲����������Ƿ�������һ���ضԴ���һ������ȱ�ˣ�ֻҪ���ж��ߣ���������ӡ�������д�����࣬�����������ӵĵط�������������Ļ���Ͷ��ˣ�����������Ҳ�����ӡ��Ҵӷ���������������ס��һ����բ����ɽ·������һ��ʯ����¥������ͬ�»������ס�ڶ�¥����ס��¥�¿��ü䡣��Щ��־�ı༭������֪�����ǿ��������ߣ����и������ڿ�����������������Ҫ��������ǽ�Ǣ����д�ø���Ҳ�����Ǵ���ȥ���ҵ�С˵���������͵����ָ����ı������ò�����Я������ȥ�ݷ����ˣ���ֻ�����űʲ��ϵ�д��ȥ�����л�Ҫ˵����Ҫ���Լ�����Ķ����㵹�������Ҹо����������²����ĸ��飬���������еıʣ�����дһ��ͨ���������Ѹ壬�Ҿͳ���˯ȥ���������������ϣ���������ϰ������ͳ�ȥ���Ҳ�ȥ�ݻ�༭��Ҳ������֪���ҵ�����ʵ�գ��Ҳ���Ϊ�ҵ����²��ģ���������Ҫ�����ҵ���Ʒ���з����ͳ���ĵط������ǰѸ���͵�������꣬�����°�����Ҵ�������һ��������������Ӳ������ѣ��ҵ����Ѳ���࣬�����ܿ������ҳ�����Ҫ���������������Ҿ�ȥ���Ѽ���ʳ�͡�������ʼ�ղ��Ѹ�ѷ������ϣ���һֱ�����Լ�Ҫ˵�������ڵ�һλ���㸶���Ҳ�ã�����Ҳ�ã���֮�Ҳ�ΪǮд�������ÿ������±ʣ����ؿ���ɫ�Ӻ����һ��ǵ���һ��ʱ�����Ϻ�������ͼ����־���ᣬ�ڿ��Ϸ��������¶��ý�����飬���а����û����ȡ��ѣ�ȴ����������ļ������ͣ��������ʵ���������ָ����졢���������ֱ༭����ѧ����������Щ�����Ͷ��������һ�����ʱ�ӿ�������õ�һ�ʡ���˰������Ŀ��С����Ҳ���Խ����һ���˵��������⡣������
�������뿪����2��������
����һ����������Ҳ�ͬ����ס��һ���ˣ����ҺͿ����Ĺ�ϵ��û��ʲô�仯�����ǺͿ����ճ�����ת�ţ��ҵ���Ʒ���ϵ����࣬Ҳ����������Լ����ˡ��ҰѸ��ӽ�����������棬���������ԣ������Ұ��������˵�������ƪ�������������ջ����͵�����ȥ������Ҳ�����£���ӡ�������ڿ������ֱ༭��������āD�������ǵ�ʱ�����ڶ�����������Ľ����������ߣ���˼�롰��������֪����д�������������������壬����Ҳ�������ӡ��Ҹ�л�������Һ���ȥ��꣬ͬ����������Ļ���࣬���ѵ�ͬ����̸����ֻ�ǵÿ�սʤ�����ҵ�һ�λ��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