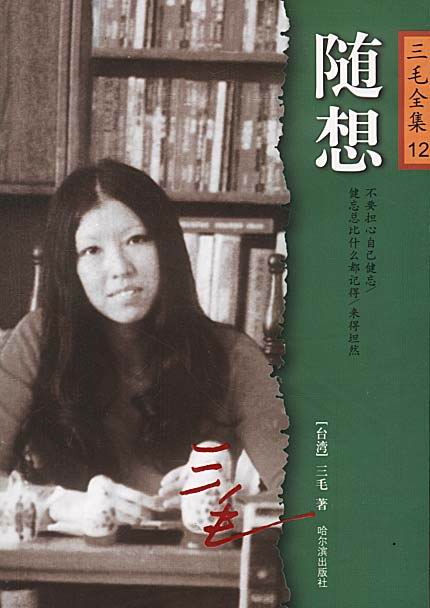随想录-巴金-第7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月六日
买卖婚姻
前不久我接到一个在西北工作的侄女的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从明年起我打算慢慢积蓄一些钱。替大儿子过几年办婚事准备点钱。这地方相当严重。孩子结婚,男家要准备新房里用的如大立柜、五斗橱、高低柜、写字台、方桌、沙发、床、床头柜等等一切东西;要给女家彩礼钱。此外男家还要给新娘买手表、自行车和春夏秋冬穿的里里外外的衣服。结婚时还要在馆子里待客,花销相当大。而女家只给女儿陪嫁一对箱子、两床被子、少量衣物和日用品等。现在年轻人要求更高了,新房里还增加了录音机什么的。人们都说把女儿当东西卖,太不像话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她讲的无非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全国各省市都有人这样做,当然也有人不这样做。但这样做的人为数并不少。而且似乎越来越多。我说“似乎”,因为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根据我个人不很明确的印象,“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迈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突然发觉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尽管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新旧服装,有的甚至戴上“革命左派”的帽子。这是一个大的发现。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眼睛仿佛亮了许多。一连几年我被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游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当时我已从“五·七”干校回来,对我的批斗算是告了一个段落,我每天到单位学习,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以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的梦魇。没有想到残余还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为了反对买卖婚姻,为了反对重男轻女,为了抗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用笔整整战斗了六十年,而我的侄女今天面对着买卖婚姻还是毫无办法。二十几年前她结婚的时候,没有向人要过什么东西,也没有人干涉过她的婚姻。可是她的儿子却不得不靠钱财来组织新的家庭。难道这完全是旧传统的罪孽?她诉苦,却不反抗。许多人诉苦,只有少数人反抗。我看过像《喜鹊泪》那样的电视剧,我看过像《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样的故事片那么多的眼泪!那么多的痛苦!那样惨痛的结局!今天早晨在广播里我还听见某个省份八位姑娘联名倡议要做带头人,做到婚姻自主,与传统决裂。她们的精神值得赞赏;她们的勇气值得鼓励。但是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传统到哪里去了?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反封建的传统到哪里去了?怎么到了今天封建传统还那么耀武扬威?要同它决裂,要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年轻姑娘们还需要有人带头,还得从头做起。总之,不管过时或不过时,我还是要大反封建,我还是要重复说着我说了五六十年的那句话:“买卖婚姻、包办婚姻必须终结了。”
我还要讲一件我耳闻目睹的事。
我的外孙女小端端出世以后,我们家请来了一个保姆,她原是退休职工,只做了几个月就走了。她在我们家的时候,她的儿子常来看她,我有时也同他交谈几句。他不过二十多岁,在什么店工作。他喜欢书,拿到工资总要买些新书、新杂志。他每次来都要告诉我,最近又出了什么新书。他母亲回家后,他偶尔也来我们家坐坐,同我们家的人聊聊。后来说是他做了公司的采购员,经常出差买东西。他不再购买书刊了。不记得过了若干时候,他来讲起他新近结了婚,请了八桌或十二桌客,买了多少家具,添置了多少东西,又如何雇小轿车把新娘接到家中,他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得意。又过了若干时候,听说他已经做了父亲。有一天他的母亲来找我的妹妹,说是他因贪污罪给抓起来了。她想求我设法援救。我没有见到她。过了不多久他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人民法院判了他两年徒刑。这是真实的生活,但是它和电视剧一模一样,这也是买卖婚姻的一种结局吧。它对人们并不是陌生的。
二月九日
再忆萧珊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啊!”
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
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于是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车子的驶近,等待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后来,“文革”收场,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即使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做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录:答井上靖先生(1)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拜读了先生的来信,充满友情的语言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在病中写字困难,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写出我心里的话来。
您谈到我们几次见面的情况。我得承认,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会见,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一九六一年春三月我到府上拜谒的情景,还如在眼前。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您的庭院中积雪未化,我们在楼上您的书房里,畅谈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我捧着几册您的大作告辞出门,友情使我忘记了春寒,我多么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朋友。这是我同您二十一年交谊的开始。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我们访问贵国到处遇见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前进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处处有援助的手伸向我们。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连三年我怀着求友的心东渡访问,我总是满载而归,我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我曾经和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谈,说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访问结束,离开东京的前夕,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联欢,席上大家交谈半个多月的活动和相处的情况,感情激动地谈起中日人民友谊的美好前景,不仅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泪,连我、连比我年长的谢冰心女士,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的灾难。
关于这个,我们两国人民都有难忘的惨痛经验。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人民友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读过先生的名著《天平之甍》,我也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大师六次航海、十二年东渡成功的情景经常在眼前出现。我也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接触到充满友情的善良的心的跳动。人民友谊既深且广,有如汪洋大海,多一次的访问,多一次心和心的接触,朋友间的相互了解也不断加深。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们谦虚,不轻易吐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但倘使什么人或什么事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交出个人的一切,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先生来信中提到“文革”期间十一年的消息隔绝,但我在前面说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谊里仍然包含着这十一年,因为我在“牛棚”内受尽折磨、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经常回忆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坦率交谈的情景,在严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听说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可以说,就是在我给剥夺了同你们会见的权利时,我同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曾中断。而且我们的友谊正是在重重的困难和阻力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两国人民不懈的努力,期待已久的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友谊发展了,合作密切了,大家用心血培育的树木正在开花结果。但是破坏友谊的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