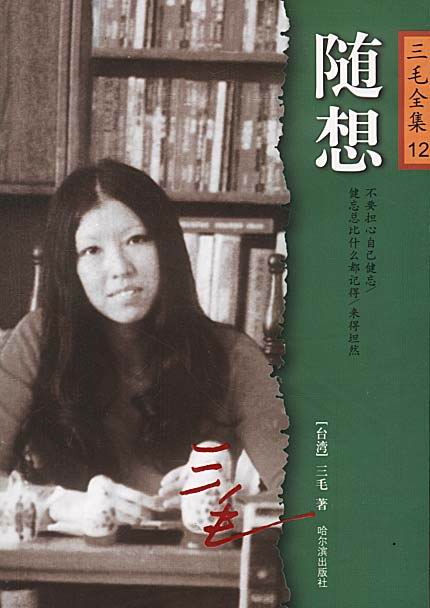随想录-巴金-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做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病中(一)(1)
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里摔断左腿给送进医院的。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的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几个年轻的亲戚,他们轮流照顾我,经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有时头脑清醒,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我反复要自己回答一个问题: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么多的债,决不能这样撒手而去!一问一答,日子就这样地捱过去了,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牵引”终于撤销;我也下床开始学习走路。半年过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但离所谓“康复”还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白天我的情绪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继续在锻炼,没有计划,也没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担心,我也不能不怀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来?”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坚持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梦就能将我完全制伏。这两夜我睡得好些,没有梦,也没有干扰。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总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从未见过面的读者。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最初将近三个月我仰卧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泪。我无法回信,而且在噩梦不断折磨下也记不住那些充满善意的字句。信不断地来,在病床前抽屉里放了一阵又给孩子们拿走了。我也忘记了信和写信的人。但朋友们(包括读者)寄出的信并未石沉大海,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倘使没有它们,也许今天我还离开不了医院。
我出院,《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国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我在医院里度过春节。除夕的午后女儿告诉我,孩子们要带菜来同我一起吃“团年饭”。我起初不同意,我认为自己种的苦果应该自己吃,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下了决心,都赶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顿饭,并没有欢乐的气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吃完这一顿“团年饭”,孩子们收拾碗筷准备回家去(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妇来了。他们说过要陪我度过除夕,还约了罗荪夫妇。孩子们走了,他们一直坐到八点,他们住在静安宾馆,来往方便。我这种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动了他们的心,曹禺又是一向关心我的老友,这次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他比较喜欢热闹,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给我。我和我兄弟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他们夫妇穿上大衣离开病房。
我兄弟照顾我睡下不久,罗荪夫妇来了,他们事情多,来迟了些,说是要同我一起“守岁”,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他们同我兄弟谈了一会,也就扫兴地告辞走了。
我想,现在可以酣畅地睡一大觉了。谁知道一晚上我就没有闭过眼睛。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可是在病房里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讲几句,多坐一会,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难道你变了?”我答不出来,满身都是汗。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我忽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在除夕,在整个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文革”决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话。即使我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也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忘掉了过去的朋友,我想我也会得到原谅,只要我没有浪费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草地边有一个水池。这次我住在三楼。八○年七月我在二楼住过,经常倚着栏杆,眺望园景,早晨总看见一个熟人在池边徘徊,那就是赵丹,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后就要跟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人永别。三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我行动不便,但偶然也在栏前站立一会。我又看见水池,池边也有人来往,也有人小坐。看见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见到了赵丹,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那响亮的声音呢?!
病中(一)(2)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
七月五日
汉字改革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女士转来“活跃在纯文学领域中的”日本作家丸谷才一先生的信,信上有这样的话:“一九八一年夏天在上海见过先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特别是,先生对敝人提出的有关文字改革的问题予以恳切的回答,并且允许我在敝人的书里介绍那一次的谈话”他那本“批判日本国语改革的书”出版了,寄了一本给我,表示感谢我同意他引用我的意见。
我翻读了丸谷先生寄赠的原著,书中引用了我们的“一问一答”,简单,明确,又是我的原话。关于文字改革,我说:“稍微搞一点汉字简化是必要的,不过得慢慢地、慎重地搞。”他又问起是否想过废掉汉字。我笑答道:“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他表示要在他的新作中引用我的意见,我一口答应了。
关于日本国语改革我并无研究,不能发表议论。但说到汉字改革,我是中国人,它同我有切身的关系,我有想法,也曾多次考虑。我对丸谷先生讲的是真心话。我认为汉字是废不掉的,我单单举出一个理由: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
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起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见我的时候说过:“单是会拼音,单是会认字,也还是文盲。”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功夫学会字母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是个多民族、多方言、十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个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国,在西贡 — 堤岸的小火车上遇见一位华侨教师,我们用汉字笔谈交了朋友,船在西贡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汉字,我们两个中国人就无法互相了解。
我还要讲一件事。《真话集》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接到样书,就拿了一册送给小外孙女端端,因为里面有关于她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书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认识,拿着书读不下去。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香港同胞使用的汉字大陆上的孩子看不懂,简化字用得越多,我们同港澳同胞、同台湾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汉字简化必须慎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汉字是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跟汉字打了七十几年的交道,我也有发言权。我从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不下数百篇,至今还记得大半。深印在脑子里、为人们喜爱的东西是任何命令所废不掉的。
我不会再说烧掉线装书的蠢话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讲过的话。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要不断发展,变得复杂,变得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
我们有的是吃“大锅饭”的人,有的是打“扑克”和开无轨电车的时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学汉语汉字并不比学欧美语言文字困难。西方人学习汉语汉字的一天天多起来,许多人想通过现代文学的渠道了解我们国家。我们的文学受到尊重,我们的文字受到重视。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谁也毁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别的人。
以上的话,可以作为我给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补充。
七月九日
病中(二)(1)
在病房里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梦,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梦,把“牵引架”当做邪恶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儿子、女婿或者亲戚,要他们毁掉它或者把它搬开,我自己没有力量“拿着长矛”跟“牵引架”决斗,只好求助于他们。怪梦起不了作用,我规规矩矩地在牵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