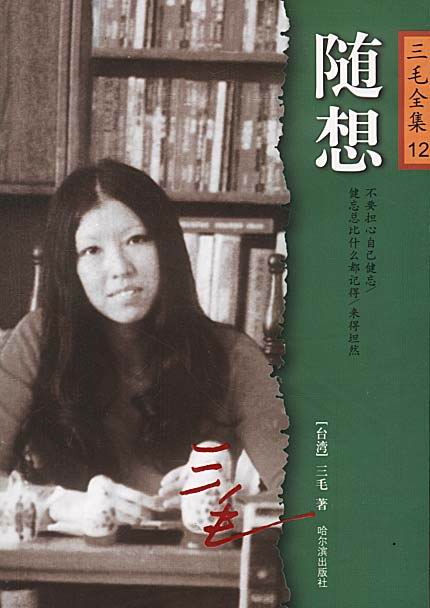随想录-巴金-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再论说真话(2)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写真话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②,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腹地
西彦同志在介绍“牛棚”(和“劳动营”)生活经验的文章里提到关于“”的批判。这件事我早已忘记,翻看西彦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发生的事。我们起初在那里参加“三秋”劳动,干完了本来要回上海,但由于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就留了下来,等到第二年年初,我们文化系统在奉贤县修建的五·七干校建成后,直接搬到那里去。当时我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面,靠边的人多数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垫了些稻草。除了劳动外,我们偶尔还参加班组学习,就是说同所谓“革命群众”,同“造反派”在一起学习。也就是在这种“学习”的时间里,“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短文里用过的一句话:“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民间”他们解释说,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这就是苏区,苏区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们揭发我“鼓动青年到苏区去搞破坏活动”。他们要我写交代和检查。
多么可怕的罪名!幸而当时我已经不那么迷信神了,否则一块大青石会压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给一个中学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简》里面,后来又给编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文章里有这样一整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对于“腹地”两个字《辞海》(一九三七年版)里就有这样的解释:“犹云内地;对边境而言也。”我不承认所谓“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释。我几次替自己辩护,都没有用。在我们那个班组学习会上我受到了围攻。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腹地是内地。他就是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当时也是“牛鬼蛇神”,还是很早揪出来的一个,据说问题不小,当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