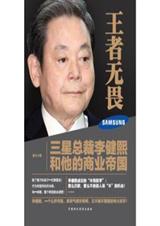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收回已交给长子的大权
送走父亲后,严庆祥耳边不时响起父亲临行前的话: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你要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自香港回上海后,严裕棠一直有点后悔,当时真不该心血来潮,对严庆祥说了那一番话。
此时,严庆祥受政府委派,先去欧美考察,然后又随中国雇主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劳工大会。
严庆祥从国外回来,正值棉纱销路滞极,价格急剧下跌,跌到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原因是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及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农田大部淹没,不但当年颗粒无收,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通,影响到冬耕,以至第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缺乏种籽,不能普遍播种,从而又影响秋收。几经折腾,百姓食不果腹,更未逞添补衣着。严庆祥瞄准机会,在同行不曾提防、市价不易波动之时,吃进大量种子,狠狠地赚了一笔。
紧接着,又一个机遇接踵而来,中国、劝工两银行以债权人的名义拍卖隆茂纱厂。
隆茂纱厂最初是永元机器染织公司,系一九一七年国人首创的利用新法漂染的工厂,因经营不善,于一九一八年转卖给日商东华纺织株式会社,改称为该社的第一纱厂。一九二九年又因营业不振卖与华商,更名隆茂纱厂,结果又赔钱过重,负债累累。由于原有机器厂房年久失修,加之纺织业正遭受空前的灾难,无人愿意接手。
严庆祥仔细调查后,又一次以其过人的胆略与精明,以三十五万两的廉价购得。之后,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也和当年改建扩充苏纶纱厂一样,由大隆将原有机器整修扩充为一万七千余锭,并新增布机四百七十余台,相继开工,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誉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
这时,严家参股的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先后提出,请严庆祥兼任三厂的总经理。
形势逼人,严裕棠此时无法装聋作哑,想来眼下有些事,只能靠严庆祥去办,至少便当点。假使不给他点好处,不压担子,他肯卖力气去办吗?办好了,是应该的;办不好,我就刮他鼻子。于是,他马上召齐所有的儿子,庄重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由长子继承父业,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严庆祥心想事成,当然十分得意。众兄弟都很不满,但只能暗地里发牢骚而已。
此时,严庆祥除了父亲名下的房地产无法过问外,光裕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执掌在他的手中了。大隆的资本额为五十万元,苏纶的固定资产则达一百三十万元之多,庞大的流动资产还不计其内,还有其他厂家的股份。梦寐以求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他心花怒放?
有一点严庆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外国在华企业的倾轧下,在本国官僚资本企业的排挤下,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已属上上大吉,至于发展全靠机遇,当企业积累不能转化为再投资时,便只能转向投机。一般人,一听“投机”二字就莫名其妙地深恶痛绝,而聪明人正是因为会投机才成其为聪明人的。其实,严庆祥对父亲把资金转向房地产经营一直有看法,他则是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收获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一枪,中与不中立刻见效。交易所的老手哪一个不是赤手千金,大发其财!
严庆祥是做花纱交易的老手,静安寺路十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过去手头紧,只好小玩。前两年大做了一笔美棉生意后,连号称“长枪将”的陶继渊都敬畏他三分。
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于是,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吃素菜馆子。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如今的严庆祥手里有了本钱,更想跃跃欲试,怎能听进去呢?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因白银外流、银根紧缩、财政困难、军费浩大等诸种因素,决定实行法币政策,国内的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法币政策付诸实施后,大量收兑银币,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却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
严庆祥春风得意,哪肯放手。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买进卖出,依然一番热闹气象。陶继渊等人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碰到一起,依然用手势交换着一些不可为外行们知悉的行情。但是,对于法币看好与看坏,似乎都各怀鬼胎,不置一辞。
严庆祥虽然谋到了光裕公司总经理的高位,但各厂的厂务都有各个兄弟处理,无须严庆祥特别操心,常常闲暇无事,便不时出入交易所,窥伺动向,以求一逞。其时,花纱市价不振,按严庆祥的估计还会下跌。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一下,便避开同行耳目,大出手,在市上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木已成舟,一闷棍之下,匆匆了结,已经亏耗了八十余万元!严庆祥元气大伤,捶胸顿足,痛惜不已,无地自容。
严裕棠得知此事,忧愤之余,深感自责,大错已经铸成,唯有亡羊补牢了。他立刻罢免了严庆祥的总经理职务。严庆祥早已明白自己的这个短命的总经理已经做到头了。
严格棠没有流露丝毫怜悯,说他专制也好,说他冷酷也好,在贯彻自己的经营路线上,他不愿感情用事。
连续遭受无情打击
通过严庆祥一事,严裕棠意识到,将全部家产交付给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冒险。好在是八十万,若被严庆祥全数压上去,岂不要倾家荡产?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沦落街头,自己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严裕棠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轮流做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
世事多变,每周开一次会,既可以通一次气,又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采纳与否及如何执行须经严裕棠最后裁决。
中央业务会议的轮流执政,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各厂的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子越发不能清静了。
权衡利弊,严裕棠再次应变。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严裕棠走这一步无非是对各个儿子的权限的一次再分配。这样的分配是迟早要进行的。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各厂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营。
光裕公司随之撤销。此时,政局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随着形势的变化,严裕棠突然热衷于创览报纸,关心时局了。
在此期间,中国各阶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日情绪日甚一日,反日运动到处兴起。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气势汹汹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次认识日本”。中国面临着外寇深入、山河破碎、遍地烽火的最危急的局面。
严裕棠时而烦躁,时而沮丧,时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西安事变之后,他的心中曾经燃起一线希望,如今连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考虑得最多的自然是严家偌大的一份家产如何保住,这可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然而,他又不能不抱有一丝侥幸,但愿自己设想的最坏的局势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又一次震撼了严裕棠,上海面临更大的威胁,严裕棠陷入了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时,政府专员林继镛抵沪与工商界人士组织上海工厂内迁委员会,将大隆也列入委员会。严裕棠觉得多此一举。
这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上海朝不保夕。
严裕棠开始实行他的预定计划。他首先把贵重的机器材料迁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仓库。这是通过严庆祺、严庆龄的种种关系接洽的。掸臣洋行是一家德商洋行,十九世纪末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设有机器、保险、生镍检验及工业机械等部门,恰可对号。其时,德国正称雄欧洲,日本也不至于找德商的麻烦。
为了应付内迁,严裕棠将一些比较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西上。此举正在进行中,大隆已被日军占领。
盛夏镇暑,连日奔波,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加之内心郁积不舒,怎能经此打击?身子顿时瘫软下来。在病榻上,他吩咐严庆祺马上去重庆加强与政界朋友的联络,保持关系。严庆祺领会父亲的用心,即刻起程,前往重庆。
所有的工厂被日军占领之后,一段时间里,严裕棠及其儿子们无所事事,显得无聊起来。
严裕棠盘算着,大隆未及撤出及运往苏州损失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制品等占百分之六十四强,而运入租界保存下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强。他越算越感到痛心,越算越感到烦恼。如此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
正当严裕棠煞费苦心却又一筹莫展之际,严庆祥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海滩的一批绅商闻人马上就要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号召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允许重操旧业,也允许新办实务。
严庆祥带来的这个消息,使严家又活跃起来了。严庆龄第一个蹦起来要大显身手。既然如此,那就无须舍近求远了。虽然看起来,迁厂的损失是巨大的,但立厂的精华到底还是保存下来,这是足以自慰的。
不管别人如何,严裕棠总要仔细斟酌利弊。心想:自上海沦陷之后,大江南北也相继沦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纷纷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旅馆、影剧院经常满客,茶楼酒肆高朋满座,各家商号无不生意兴隆,被称作“孤岛天堂”。故此工商业复业者日多,特别是纱布生意,因为战时纱厂毁损最大,纱布筹码枯竭,价格步步上升,投机分外热闹。纱业的畸形兴起,对棉纱机器的需要顿感迫切。要进口机器,不仅外汇困难,在时间上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左右,远水救不了近火;上海原有能造棉纺机器的厂家内迁的内迁,毁坏的毁坏,仅有的几家哪里能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即使新办的纱厂,大部分是急功近利,购买旧纱厂的机器来东拼西凑,以敷一时之用。这对于拥有生产设备、具有生产能力的严家来说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备。这两兄弟同在德国留过学,都堪称机械方面的专家。严庆禧为人随和些,肯礼让三分,配合较为骄纵的严庆龄,又是最适当的人选。
厂址很快就选定了,设在越界筑路的渚安浜路,以借租界保护。为更隐蔽起见,不用大隆名义,而是假借了美商的